- +1
“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李金发诗作的“感伤颓废”
【编者按】
《李金发诗全编》是中国象征派诗歌开创者李金发诗作的首次集结,汇集了他自20世纪20年代从事创作以来的全部诗歌作品,其中包括《微雨》《食客与凶年》《为幸福而歌》《异国情调·诗》《集外诗汇编》等,附录还收录了李金发搜集整理的578节民歌《岭东恋歌》及陈厚诚教授整理撰写的《李金发年谱简编》。
陈厚诚教授在该书序言《李金发:中国新诗史上的“盗火者”》中就几十年来李金发诗作被质疑、批评的“晦涩难懂”“感伤颓废”和“文白夹杂”这三个问题进行了阐发——“这三个问题,一个属于艺术方法,一个关乎诗歌内容,一个涉及诗歌语言。这三方面的表现,本来都属于李金发诗歌的艺术特点,它们都是对新诗发展的贡献,但却长期被当作缺点和问题给予批判和否定。”本文节选自其中对“感伤颓废”问题的讨论,澎湃新闻经四川文艺出版社授权发布,标题为编者所拟。

青年时代的李金发
首先要明确,与上面论及的“晦涩”一样,“颓废”一语在诗歌领域表示的是一种美学倾向,它与人在生活中潦倒放浪、自暴自弃的堕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种美学倾向起源于法国象征派先驱波德莱尔。波氏在为他的诗集《恶之花》草拟的序言中曾说:“什么叫诗歌?什么是诗的目的?就是把善同美区别开来,发掘恶中之美。”在这种美学观的指导下,他便在诗歌创作中实行了审美对象的大转移,将自己的视线从传统的田园风光、动人爱情转向现代大都会的丑恶。这样他就将诗歌创作由“审美”变为了“审丑”,他将自己的诗集定名为《恶之花》,表明了他就是要“从恶中提取美的东西”。
到了19世纪80年代,由波德莱尔开创的象征主义在法国形成了一个文学运动和流派,其代表人物有被称为“象征派三杰”的魏尔伦、兰波、马拉美等。由于象征派诗歌也像波德莱尔的诗一样充满了颓废、绝望、病态和忧郁的声调,所以人们送给象征派一个称号:“颓废派”。魏尔伦于1886年创办《颓废者》杂志,欣然接受了这个称号。所以在法国文学史上象征派又称为颓废派,波德莱尔则被视为颓废派的先驱。
在波德莱尔的影响下,李金发在诗歌审美对象的选择上,除小部分诗仍然直接表现了美的善的事物外,多数的诗都是面向生活中的阴暗面,大量营造衰老、死亡、梦幻等丑和恶的意象,并通过这些意象来寄托、抒写自己忧郁、痛苦、厌倦、绝望等内心情绪,带有明显的“以丑为美”“从恶中发掘美”的美学倾向。李金发成了一位颇具颓废色彩的诗人。
对于李氏这种唯丑、颓废的倾向,评论界早有察觉。黄参岛就曾称李氏是一个“唯丑的少年”,指出李诗具有波德莱尔“以丑为美”的倾向,“厌世、悲观、颓废、感伤是其诗歌的基调”。不过当时这种评论,是就李诗的创作特色而言的,并无贬义,反倒是肯定这样的诗“才是上了西洋轨道的诗”。
20世纪30年代,李金发开始受到来自左、右两方的夹攻:现代评论派的梁实秋指责他“模仿一部分堕落的外国文学,尤其是模仿所谓‘象征主义的诗’”;左翼诗人蒲风则批评他的诗所表现的只是在时代大潮面前“落伍的人们的苦闷”,等等。这就开始显现了对“颓废”予以否定的趋势。
到了20世纪50—70年代,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对于李诗“颓废”倾向的批判更加升级。有人说“李金发留学法国,巴黎的那种霉烂生活,使他沉浸在官感的享受里,形成了他的颓废的买办资产阶级思想”,而在诗歌创作上则是“法国象征派诗那种逃避现实的以幻梦为真实,以颓废为美丽的‘世纪末’的思想和他的思想起了共鸣”。国内通行的高校文学史教材则尖锐批评李金发的象征派诗“充满了感伤颓废的色彩”,认为其离奇的形式“正是为了掩饰他那种颓废的反动内容”,所以将其归入新诗发展途中的“逆流”,称其“所起的作用是反动的”。这样,“颓废”就从一个诗歌的美学倾向变成了阶级属性和政治倾向问题,受到严厉的批判和彻底否定。
直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随着思想解放和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北大孙玉石提出不能将自然界和政治斗争中的“逆流”概念用来定性文学艺术流派中的各种复杂奇异的现象,他的这一看法也得到了老一辈新文学史家王瑶先生的支持,这才引发学界对于李金发大量以丑恶事物入诗和颓废问题的重新思考。
孙玉石首先在《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一书中,澄清人们对象征派“唯丑”倾向的误解,说明象征派诗人“不是为嗜丑而写丑”,而是“在丑的描写中表达了美与丑相互转换的观念”,而李金发“正因为追求美,他便更憎恶丑”,“丑恶,死亡和梦幻,便都纳入了他艺术表现的视野”。
此后,孙玉石在《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8)》一书和《论李金发诗歌的意象构建》等文中,继续对李金发这种“唯丑”的倾向做了深入的研究。他研究的特点,正像他研究“晦涩”问题一样,主要是在学界对象征派“以丑为美”的倾向已成共识之时,他则在对现代解诗学的倡导和实践中,将这一理论共识落实到对李氏具体诗作的解读之中,回答了李金发在诗歌创作中究竟是怎样让“丑”的意象显示出“美”的问题。
根据孙玉石的研究,在“以丑为美”方面,李金发最常用的方法是以丑的意象与被比喻的对象强行搭配,造成一种传达上强化自己的情绪和读者接受印象的效果。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对《夜之歌》这首充满浓重颓废色彩的诗的解读:这是一首爱情的绝望之歌,诗里写的本来是爱情失意之后,自己不愿再回忆过去那段美好时光(“粉红之记忆”),但却用“发出奇臭”的“朽兽”的意象来形容;又用“死草”“泥污”“可怖之岩穴”“枯老之池沼”等丑的意象来渲染诗人痛苦绝望的感情。而正是这些丑的意象的渲染,让读者能在怪诞中更深地体味到诗人的心,一颗跃动着生命、跃动着爱的渴望的年轻人的心。于是丑的意象经过体味就变成了美的理解与获得。
另一个重要途径是,李金发自觉地在死亡意象里开掘关于人生的哲理,赋予死亡以更富意蕴的承载。诗人时而将“死”描写得“如同晴春般美丽,/季候之来般忠实”(《死》),时而把夜形容为“如死神般美丽”(《心为宿怨》),让人认识到死亡只是生命的必然归宿,无法逃脱,并赋予死神以美丽的色彩,从而大大化解了读者对死亡的恐惧感。特别是《有感》一诗,通过“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这一美丽而奇警的意象,传达了生与死近在咫尺的感喟,将生死问题上升到哲理性的沉思,从而给死亡意象带来了幽深的意蕴与审美品格。
此外,李金发还常使用通感、比兴等手法,来给营造的死亡意象带来审美的效果。例如《夜之歌》中“粉红之记忆”一句,记忆是没有颜色和气味的,它只是感觉世界的现象,诗人却用“粉红”色形容记忆,还让它发出“奇臭”之味,用视觉、嗅觉的词来修饰感觉现象,从而加深了“那些无限美好的往昔爱情我再也不愿去回忆了”的沉痛感。这种“通感”手法的运用,在看似不合理的搭配中,却造成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让读者得到一种簇新的审美感受。《有感》一诗则有比兴手法的成功运用。“残叶溅血”是一个明喻,用秋天肃杀,红叶如血飘落地上,来比喻生命的凋零,意象十分鲜明,它衬映和强化了后面一句主题歌“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死神唇边的笑”是一个美丽而又神秘的、带有不确定性的意象,是一个暗示,可以让人产生许多神秘的遐思。这个暗喻和前一个明喻就如电影中两个叠加性的镜头,接连推到读者眼前,将起兴的喻体与被比喻的本体微妙地联系起来,造成极好的审美效果,“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因此也就成为20世纪新诗中一个经典性的意象。
通过上述这样的分析研究,孙玉石指出李金发对于“丑恶”“死亡”意象的关注与描写,其中也“包含了他对于真善美追求的一种曲折的表达方式”;认为他的诗歌“对‘丑’的凝视,已经成为对于美的挖掘的变形”,而对于“死亡”的关注则是“对于死亡进入形而上层面的思考”,“在死亡意象里显示出生的美丽”。总之,这些诗“是对于诗歌旧的传统经验的破坏与挑战,也丰富与拓展了新诗的经验所拥有的更大的自由空间”。不过,孙玉石在对李氏这类诗做出高度评价的同时,也曾不止一次指出作者“没有西方象征派大师们那样深刻的社会批判精神”,是其不足,这也是应予注意的。
关于李金发诗歌的“颓废”倾向问题,除孙玉石外,还有不少年轻学者著文探讨。有人指出李金发在自己人生经历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的“生之冰冷”与“死之温暖”的生命意识和死亡哲学。在这种意识和哲学的影响下,“他用炽热和激情的文字描写死亡的美丽,正衬出了他对生命的期待和幻想”。有人称赞李金发将“丑的意象和复杂的色调引入诗歌,不仅拓宽了中国诗歌的意象和色彩的领域和范围,而且强烈地冲击着人们传统的审美习惯和审美心理,颠覆了在人们心目中传承已久的,只有美好的东西才能成为审美对象的无形成规”。还有人认为,是资本主义时代工业规模的扩大和都市化的无节制膨胀,造成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制造出颓废者和反叛者。“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便宿命般地注定了必然要受到外界和自我的约束,而难以摆脱痛苦和不幸的纠缠”,而这“正是李金发的象征主义诗歌所要表达的人的存在性的难题”。就此而言,李金发的诗是“超越了当时主流诗歌所承担的历史使命趋赴和现实主题的功利性诉求”,也“超越了特定时代和民族地域的狭隘,而呈现了世界性的广阔,透视一幕在现代性的光环笼罩下人的生存的颓废图景”。
另外,还有研究者联系李金发在巴黎的生活状况来探讨诗人颓废倾向形成的原因,根据诗人对留学巴黎期间“没有物质的享受,所谓花都的纸醉金迷,于我没有份儿,我是门外汉”的自述,指出过去有人认为“李金发留学法国,巴黎的那种霉烂生活,使他沉浸在官感的享受里,形成了他的颓废的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说法,是缺乏事实依据的。恰恰相反,诗人在异国所过的孤寂清苦的生活,所受的异国学生的歧视和欺侮,以及所见到的种种人间悲惨、丑恶的现象,才是将他推入悲观颓废境地的现实根源。李金发也曾幻想过“欢乐如同空气般普遍在人间”的理想境界(《幻想》),但这幻想却被无情的现实所击碎。所以他的颓废是由时代社会造成的,他和同时代被称为颓废作家的郁达夫一样,患的都是一种“时代病”,或者说他们都是“时代病”的表现者。从这个角度看,李金发与波德莱尔也有相似之处,也像波氏一样是“生活在恶之中,爱的却是善”。他虽无力与丑恶的现实抗衡和斗争,但却也始终不曾向黑暗现实屈服,更没有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正像他在诗中表示的“我不懊恨一切寻求的失败,/但保存这诗人的傲气”(《春城》)。李金发是一位在黑暗中饱尝了“心灵失路”的痛苦,但却保持了自己的那份正直和骨气的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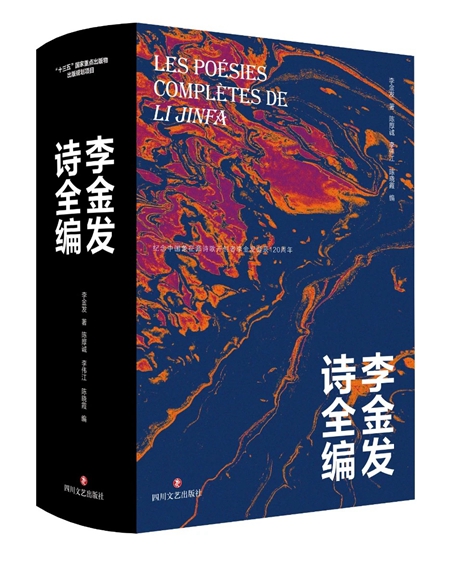
《李金发诗全编》,李金发著,四川文艺出版社2020年12月。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