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的读书经验”|葛剑雄:不同的目的,用不同的方法读书
上海志达书店的“悦悦讲坛”邀请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特聘教授傅杰主持题为“我的读书经验”系列讲座。傅杰表示,“将不定期邀请我敬佩的师友来书店,或忆一忆他们的读书经历,或聊一聊他们的买书故事,或谈一谈他们的读书心得,或向青年朋友推荐若干他们心目中的好书。”澎湃新闻经“悦悦图书”授权刊发该系列讲座稿和视频。
第八讲傅杰邀请到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葛剑雄。葛剑雄著有《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发展史》《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黄河与中华文明》《悠悠长水:谭其骧传》等,部分著作编为多卷本《葛剑雄文集》。

葛剑雄在讲座现场
得知要来讲读书经验,我考虑之后决定按照三个部分来讲。第一部分,讲讲我自己的读书经历;第二部分,讲讲我自己的读书体会;第三部分,就读书对于人生所起的作用,谈谈我的看法。
一、我读书的三个阶段
今年已经七十六岁的我,回想起自己最早看见有字的材料并且产生兴趣,是在我进小学之前,大概四岁到五岁之间。我把自己的读书经历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不自觉地读书;第二阶段,比较自觉地读书;第三阶段,随心所欲地读书。
(一)不自觉地读书
我出生在浙江吴兴县(今湖州市)南浔镇,一个远近最富的地方,富商按照财力多寡有“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这样的等级。但我们家,不要说“象”,跟“狗”都没有什么关系。我的父亲原本是绍兴人,到南浔来当学徒,然后留了下来,有了我们这个家庭。我们是外来的,也是底层的。在这么富的镇上,我们这样的家庭却几乎是没有书的。
我总觉得,读书跟一个人的天性是有关的。不到五岁的时候,我已经对那些有文字的纸产生了兴趣。有文字的纸是哪里来的呢?窗上、墙上有些地方破旧了,就会拿报纸贴在上面,通称“申报纸”。为什么叫“申报纸”?因为旧时《申报》影响力很大,哪里需要用报纸去贴、糊、包,都是用《申报》,后来民间就把报纸都称为“申报纸”了。小时候看着这些报纸,我就很感兴趣,那时也不识字,只觉得上面的东西很好玩儿。
后来,家里的姐姐上小学了,我就吵着也要去,所以就提前进了小学。我们那个小学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就是《明史纪略》的作者庄廷鑨修史的地方,原来是一个寺庙(叫圆通庵),门槛筑得非常高,我要在别人的帮助下才能跨过去。姐姐把课本拿来,我就会翻,也会跟着念,不管念的对不对,就那样念过来了。到我真正上学以后,大概因为自己的记忆力还不错,别人都把背书当成考试性的,我却背得很愉快。
等到大我两届的姐姐进初中的时候,那时的初中课本已经把文学跟汉语分开了。文学的那一本上是大量的古诗词,我就拿过来翻。所以,我在上初中之前,就把初中课本上所有的古诗文都背出来了,当然,意思是不太明白的,也不考虑是为了什么,只觉得好玩儿。这就是一种不自觉的读书。我现在也经常劝家长们,不要逼着孩子学这个、学那个,如果孩子自己看到觉得好玩,就让他去随便翻,也许就把他的潜能激发出来了。
尽管我当时有这样的兴趣,但比较可惜的是,我周围没有什么有文化的人,我的父母只有小学的文化程度。家族里能够接触到的文化程度最高的是我的舅父,他先考了平湖师范,后来又去浙江大学上了两年,但他学的是数学。所以,我都是凭自己去读书,喜欢什么书就看什么书。我记得小时候翻过一本《中国历史故事》,那是我最早接触到历史,书里的内容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清清楚楚。后来又翻过不知哪里找来的《丁丁游历北京城》,是一个系列的书,讲主人公从上海坐火车到北京一路的见闻感受,很多内容到现在我都记得。

《丁丁游历北京城》
到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转到上海来了,读书的机会就多了。家附近有新华书店,我就到新华书店去翻书。等到初中有学生证了,还可以凭学生证到上海图书馆去看书。我家住在闸北老火车北站后面,后来又搬到共和新路铁路边上。那时舍不得花钱坐车,就走大概四十分钟到老上海图书馆,也就是现在人民公园边上美术馆的位置。那时看书也没有什么目的,就是什么好玩看什么。
有一天,我看冯梦龙“三言”里面有讲到王勃写的《滕王阁序》,觉得很有趣,就去问哪里可以找到《滕王阁序》。别人告诉我《古文观止》上有,我就借《古文观止》去看,看了觉得文章写得确实好,虽然好在哪里也不知道。特别是读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觉得特别好,就努力记下来,记不下来就先抄下来,后来竟然把《滕王阁序》背下来了。在这样的兴趣下,我慢慢对中国古典文学相关的东西都很感兴趣,也读了更多相关的书。
一次,老师带着一批大队的干部去新建的闵行一条街参观工厂之类的。我其实不是干部,但是负责出黑板报,就被聘作宣传干事,所以就和大队干部们一起跟着老师去。中午在那边吃饭的时候,语文老师见我在看书,就问是什么书,看了一眼是《楚辞》,就问:“你看得懂吗?”我说:“大概看得懂一点。”然后他又问我:“你还想看什么书?我给你借。”因为那时候学生是很难从图书馆借书的,都要图书委员给登记,而且书也很有限。后来,历史老师也发现我喜欢看书,对我说:“我们老师的书,你想看什么都可以给你借。”就这样,我又看了很多书。要说当时对什么感兴趣,也不定,兴趣很广,样样都喜欢,拿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精力也不错。
自己家里没有书,学校借到的书也很有限,但还有一个读书条件,就是旧书摊。当时,在旧书摊上坐着看,每天是一本一分钱;借回家看,每天是一本两分钱。我一度对《三侠五义》等武侠小说很感兴趣,这些是图书馆里没有的,我就在旧书摊上看。还有一段时间,还珠楼主在报纸上连载武侠小说,我也看得津津有味。《水浒传》《水浒全传》《水浒后传》等这类书,大多也是那时候看的。
有的书,说不定看了之后就会对自己产生怎样的吸引力。念初中时,苏联还是“老大哥”,当时我们看了一本苏联的英雄故事《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是柳·科斯莫杰米杨斯卡娅写的关于女儿的故事。后来科斯莫杰米杨斯卡娅来中国访问,报纸上报道很多,我就又看了一遍《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这个故事里讲到,卓娅和舒拉曾经看过一本书叫《牛虻》。出于好奇,我千方百计把《牛虻》这本书借来,从吃过晚饭后,用整整一个晚上把这本书看完了。这是我第一次看《牛虻》这样的书。不晓得什么原因,那天看得非常激动,特别是看到他的爱情、他和父亲的关系等。书里好些地方,让我多少天都丢不下来,也说不出有什么感悟,就是对自己的吸引力很大。这大概跟读书的年龄也有关,我正好处于从小孩子到青少年那种懵懂的阶段。在那之前我看的很多书都是讲革命的,涉及爱情和人性的内容,我是在这本书里才第一次看到。

《牛虻》
我一度很喜欢画画,也没有人教,就自己画。那时有很多连环画,我就比着连环画上的东西画了好多。我初三的时候,闸北区新建了一个少年宫。少年宫都有很多课外小组,是不收钱的,只要有本事就能考进去。我同时报了美术班和文学创作班,都考进了,结果两个班是同一天活动,我又都不想舍弃,只好这个星期参加一个,下个星期参加另一个。本来是这样维持着的,后来美术班开始要进入油画的学习了,我就退出美术班了,因为虽然不收学费,还是要颜料费的。当时我家里连买彩笔都只买五彩的,觉得十三彩的太贵了,更别说买颜料和画布了。后来,四川路的市青年宫办了书法班,我去报名,也考上了。那个书法班真的是个很难得的机会,教我们的是很有名的书法家,虽然是个大班,他还是会一个个学生来辅导。不过,学了一期之后,我因为太忙就退出了。
到了高中阶段,我读书就稍微自觉一点了,会想到将来的目标是什么。数学比赛这类的尝试止步于一轮以后,我就知道自己在这方面大概没有多少能耐,所以就把兴趣放在了文科上。文科究竟是什么呢?我最初也不明白。后来在少年宫遇到一位文学班的辅导老师,他其实是当时河南路上一家染绸厂的厂校老师。因为接触下来关系越来越好,后来我就开始到他家里去求教,这才知道他跟钱锺书先生是表兄弟的关系。他借给过我很多书,也引导我要看什么书,于是我就对文史越来越感兴趣了。当时,我一门心思要报考北大的古典文献专业,就从文、史两方面去准备,读书目标也就比较集中了。他说,学古文只看《古文观止》还不够,我就照着他给的书单去看书。他跟我说哪本书很好,我就借来去读。有些书他建议通读,我就通读一遍;有些什么地方他建议认真看,我就认真读。
高二的暑假检查身体,当时同学普遍营养不良,还查出来四个是肺结核,包括我。我的状况最严重,需要马上休学。休学期间别的事做不了,但总还可以看书,因为我不想把功课丢掉。这时,老师们帮了我很大的忙。我们市北中学当时是市重点,书还算比较多的,但一部分书是不外借的,阅览室也比较小,按照规定只有老师可以在图书馆里,学生是不能进去的。我的历史老师、语文老师以及其他学科的老师,都帮我去跟图书馆打招呼,所以那时凡是老师能借的书,我也可以借,还可以到教师阅览室里去看书。这个时期,我算是比较有意识地看了很多书。
因为身体还不合格,我高中毕业时不能参加高考,老师们就劝我先工作。当时上海缺少语文教师,上海的教育学院就给各区的教育局开了一个师资培训班,按照规定的办法,如果是重点高中的就可以留在原来的高中培训,如果不是重点高中的就调配到其他中学去,在中学里经过一年的培训之后就可以正式当教师。于是,我就留在我的母校市北中学培训。一开始我说想教语文,班主任告诉我语文教师负担最重,不但要备课,要每两个星期批改一次两个班级的作文等等。他知道我英文还不错,就建议我教英文。
我们是高一才开始学英文的。按照之前的传统,上海的高中是应该全部学俄语的,但我们1960年升高一的时候,我国跟苏联已经产生裂痕了,所以从我们那一届学生开始,一半学英文,一半学俄文。我正好分到学英文。我生病休学期间,因为喜欢英文,就把高三的英文课本都背出来了。回到学校后我就直接上了高三。有一次考试,我五分钟就交卷了,同学们也不太认识我,大概以为这家伙交的是白卷。监考老师看到我写好了,但还是劝我再看看,我说不需要再看了,就交了。其实,高三期间有好几位老师了解我的学习程度之后跟我打招呼说,这个课我可以不用听,于是我就在课上看我自己的书。
要做英文教师,我心里明白,我这个英文水平是不够的。所以,我1965年8月先到学校报到,然后一开学就马上报名到上海外国语学院夜校部进修。夜校部进去之后是按照成绩分的,我被分在二年级,接着从二年级往上读。因为要教学生,我找了很多英文的书。那时上海外语书店内部门市部以便宜的价格卖很多苏联的教材,我也买了各种能够买到的英文书。此外,我还订了一个英文的杂志《英语学习》,又找来许国璋编的大学课本……我就是靠这样自己学的。
但是好景不长,一年不到,“文革”开始了。我还记得很清楚,最后一次到外语学院去上课,老师说:“看来我们这个课上不下去了。”果然全部停掉了,包括我们中学。文化大革命开始要组织“阶级队伍”,我在学校虽然不是党员,但很受党支部的信任,被算作是左派的。后来我就一直跟着党支部书记,听他的安排做一些整理材料的工作。等到党支部被打倒,书记被斗,没有事情做了,我就去学游泳,也打羽毛球。此外,一次我还在地摊上买到一包拓片条,是颜鲁公的《家庙碑》,就把学校书橱的玻璃拆下来,一块一块放在那里裱起来。当时也不敢随便看什么书,我就去买了一套英文的《毛选》和英文的《毛主席语录》。我住在学校里,有人来查,发现我读的是“毛泽东思想”,就没什么事。那时唯一还可以发行的一本英文杂志是Peking Review(《北京周报》),我也看。我还从淮海路的旧货店买了一个英文打字机,大概是二十年代或三十年代的产品,直到前几年还在给我的学生用。当时一没有什么事干,我就练打字。打字我本来就会,那时候练得更好了。所以后来用电脑,我一开始就能盲打。
一直到“批林批孔”开始,要我写大批判文章,我就趁机把儒家的书堂而皇之地看了。后来扩大了,要“批法反儒”了,说古代的“儒家是反动的,法家是革命的”,那么儒家和法家的书,《韩非子》《荀子》等,我就可以看了,还有当时被划为法家的柳宗元、王夫之、魏源等人的书,也都可以看了。
因为写文章比较快,我慢慢就有点名气了,代写的文章逐步从工宣队到区里。甚至有一次团市委开纪念五四的会,叫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团发言,发言稿也是我帮忙写的。后来越来越多这种文章,都是让我来写的。最高纪录是在毛主席逝世时,我们学校开了一次隆重的追悼大会,会上党支部书记、工宣队队长、教师代表、红卫兵代表……所有人的发言稿,其实都是我一个人写的。那时上海有个写作组,一度要调我到写作组去,说现在要批判教育战线上的修正主义反动路线,最好能找一个有教学经验的、年轻的、文章写得好的人,已经有十年教龄的我是很合适的。工作都移交好了,却又没消息了,其实是别人走后门去了。后来有人跟我说,没去也是好事,要是去了,“文革”结束后都要被审查一段时间的。在写文章的条件下,我看一些书是毫无阻拦的,不管以学习还是批判作为理由,总有理由可以看。
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又有了新的读书机会。当时大概是因为有些高知没有事情做,周恩来总理就让他们翻译一些世界上的历史、地理、人物传记、经典名著等书,比如一些国家的国别史、国别地理、一些二战回忆录、一些历史名人的传记等,翻译出来供干部内部参考。据说周总理提到“中学教师也算干部”,所以,这些书也供应给我们中学了。领这些书需要凭证明到新华书店楼上或后门,不用亲自挑,确认你是什么学校的,就直接递给你扎好的一捆。这些书是先放在我的房间里的,我全部看完之后再给其他人,其实除了我也没有其他人要看。抓住这个机会,我就看了很多这一类的书。其中,因为看书的同时会联系当时的社会现状,《第三帝国兴亡史》这本书让我有非常大的震撼。
那时我的兴趣面很广,对技术、科学这些也很感兴趣,《航空知识》我每期必看,内部的《国外科技动态》我也看。看了之后,如果有些新的东西——国外的科技动态,如一度流行的黑洞、射流、超声波、多晶硅等,看不懂,就问同学们,因为我的同学好多都是理科大学的。其中有一个很好的同学是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我一有不懂的就问他,甚至打电话问,让他把原理告诉我。那时,有什么书看,我就会对什么书感兴趣,因此看了很多书。后来有人问我那时候看书是为了干什么,我就会反问:那时候不看书还能干什么?
另外,我还有一些特殊的经历,虽然不直接涉及读书,但我发现,那些经历对读书也是很有帮助的。在那几年里,我跟社会上各种人、各种事打交道,真实地接触到了社会的各方面。正因为这样,后来我研究古代的人口、制度,一开始就明白一个道理:写在书面的东西都是表面的,背后的东西要仔细体会。后来,别人经常开玩笑跟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什么都知道?”其实我的经验就是这么来的。已经过去了的事情,我们无法再回到古代去调查,但我们可以通过调查现代社会去了解古代,因为很多东西其实是共通的。第一,人性是相通的;第二,古代很多制度以外的东西,在今天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继续存在而已。所以现在,我经常告诉我的研究生,特别是对历史,对古代的东西,真正的懂,不是看懂了文字,而是要看懂文字背后真实的内容。
在社会实践中观察、体会,还要善于对比和联系。如果知道了很多,但不会联系和对比,也是不行的。曾经我到南极去时,别人说:“你是研究历史地理的,跑到南极干什么呢?人类研究南极才两百年……”我说:“一方面,我去南极不是为了学术研究,而是为了增加人生经验;另一方面,如果自己是个有心人,在哪里都可以有所收获。”从南极回来后,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地图上的遗憾》。因为在南极时我发现,那里所有的重要地名都是外国人命名的。这就涉及到地名的由来,跟历史地理还是可以联系起来的,历史不能改变,但未来可以期待。所以,无论做什么事,善于联想和对比,就会有所收获。
(二)自觉地读书
这种不自觉的读书,随着我考取研究生就结束了。一开始听说大学恢复招生,我高兴得很,心想总算盼到了。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一度对上大学已经放弃希望了。仔细一看招生条件,只招工农兵学员,我们教师不属于工农兵,是没有资格的。那时候毛主席还有一些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我作为学文科的,就觉得永远没有希望了。还有两句指示是“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当时我们想不通:怎么我们中学教师也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后来才听说,因为教育体系是资产阶级的,我们这个教师工作就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我想那也没有办法,就把上大学的事完全忘了。
后来恢复高考了,我就马上去报名,但说我年龄超了,规定是30周岁以下,过几个月也不行。正当我处于绝望中的时候,半年以后研究生招生也恢复了,年龄要求是四十周岁以下,我还可以报,而且当时《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表示要“不拘一格降人才”,报考研究生不需要任何文凭,我就报了名,考了试。本来没有寄希望,结果考下来我竟然是历史系所有考生中的第一名,而且遥遥领先于第二名。我觉得,其实是得益于我在那之前乱七八糟看书而歪打正着。因为看英文版《毛泽东语录》,词汇量算比较丰富,外语考了第一;因为在“批林批孔”期间看了很多古文书,古文分数也不低;政治考试就更不在话下了,我一直教政治课,往往什么公报刚发布,我很快就背下来了;……我所有成绩中最低的一门是地理,因为地理我没有学过,只能靠平时乱七八糟看的一点书。
进了大学后我明白,再这样乱七八糟看书是不行的。当时有个同学向别人吹我们是自学成才,我就跟他讲:“人家这样讲是夸我们,但我们自己应该明白,我们最大的毛病就是:知识是不系统的。”我们的导师谭其骧先生也要求我们要认真读书,具体是从1978年开始的,也就是谭先生第一次给我们上课。当时他还在华东医院住院,我们五个研究生到医院去,在医院的门厅里听了第一课,他给我们讲了《汉书·地理志》。因为周围的噪声很大,老师大声讲话很累,所以后来上海辞书出版社在华东医院附近给我们借了一个房间,我们就每次到那里去上课。从那个时候我开始明白:读书,到我们这个年纪、这个阶段,不能再随心所欲了,专业上要根据老师的指导去读,同时再弥补自己知识的缺陷。我所谓的自觉的读书,主要就是根据专业及研究的需要去看。以谭先生跟我们讲的一些找资料的方法、原则为基础,尤其重视一些经典的、学科必读的书,比如《汉书·地理志》,就是谭先生曾跟我们讲的“读多少遍都不嫌多”的一部书。
进入写论文的阶段,我根据谭先生所讲的,凡是跟我论文这个专题有关系的文章都要读。但当时有很多书是我们想看但是国内找不到的。比如,一开始我不知道何炳棣,也不知道何炳棣的书,是在《中国史研究动态》里看到的,王业键教授介绍了何炳棣先生的著作和学术观点。我觉得他的书很重要,但上海没有。之后我到北京去,带着谭先生给我写的介绍信到科学院图书馆去找,结果那里也没有。一直到1985年我去哈佛大学,才找到第一本,第二年又找机会见到了何先生本人。
现在回头看我写的《西汉人口地理》,也就是我的博士论文,感到幸运的是,有些分支的外文书当时看到了,要是没看到就会留下很大的遗憾。中国古书上讲的一些人口现象,其实国际上的那些人口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们已经研究过了。还好当时我们复旦的条件还不错,我也托人找了几部外文书来,把一些该写的现象都写到了;要是没有看那些书,哪怕是看再多中国的史料,我也不会想到要从那个角度去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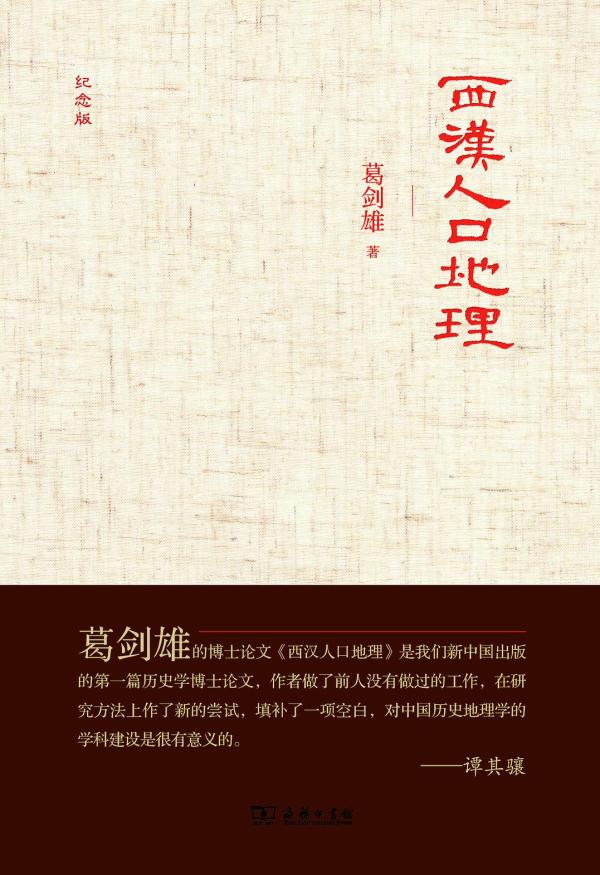
《西汉人口地理》
等到我选择以人口史、移民史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就更加明白:要围绕着自己研究的专题,尽可能把这些书穷尽。也就是说,凡是与你关注的专业或知识领域有关的书,你全部都要看到,非直接有关的,也要千方百计去看。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数据库,所以我在哈佛大学的一年里,就利用哈佛大学的图书馆,把这一方面的书尽量都找到去看。我第一次走到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书库,的确感到很震惊,里面华文的资料相当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各种资料在那里都可以找到,楼上还有丰富的善本,包括很多没有被整理过的稿本。
我们这个专业需要查很多地图,然而很多地图在国内是不让随便查的。谭先生当时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过程中,要到故宫去看一些旧地图,经过了外交部批准,又专门有人介绍进去,结果好多图也还是拿不出来。不同的是,后来我们到美国去,他们竟然还主动问我:“既然您是研究地理,要不要看地图?”他们问我要看什么地图,告诉我也可以自己去找。那时我才发现,美国有好多我们在国内找不到的中国的地图,有些是早期传教士带出去的或者自己画的。
这段时间里,我已经明白,必须控制自己的欲望,限制自己的兴趣点,不然很难完成得了自己的研究。曾经,我见到何炳棣教授的时候,他劝我说:“如果你要真正研究中国史,我劝你先研究世界史。世界史研究得好了,中国史才能研究得好。”何先生的眼光很尖锐,但他的毛病就是,太过自负。他曾跟我讲:“你看,这么多人到外国来留学,都是吃中国饭的……只有我何某人,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西洋史。”在这一点上,我又想到季羡林先生。季先生到德国去学的是梵文,他也觉得,不应该跑到外国来还研究中国,所以鉴于当时德国研究梵文的水平最高,他就在德国研究梵文。听何先生这样劝我,我就跟他讲:“何先生,你的话很有道理,可惜我已经四十岁了,再花时间去研究更多别的也来不及……”现在想想,我的决定是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不顾条件地去追求尽善尽美。我也知道自己研究的面很窄,但为了做好研究我不得不控制范围。
后来还有人跟我讲,应该用英文发表文章,因为用英文发表在国际上的影响会大得多,毕竟看得懂中文的人是少数。我就跟他讲:“这我也知道。但是我用英文写一篇文章可能是我用中文写一篇文章所花时间的好多倍,而且自己还不一定有把握。现在我为了能够使我的研究成就能够快点出来,达到一些目标,我只能先用中文发表。我相信,如果这个成果是有用的,将来自然会有人把它翻译成英文。”所以有一年,我跟剑桥出版社已经签了约,要给他们写一本英文版的《中国历史地理》,我写了一章后就停掉了。因为,一方面我觉得太花费时间了,不如我写了中文的让别人拿去翻译;另一方面,我发现东西方做学问毕竟还是不同的,他们对我写出的那一章也不太满意。他们认为,我应该按照他们的写法去写,也就是写给外国人看,更多的应该是讲故事和事实,但那不是我想写和能写的。
我始终觉得,到这个阶段,适当控制自己的欲望、限制自己的范围,还是对的。我也知道有很多书都值得看,但是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目标里不可能做到这些。所以后来,等我做了图书馆馆长,有人感叹说,觉得我很幸福,有那么多书可以看。我就告诉他,做了图书馆馆长之后,自己就没有再借一本书坐在图书馆里从头看到尾看完过,因为现在的图书馆馆长要管理很多事务。因此,在这第二个阶段,也就是自觉的读书阶段,我认为,我达到了我的目标,虽然只能说是有限的目标。
(三)随心所欲地读书
我在做图书馆馆长的时候,就同时辞去了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研究中心主任以及一些学术委员会里的职务,因为想把主要精力想放在管理好图书馆上。到了这几年,我才开始可以随心所欲地读书——我的读书已经不再跟某一项具体的研究或者某一个努力的目标挂钩了。我真正的幸福,就在这一阶段。我认为,随心所欲地读书,是读书的最高境界。可惜一个人往往要到了退休,到了读书已经没有其他功利目的的时候,才可以这样做。我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自己的兴趣,往往有的书只是简单翻过。但即便是这样,我也觉得很有乐趣。一本书,我喜欢看就看几页,不喜欢就不看,翻到哪里有兴趣就看,可能还没有看完又碰到更好看的,就看其他的去了。
如果你要问:这样的读书有没有收获呢?第一,它增加了人生的乐趣。第二,我看的书既然能让我随心所欲地看,就说明是符合自己的价值观念的;反过来说,如果我不喜欢某一本书,就会去找它的岔子。举个例子,有一本书叫《1421:中国发现世界》,是一个英国的退休军官写的,说郑和发现了非洲好望角,发现了南极,发现了美洲……总之,非常了不得。据说那本书销量超过一百万。那时,有一位伦敦的记者从英国打电话过来想就这本书采访我,我说:“对不起,我不接受。”因为我认为这本书不是学术书,没有必要去骗人。后来这本书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影响也越来越大,有人就劝我一定要说几句话。其实这不是我想看的书,但既然要让我说几句话,那么我就把这本书翻了一遍,发现里面漏洞很多,然后写了一篇评这本书的文章《评〈1421:中国发现世界〉——兼论真实史料的重要性》。我认为,我写的那篇文章到现在都颠扑不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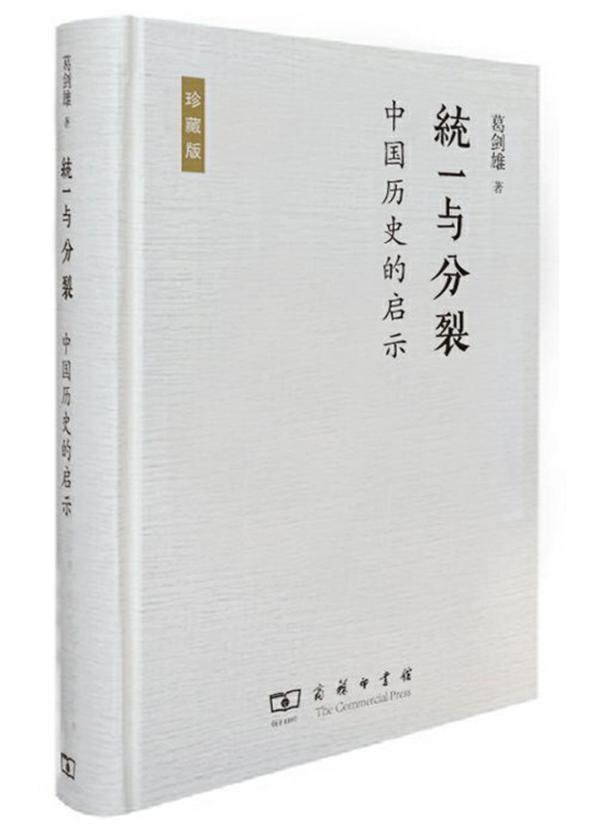
《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
除了到退休之后,其实人生还有一段时间可以这样随心所欲地读书,就是童年时期。像我小时候,就是随心所欲、没有目的地看书,好多书在潜移默化中对我帮助很大。而且人小时候的记忆力特别强,那时候形成的一些概念多少年过去都不会忘记。照这样来看,现在的父母其实应该有一个阶段让孩子随心所欲地去读书,可惜现在的孩子们大多没有这个福气。
二、不同的目的,用不同的方法
经历了这三个读书的阶段下来,我主要的体会就是:我们读书无非有三种目的,不同的目的应该用不同的方法。
第一个目的:求知。为这个目的而读书,要学会选择。
现在的书太多了,即便是同一个学科、同一个分类下,也有很多很多书。我做图书馆馆长的时候了解到,中国每年大概新出五六十万种书,即便扣掉重复的,至少也要有三四十万种新书。有一年我给复旦图书馆采购了十二万种图书,在所有高校中是排第一位的。这么多书,光是编目就要相当长的时间,更别说读了。所谓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在古代可以做到,毕竟古代的学问比较简单,现在是做不到的。古人讲“学富五车”,其实,五个牛车拉的书,到现在一个小U盘都装不满。
以前我们讲“开卷有益”,现在,如果不会自己选择的话,在开卷的条件下你看一辈子都看不完,而且很多东西是对你没有用的。我们现在处于自觉读书阶段的人,什么都是有限的,时间也有限,精力也有限,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里抓住起主要作用的。如果选错了,一方面浪费时间,另一方面有些书你其实是看不懂的。比如对我们历史地理感兴趣的人,你想要找到最合适的书,就要考虑你处于什么阶段。如果是一个中学生对历史地理感兴趣,去看给大学生、研究生看的书,一般是看不懂的。所以,求知识的话,就要学会选择,选择自己需要的,而且要选得细。
自己不会选书怎么办呢?国外很多高校的图书馆都有提供咨询服务的馆员,很多都是有博士学位、双学位的,可以很好地起到学术引领的作用。在国内没有这种服务怎么办呢?一方面在学校里可以问老师,另一方面如果是自学的话,要学会通过目录、索引找到想要的书。
第二,如果到了研究阶段,要去研究问题,这时读书必须学会穷尽。如果不穷尽,可能会做一些无效劳动,也可能无意识地剽窃了别人的成果。
举个例子,如果我要研究上海的历史,那么我就要把跟上海有关的所有书和论文——不仅包括中国人写的,也包括其他各个国家的人写的;不仅包括现代人写的,也包括古代各个朝代的人写的。这些统统都看一遍才能知道,我的研究要做的是什么。所谓研究,必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进步的。如果不看前人的,可能你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东西早就有人做出来了。那么说得好听一点,你是无效劳动;说得不好听一点,你就是剽窃。如果有人说自己穷尽不了,那只能说明你还没有资格做这么大的题目。还是拿研究上海为例,如果说与上海有关的两万种书(随意举例)中你研究阶段最多只能看两百种,那是不行的。怎么办呢?可以缩小题目。比如把题目缩小为“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还可以进一步缩小为“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公共租界”。
如果无法穷尽还勉强要做,是做不出有价值的东西来的。我在写中国移民史的时候,涉及到海外移民的资料,我觉得九十年代在这方面我没有获得这些资料的条件,语言能力也差很远,硬做肯定是做不好的,就把它砍掉了。所以我的中国移民史定了个原则:写向海外移民,就写到他们离开中国出去为止,到外面之后的事就不写了。而且,到外面之后的事属于华侨史,可能已经有人写了,也用不着我来写。所以,知道穷尽不了,就要缩小范围或者改变方向。
现在,有些人说“读书不要太功利”。为什么不能功利呢?其实关键要看你读书所处的阶段。复旦“自由而无用”的精神,指的是人生,人生可以自由而无用,但做研究不能无用。也有些人说要“快乐读书”,但是在做研究上,有些书是很枯燥的,还有些书本身就很沉重,看起来不可能快乐,但为了研究也得看。还有些人说现在是“读图时代”,一定要看有图画或者有视频的资料,这是不对的。一个人真正的本领是一种抽象思维的方式,如果你到了研究阶段、高级求知阶段,还是只能通过形象来思维,是不行的。更不要说,有很多东西是不能通过图画和视频来展现的,只能以抽象的方式表达。
第三,如果是为了人生的乐趣而读书,那么前面两种都不需要,可以随心所欲。
像一些退休的教授,天天跑到复旦图书馆里,很多是常客。他们读书是为了什呢?他们一不为评职称,二不为写论文,三不为评奖,读书就为了乐趣。而且他们的确可以在读书中找到乐趣。我自己这几年也是这样的,已经可以随心所欲地读书了。我看书也没有什么目的,就是为了取得一种身心的快乐,一种精神的满足。这种状态,是符合复旦“自由而无用”这句话的。但是说“无用”,其实也有大用,这个“用”就是自己人生的需求。
在这一点上,我想到了周有光先生。在周有光先生一百一十岁的某一天,我去看他,保姆说周先生还在睡觉。我就疑惑:怎么现在还在睡觉?保姆说,周先生今天中午看电视看的时间长了,才刚刚睡下。保姆让我进去看看,说了一句:“周先生,有人来看你!”周先生回:“我要睡觉,谁都不想见。”他翻个身又睡了。这就是随心所欲。我对保姆说,不要叫醒周先生了,希望不要打扰到他,就只看了看他侧卧的背影,把带来的花放在房间里,回去了。周先生晚年有次与我通电话,讲到他的夫人九十四岁的时候去世了。我刚想讲点什么,他就说:“你不要讲什么宽慰我的话,这是自然规律,她走得很平静,就很好了。”后来又碰到我,他讲:“人能够活到这个岁数,已经很好了。我唯一的担心是,她走了以后,我会不会感到寂寞。现在我发现,我一点都不寂寞。我上午上上网,然后我自己也写一点文章。”他拿出自己用当年别人赠送的第一台电子打印机打印的稿子给我看,说:“你看看有没有价值。”又接着说:“另外呢,你们来,我也跟你们聊聊天。”我又问:“那你还看什么书吗?”他说基本不,有的也看。这就是他已经达到的境界,甚至对生死都想得很超脱。他讲:“上帝把我忘记了。怎么还不叫我回去呢?”我说:“是因为我们要留住你。”
读书到周先生这样的阶段,无论看什么书,从电脑上看也好,或者就听别人讲也好,其实他都把这些当成一种人生的乐趣。这一点,我觉得对我们大家很有意义。因为未来的人,工作的时间会越来越少,人类用来解决物质需求的时间会越来越短,一个国家只需要少数人从事物质生产,就可以有足够的物资和能源。那么人空闲下来干什么呢?不要以为空闲就是人的幸福。挪威人均收入长期都是八万美元以上,位列世界上人民最富裕的前几名,但是挪威的自杀率在发达国家里面是最高的。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太空闲了;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一出生,从摇篮到坟墓都是有保障的。此外,再加上特殊的地理条件,有半年时间是黑夜,人又稀少,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精神生活靠什么来填补呢?一旦再到了行动有所受影响、很多户外活动都不能进行的情况下,又靠什么呢?
所以我想,如果会读书,能读书,那么读书就是我们人的一种基本的幸福的保证。至于读什么书,为了什么目的,在这个阶段已经完全用不着考虑了,可以随心所欲。
三、读书对人生所起的作用
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有一句话说“知识就是力量”。其实,知识可以是正能量,也可以是负能量,还有的知识并不能转化为力量。这句话是激励人去学知识,但并不是真理。一些中小学老师常讲“天才出于勤奋”,也不是绝对的。有的人是天才,却不勤奋,没有发挥出来;但没有与生俱来的天赋,再勤奋也成不了天才。古代还有一句话叫“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但并不是人人都可以通过读书得到这些的。我们还经常听到“读书改变命运”,但读书真的能改变命运吗?也不见得。
那么,读书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呢?
现在,我是这样想的:一个人的人生要想能够成功,能够作出超过一般人的贡献或者说杰出成就,有三个条件——天赋、机遇、个人的努力。
第一个条件是天赋。需要天赋是绝对的,因为天赋是客观存在的,后天条件和努力只能使它得到发挥,而不能改变它。天才是少数,但我们要知道,每个人都有不同方面的天赋。有的人善于动手,有的人口头表达能力强,有的人文章写得好……这些很大程度上就是天赋。
第二个条件是机遇。以我为例,当初我做中学教师需要档案。一个人的档案是从中学毕业开始的,在中学毕业以前必须到你父母的单位去抄他们的档案,弄清楚你的家庭出身,有没有政治问题等。这张纸,加上你自己的学籍卡,就构成你档案的第一部分。档案会一直跟你走,跟着你进入大学或进入社会。在那个时代,如果你出身不好,你的前途就完了。包括后来我考研究生,如果改革开放再晚几年,到我过了四十岁,那么我就是本领再大也不能考研究生了。这些就叫机遇。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都需要一些机遇。所以,一旦机遇到了,一个人就要抓住机遇。
第三个条件是个人的努力,包括读书。今天我主要讲读书,绝不夸大读书。读书不是人生的决定因素。只能说,在个人的努力里,读书(广义的读书)是一个很有效的手段。如果有了天赋和机遇,但到了一定的阶段个人却不努力,也不可能成功。凡是那些杰出的人物,除了前面两个条件之外,在这第三个条件上必须达到完全奉献、甚至信仰的程度,才能够成功。我们可以看看古今中外有名的艺术家、科学家、学者,他们都不是一般的努力,而是到了奉献甚至信仰的程度。
曾经,我在参观米开朗基罗为西斯廷教堂所画的壁画时,有人跟我讲,一般人就是体力也完成不了这样一幅大的壁画。米开朗基罗之所以能够做到,是因为他把这个不止看作艺术品创造,而是作为一种对宗教的信仰,所以才能超常发挥出来。相反,也有一些很杰出的学者半途而废的。他们是天才,也得到了机遇,但达到一定程度的成功之后,就退出或放弃了,最后没有达到本可以达到的境界。
我是研究历史的,而且从初中生教到博士生,前后也教了五十几年的书了。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遇到了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机遇,所以大多数人都算是有机遇的。那么,在机遇和一定的天赋之上,能不能真正成功,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读书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