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进山评《刺猬、狐狸与博士的印痕》|自然科学家的人文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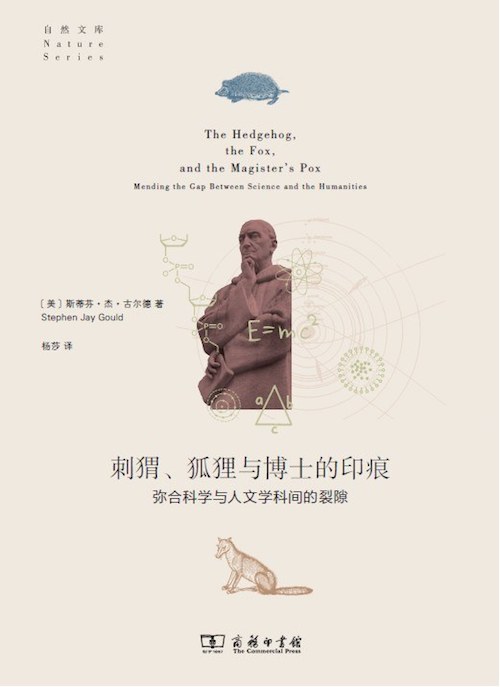
《刺猬、狐狸与博士的印痕:弥合科学与人文学科间的裂隙》,[美]斯蒂芬·杰·古尔德著,杨莎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6月出版,352页,65.00元
由于专业背景和个人爱好的原因,我很幸运地能接触到两位名叫古尔德(Gould)的天才的作品。一位是古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我在学生时代就熟悉他提出的“点断平衡论”这一对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的重要补充理论。另一位钢琴演奏家格伦·古尔德(Glenn Gould),则是巴赫在20世纪的最佳代言人,他弹奏的《哥德堡变奏曲》是我经常欣赏的曲目之一。这里要讲的是关于古生物学家古尔德(下文同)的《刺猬、狐狸与博士的印痕》一书,巧合的是,这本有趣的书似乎也与演奏家格伦·古尔德有丝缕的联系。
古尔德的书我读过的并不算多,但与之前纯粹的关于生物演化的科普读物不同,这本书实际上是谈科学哲学,所讨论的主题涉及一个大问题,即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具体地说,是一个科学家如何借鉴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书中并没有给出相反的过程)。书中简写的“科学”特指自然科学,这或许也因为人文科学研究者通常会被称为文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等等。该书的题目是古尔德风格的一个比喻,既然一切科学都是隐喻,那这书名何必不用呢?
作为一名古生物学科研人员,我希望分享给读者的不需是本书的内容,而是对它们的一些理解与感悟;有些与我的专业背景有关,有些则可能看起来不着边际。除了书中谈到的“方法论”给我的启示外,我也想谈谈科学家的人文精神。
在我好奇古尔德为什么会写这样一本书的同时,我意识到这与他的学术生涯关系密切。古尔德最初学术阶段主要研究腹足动物(如各类蜗牛)化石。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古生物学训练是学院式的,主要目的仍是对新发现化石的系统分类。在当时古生物学还未从博物学完全分离,方法上更接近人文科学。而古尔德恰恰是早期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古生物学的先驱人物之一。随着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古生物学通过整合多学科证据,建立数学模型等等,某种程度已经具备“自然科学”的基本特征,虽然其以“将今论古”作为主要方法论仍不严谨。参与了这一过程的古尔德却从自然科学的发展史中发现了令人不安的现象与趋势。我想这不安可能主要来源于两点,一是科学家对“客观性”的过度自信,二是对“还原论”的过于依赖。
科学家真的很客观吗?
古尔德用大量的篇幅探讨了自然科学发展过程中由弱势到过于强势的必然性。宗教与科学之争以及西方中世纪千年的黑暗时光,我们国人很难有文化代入感。在我周围的“科学与宗教之争”,只能体现在我工作的研究所一个实验室恰恰位于某著名寺庙的山门正下方(共用一堵墙),后来才知道这科学被宗教压在下面的隐喻(又戏称为科学挖宗教的墙角),甚至被顶级学术期刊报道过。我刚上高中时,阅读到《时间简史》的中文初版,它所在的第一推动丛书的命名,也多少有宗教色彩的。有趣的是除了偶尔谈到上帝,物理学家喜欢用“妖”而非“神”来做一些假设,比如笛卡尔妖,麦克斯韦妖,到著名的拉普拉斯妖(甚至动漫中都会提到),这些妖可以做到创世神才能做到的事,让我一度怀疑其客观性。
这里想说的是书中古尔德对宗教的不可知论的态度令我印象深刻。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虽然有些科学家有宗教信仰,但作为重要演化理论的提出者显然应该是无神论者。虽然我个人不是有神论者,但从科学的角度讲,神的概念几乎不能证伪,因为其存在与否的科学认可的证据均无法获得。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我曾碰到过一个化石属,近一百年前最初建立它时只是基于其表面纹饰,现在标本遗失产地不明,理论上无法证明它是无效名。我猜测古尔德也是以科学的理由来表明自己对一这领域不可知态度。
我想引申的是,当一个科学家信誓旦旦地说“我很客观”的同时,其已然陷入主观的囹圄。这会让我想起人们总认为大脑是人体最聪明的器官,然而这个判断是大脑做出的。主观性有的时候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影响着人。以古生物学的一些研究为例,科学家总会将寒冷极区解释为“恶劣的”“不适宜”的环境,这是一种“人类中心”或是“温血动物”视角,事实上这样的环境下有些生物最适宜生活。最“客观的”科学家似乎也无法摆脱集体无意识的影响,论断难免主观色彩。涉及到人的科学更不容易客观,如心理学,甚至双盲实验都无法完全避免人为因素的干扰。书中称古生物学与心理学等为湿软科学,某种程度上我是可以接受的,而从更硬的科学,不论是量子力学中的观察者效应,还是解释宇宙特性及常数的“人择原理”,都更加无法摆脱人的因素的影响。或者更近一步讲,恰恰是发现了人的主观因素的影响,才有这些更为“客观”的理论的产生。
古尔德提到的一个与客观性相关的趣事是我感同身受的。十多年前,我的第一篇SCI论文中,几乎全是被动语态,作者近乎于局外人般的冷漠以显示论文的客观且条理(而非莫尔索眼中的荒谬)。近年来论文的“潮流”却常能看到第一人称的句子,而我自己也在提出重要观点时用第一人称。坦白讲,虽然我并不十分清楚这样做的明确含义,但感觉第一人称的写法读起来更自然,似乎会有助于读者接受你的观点。
还原论越来越没有用吗?
这个问题书中已经给出了明确的否定答复。我的兴趣奇怪地落在书中提到列维·斯特劳斯的名字上,家里书架上正好有他的《结构人类学》一书。古尔德似乎并没有兴趣将它与二分法的起源联系起来。我外行地猜测结构人类学探讨的主题,正是早期人类的二分倾向,或许这是最早的“格致”之学,物格为二以致知。
虽然统一场论或大统一理论还在朝着还原论的方向发展,我也非常认同现在书中所谓的顶层科学已经很难再用这一方法去解决问题,特别是古尔德也提到偶然性问题。复杂系统是非加性或非线性的,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比如蝴蝶效应)导致还原链条的丢失是明显的。近顶层科学几乎全是在讨论复杂系统,其中的偶然性似乎表明“上帝偏爱掷骰子”。以演化生物学对物种灭绝原因的探讨为例,最终的结论集中在一句“坏基因或坏运气”(bad genes or bad luck)上,这显然无法用还原论来解释。类似的,古尔德是从南北战争的偶然性中顿悟到点断平衡论,这看似匪夷所思,但这与他长期思考演化的难题,及积累的古生物学的大量事实难以分割。我想大概这种形式的融通,也促成了古尔德弥合科学与人文科学间裂隙的想法。从我粗浅的对一些人文科学的理解,以及对传统古生物学多年的工作,我感觉还原论失效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人文科学或湿软科学相关概念边界通常不够明晰,导致概念的拆分与综合会有重叠或漏失,在还原过程中的失真被逐渐放大,甚至完全无法还原。

斯蒂芬·杰·古尔德
古尔德的理想与可能的困难
在明确了科学家自身无法完全客观,而还原论又向上失效后,古尔德建议用融通来建立科学与人文科学间的对话,使刺猬与狐狸充分合作以解决科学的难题(看起来似乎对人文科学有些不公平)。有些意外的是古尔德似乎受到了禅宗的感染(考虑到铃木大拙的影响力),他讲到了顿悟的重要性,并把它作为融通的一个方面。这看起来有些不靠谱,但实际上在科学家中也并不罕见。一个卡了很久的想法,一大堆研究了很久的数据,在某一天,甚至可能是在快要绝望时,突然混乱就变为了秩序,这顿悟看起来是来自人文科学一个方法。
古尔德希望通过融通将科学与人文科学聚合起来,取得更大、更富有成果的连贯性,同时强调理解这两个领域对于任何智识上和精神上都“完满”的生命有绝对的必要性。坦白讲,这点很让人受鼓舞和感动,如果不是因为了解荣格的一些工作,我也会认为这一前景非常乐观。我们知道人文科学包括了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是以人为本的学科,这些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差异有目共睹,我想最主要差别之一是情感卷入问题。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科学家通常冷静面对实验对象,对任何看起来好的数据都持怀疑的态度;而艺术家却需要对其作品本身有持续的情感投入。从大脑分工上,科学家用左脑多,而艺术家用右脑多。虽然有些人文学科也多需要左脑(比如历史学),但不同于科学多依赖流体智力,人文科学偏爱晶体智力,这也是为什么科学家的黄金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而人文科学专家则通常晚很多。
分析心理学在当代心理学中已经几乎被遗忘,但它基于大量案例提出的概念和事实却仍有重要的意义。荣格识别出思维与情感,感觉与直觉两对相反的心理类型,他的一个研究发现,科学家以思维型居多,害怕感情的卷入,并认为会干扰自身的思维。而感情几乎是人文科学中核心的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
一个乐观信号是,有些现代科学家似乎与荣格研究揭示的差异明显。希望我的担心完全来自社会刻板印象或荣格的过时研究。我认识的一些科学家都有人文科学爱好,有的甚至近专业水准,既喜欢科学又喜欢艺术的人之所以少,只是一个概率问题。二者兼得何其难也,我多年来看书比较杂,也仅仅能对本专业了解些门道而已。此外,古尔德谈到的顿悟式发现也被许多科学家津津乐道。我甚至想起来,几年前我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合作时,一位老前辈突然很兴奋地做了一个双手推墙的动作,并说他可以开始推动古板块了。
谈一谈科学家的人文精神
一位澳洲的同行曾和我讲,能和我聊起古生物之外的共同兴趣他很开心。他是在谈格伦·古尔德的作品,这位同行的确也很喜欢其演绎的巴赫。我有些遗憾于自己识谱能力有限,然而欣赏巴赫的确给我很多乐趣。我所指的人文精神却并不仅是发展一个业余的兴趣,也不是为了在方法上的融通而去熏染的人文气息。我理解人文精神的核心是那句古希腊箴言“认识你自己”,人文科学因此聚焦于人类自身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而科学家做的事更多是“认识世界”(医学、心理学等也主要是将人当作世界的一部分来认识的)。古尔德不仅仅希望弥合两者之间的裂隙,更希望同时以科学和人文为支柱,支撑起智慧之幕,这显然需要科学家的人文精神。
我们的文化有着先天的优势,曾经有位英国同行向我核实,是否我们能读懂一千年前的中国古书。我非常自豪地答复,公元前的一些书甚至中国的高中生理解起来都不是问题。他非常羡慕又惭愧地说,他们连莎士比亚原著都很难读下来了。然而现实非常可惜的是,很多人(特别是理科学生)在高考之后,就几乎不再碰传统文化。我们文化的人文精神接近于失传,特别是对我们的科学家,更需要重拾人文精神。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很多人听起来感觉教条;格物致知的阳明哲学与现代“求知者”日益增长的物欲看起来也如此不协调。中国自古以来的学问主要关乎人的内心及与万物的和谐,自然科学甚至被认为奇技淫巧而屡遭排斥。而现代的我们却走到了另一极端,造成的后果更甚于古尔德对西方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的局限性。随着教育与科普的发展,多数国人已脱离了传统的“迷信”,然而有不少人又不幸地进入了对科学及科学家的迷信,认为有科学家在,人定胜天。庆幸我们已及时止步,人们了解到有绿水青山在,才会有梦想在,没有让“科技改变生活”变为“算命说知识改变命运”一样的段子。
科学家的人文精神,不仅体现在对自然的敬畏。心理学上有一个“过度理由效应”,根据它的推演,科学家如果只是为了名利而工作,不论他是否得到满足,都不可能全心投入科研活动中。而破解这个效应的唯一办法,就是科学家的人文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讲恰恰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科学家的初心是什么,我相信科学家自己会知道。格物致知并不意味着科学家要格除物欲,过清苦的生活,但纯粹对名与利(如各种帽子及其效应,很多科学家总是倒因为果,帽子本应是水到渠成的结果,而非前进动力)的追求则会让人迷失方向。我也需要强调学科领军人才或科研管理人才的重要性,也从心底里佩服这些人的牺牲精神,比如曾经某位年轻院士非常无奈地讲起他几乎没有做学术的时间,我明显听出伤感的气息。但那些名利导向的“学术权威”,也许在被手拿金枝的后辈取代后,才会发现自己忘了初心而感到失落。
本书尤其推荐给喜欢人文科学的科学家
这本书对多数读者来说可能会有些枯燥,但里面穿插的各种八卦的确有提神醒脑的功效,比如看到爱伦坡写自然科学教科书的原因,以及罗斯福对色彩伪装理论批判的私人信件等时,我得承认可能我的笑点有些非主流。
不像格伦·古尔德的钢琴曲,即便我不怎么识谱也能“附庸风雅”地听进去,特别是他弹的平均律,我猜喜欢数学的人都能听到心里。古尔德的一本专业书却是有些打击到了我——《演化理论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Evolutionary Theory),包涵了他多年来天才的关于演化理论的构想,但因为复杂的书写方式和生僻单词(包括他本人自创的词汇),我最终没能读完,也非常盼望它的中译本。相比而言,当下这本读起来就非常舒心,也许读者会在个别地方觉得晦涩,我能大概想象原文的复句及生僻单词,译者老师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