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数字媒介时代:我们不是迈向更高级的未来,而是更高级的过去
在写作已经出现了几千年之后,阅读依旧是人们关注的对象和争论的主题。人们对阅读的叙述是相互矛盾的,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些叙述体现为人们对于读写能力的祛魅或者对于其未来的担忧,而今,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则进一步发展为更加严重的两极对立。
如今,对于启蒙运动时代的读写能力概念的祛魅常常是通过一种对于数字技术的不加批判的赞美而表达出来的。后麦克卢汉时代的技术主义者对互联网大加赞美,认为它可以颠覆书本所曾经享有的那种令人不快的权威性。一位名叫克雷·舍基(Clay Shirky)的数字媒体专家宣称,人们没有必要为了深度阅读(deep reading)的消亡感到哀伤,因为它原本就是一个骗局。在谈到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的名著《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时,他似乎因为“没有一个人”再会阅读这部小说而感到非常高兴:它“过于冗长并且如此乏味”,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托尔斯泰的经典著作实际上根本不值得他们花费时间去阅读”。舍基所表达的这种民粹主义情绪迎合了当今的时代精神,以至于《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在2010年将他提名为“最顶尖的一百位全球思想家”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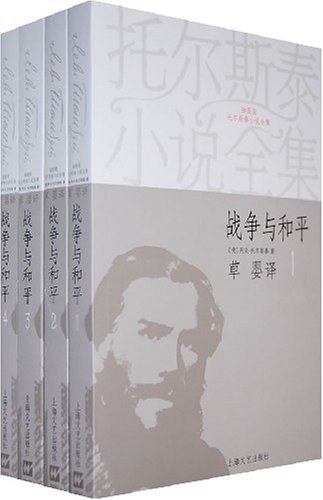
《战争与和平》
当某些人为所谓的古滕堡式印刷文化之死而进行欢呼的时候,那些因为社会正面临读写能力的危机和文学经典的必然衰落而忧心的批评家们则发出了悲叹。有人声称学校没有办法让相当一部分学生学会如何阅读,而这一传言常常会引起人们围绕着谁应为此负责的问题而展开愤怒的相互指责。患有技术恐惧症的人士指责说,互联网的干扰使得人们无法再进行严肃的阅读,而受其影响,关于读写能力正在下降的警告也发展为一种声称严肃阅读正面临空前困难的观点。昔日那些忏悔文学作品的作者们曾经声称自己难以抑制阅读的激情,可是在今天这个容易分心的时代,评论家们常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表明,人们在试图阅读严肃的文学作品时将面临非同寻常的困难。
争论的一方把技术看得如同救世主一般,而争论的另一方则把技术看成罪魁祸首。虽然争论双方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但是他们都把阅读意义和阅读地位的变迁归因于数字媒介的出现。然而历史表明,大多数被他们归因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之影响的事物都曾经是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的人们关注过的主题。关于信息过量、媒介干扰和注意力缺乏等方面的传闻绝不是什么新生事物。那些讨论读者所面临的当代挑战的文章不过是某些流传已久的关于选择过多、信息过量和变化过大的老论调的翻版。一位当代批评家在谈到那种以数字形态进行的泛读时指出:“可供浏览的文本太多了,以至读者们心生敬畏和恐惧,且无力对它们加以辨别,所以读者们往往只是浮光掠影,匆忙地从一个网站跳到下一个网站,而无法让文字引起他们内心的共鸣。”
我们由此得出结论:我们所面临的当代困境并非起因于那些强大的和令人兴奋的新式交流技术,而是由于我们难以决定应该交流什么内容。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阅读不可避免地获得了一种新的意义。
脱离内容
当人们的阅读内容对他们来说变得真正重要的时候,读写能力才能体现出其自身的价值。写作和阅读并不仅仅是交流的技术,而且阅读也不纯粹是一项可以被个人用来解读文本的技巧。读者可以从他们对阅读内容的沉浸式体验中汲取意义,而他们的阅读方式又会受到所处身时代中更为广泛的文化态度的影响——要知道,每个时代流行的学术氛围,以及思想和文本所拥有的对于共同体的意义,都会塑造出某种看待读写能力的文化态度。由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等宗教对文本阅读加以神圣化,所以曾有很多人相信,阅读可以让他们接近真理并更好地理解上帝赐予人类的旨意。宗教改革促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扫盲运动,因为在当时有成千上万的文盲信徒试图阅读那些已经被翻译成母语的《圣经》。识字率的上升同宗教改革的发展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
18世纪的启蒙运动十分重视思想和教育,从而有助于创造一种高度重视阅读的环境。在18世纪的时候,“阅读兴趣”成为一句习语并产生了巨大影响。虽然并不是每一个学习如何阅读的人都会对精致的哲学观点感兴趣,但是在阅读被人们当作一项重大的文化成就而加以赞美的环境下,它成了一种用于增长知识、促进理性和提升审美趣味以及实现自我完善的媒介。学会如何阅读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正如乔纳森·罗斯(Jonathan Rose)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知性生活》(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在19世纪的工人阶级当中,有很多人都学会了如何依靠自身的力量来进行阅读,因为他们相信自我教育的重要性。这些自学成才者为了学习阅读而投入的精力和热情表明,当阅读显得很重要时,人们很容易以读书为乐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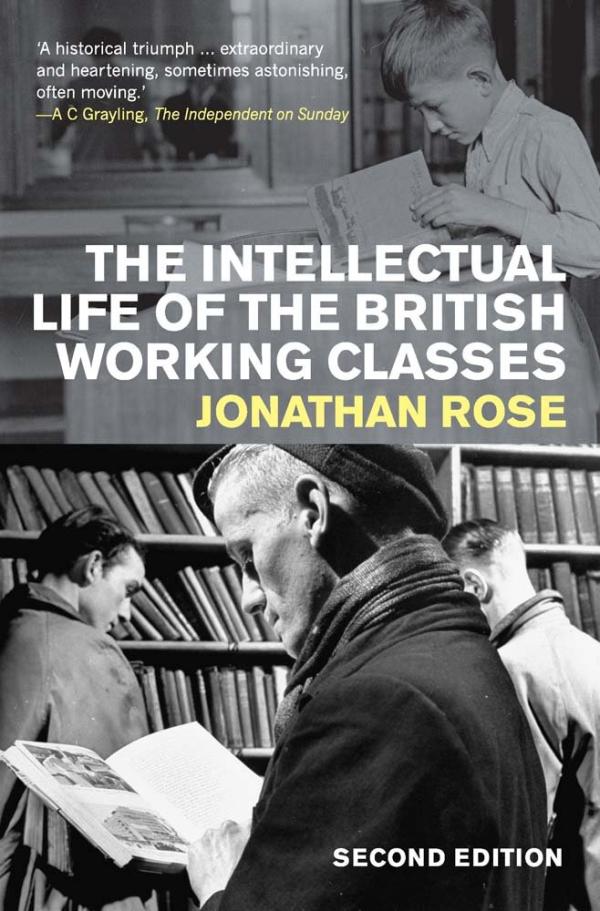
《英国工人阶级的知性生活》
正如我曾在一项关于知性生活的研究中指出的那样,现时代的人们发现自己很难认真地看待思想以及知识的权威性。我们所在的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而不是一个思想的时代。在思想的地位和知识性论断的客观意义得不到重视的背景下,读写能力本身也会被看得无足轻重。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探讨过的那种对于读写能力的袪魅正是这种文化困境的表现之一。它的另一个甚至更令人不安的表现是,人们显然找不到一种适当的语言来表达阅读的价值。读写能力的倡导者常常采用公共卫生运动的倡导者所采用的那种方式来吸引潜在读者的注意力,例如他们常常宣称:阅读可以充当一种有效的压力缓解疗法。
英国教育部于2012年发布了一份用心良苦的报告《关于快乐阅读的研究证据》(Research Evidence on Reading for Pleasure)。这份关于“快乐阅读”的研究报告实际上并未能把阅读的快乐说成是一件具有内在价值的好事。相反,它得出了这样一个不痛不痒的结论:“证据表明,快乐阅读是一种能影响情感和社会的活动”,而且这种活动还意味着“可以为读者赢得更高的评价”。它在陈述快乐阅读的情形时所采用的这种扭扭捏捏的表达方式本身便意味着,在读写教育上出现了某些严重失误。这份报告的作者找不到一套规范性的语言来阐释快乐阅读的意义,可以说,他很难胜任赋予读写能力以意义的艰难使命。
这些倡导阅读的善意人士发现,他们很难找到一种合适的语言来论证自己的理由并让人们注意到阅读对阅读者的变革性影响。他们撰写的倡导阅读的宣传材料中,很少像人文主义者那样强调阅读具有内在的价值;相反,他们把读写能力当作一种可以为读者带来重大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的有用技能。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声称:英国的失业问题同读写能力的低下有关,而且“只要这个国家能采取行动来确保每个孩子都在11岁之前掌握良好的阅读技能”,那么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320亿英镑以上”。
阅读的意义是在阅读主体同文本内容的互动中产生的,这种互动有助于启发读者的灵感或激发读者的情感。在整个历史上,读者的所有感受都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于他们同阅读内容之间的互动。然而,当社会发现赋予内容以意义很困难的时候,又会发生什么呢?
斯文·伯克茨(Sven Birkerts)的《古滕堡哀歌》(The Gutenberg Elegies)一书生动地阐释了阅读这种活动的意义:由于阅读具有形而上的性质,例如它能塑造自我,所以需要按照阅读自身的价值来评价它。他还描写了“印刷文本的稳固地位”如何“被新发明的电路中脉冲的急流取代了”。伯克茨担心,书本丧失权威性将会对“由信仰、价值观和文化愿景所构成的完整体系”造成严重影响,因为“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我们社会的灵魂——都记录在印刷文本之中”。
伯克茨指责电子媒介的兴起及其带来的变革让社会变成了“一个未知的领域”,并且指责数字技术及数字媒介的兴起让“我们的大部分遗产都变成了对我们完全陌生的东西”。绝非只有他一个人认为,社会对于印刷文化的疏离起因于数字技术所带来的革命性影响;在他之外,还有众多的文化评论家和媒体评论家也先入为主地相信,互联网导致了古滕堡时代具有线性思维方式的读者的消亡。他们还声称,那种同启蒙时代的思想有关的理性认知形式已经让位于一种全新的认知形式。那些对后古滕堡时代的到来表示欢迎的人们实际上正在为这种与印刷文化有关的理性形式和知识形式的衰亡而喝彩。
无论互联网导致了何种长期的变革,它都没有直接导致社会对于自身文化遗产的疏离,也没有直接导致那些同读写能力危机有关的问题。正如我们曾经指出的那样,关于阅读危机的讨论早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就已存在,而关于社会同其文化遗产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思考自现代以来便是导致人们陷入长期争论的根源。各种形式的权威都在遭到挑战,以至到了20世纪下半叶的时候,权威一词越来越多地被打上了负面含义的烙印。
在关于21世纪社会发展道路的争论中,这种把文化权威的衰落同新媒体的兴起和影响混为一谈的观点变成了一种流行思潮。一种执着于新技术和新媒体之影响的思想倾向在文化景观中产生了重大影响。麦克卢汉最为系统地阐释了这种技术决定论的观点,他认为真正重要的东西是媒介而不是内容,并且把内容描述为“窃贼手中的一块美味多汁的肉,其用途是干扰和分散‘心灵的看门狗’的注意力”。
然而,假如内容果真只是一种干扰,而媒介才是“信息”,那么阅读内容的相对重要性便成了主观的东西。按照这种观点,在印刷文化中形成并体现出来的内容——知识、智慧和文化遗产——将失去其对于新媒体的权威性。这种观点得到了后古滕堡时代生活方式的支持者们的公开赞同。《卫报》(The Guardian)的主编凯瑟琳·维纳(Katherine Viner)以乐观主义的语气谈到了“长达五百年的由印刷主导信息的时代”的终结:
实际上,数字技术是一次巨大的观念转变、一场社会变革和一颗集束炸弹,它彻底改变了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社会秩序、我们的自我认识方式和生活方式。我们正置身于这一变革之中,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因为离它太近而难以察觉到它。然而,这一影响深远的变革正以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对于技术变革的过分强调不仅会导致对于内容的文化意义的低估,它还表现了一种对于内容的脱离。因此,尽管伯克茨等人对于隐含在内容的主导性地位之中的文化连续性的丧失表示哀叹,但是维纳却兴高采烈。
按照维纳的观点,印刷文本中总是存在某种固定的格式。在古代的苏格拉底看来,阅读文化是不自然的,因此还缺少此前的口传文化所具有的那种纯粹性,而继承了这一偏见的当代批评家们不仅厌恶文本的固定性,而且兴奋地认为,数字技术有可能帮助人们打破固定的文本对于读者的僵化限制。似乎如此一来,印刷文本的人为性特征便可能被一种更具自然性和自发性的阅读态度所超越。
如同其他那些赞同“古滕堡间歇期”(Gutenberg Parenthesis)的人士一样,维纳也预测人类将会回归到印刷技术出现之前的那个更加自然和更具参与性的口传时代。她宣称:“在长达五百年的时间里,知识以固定的形式被保存在印刷文本之中,而且这种形式的知识被人们视为可靠的真理;如今,在迈向后印刷时代的过程中,我们将重新回到此前的时代,即从我们遇到的人们那里听取正确或错误信息的时代。”
假如我们真的像维纳所说的这样,不可能再通过对印刷文本的阅读来接近“可靠的真理”,那么社会所面对的问题将比一场单纯的“读写能力危机”更加严重。阅读的历史总是同寻求意义的活动相关联。而且意义——无论是宗教意义、哲学意义还是科学意义——总是通过提供对真理的洞见来获得自我实现的。阅读一旦丧失了其寻求真理的潜能,便会沦为一种平庸的活动。阅读一旦沦为了工具性的技能,它的作用便会局限于对文本的解读和对信息的获取。在“二战”之后的时代,由技术专家们主导的培养功能性读写能力的学校正是以此种方式来理解阅读的目的,而麦克卢汉所鼓吹的那种脱离内容的阅读观也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由技术专家们主导的培养读写技能的学校同那些反对人文主义阅读观的复古思想结合在一起,再次出现在今天的教育领域中。在学校里,阅读之战的争论双方都未能认真地看待阅读的内容及其文化意义。争论的一方所关心的是如何保证学习的自然性及其同儿童习性之间的关联,而另一方的目的则是指导学生掌握读写的技巧。一旦剥夺了阅读所具有的审美的和知性的内容,阅读教育便可能沦为一种技能培训活动。
回到前古滕堡时代的幻想
那些对印刷文化感到失望的人们相信,数字媒介交流将有助于把读者从静止不变的印刷文本的不自然限制之下解放出来,而且他们把数字技术的发展视为一种同写作的发明一样意义深远的变革。一些评论家对于这一信念做出了最为系统化的表达,他们宣称,古滕堡在1500年左右取得的这项发明开创了一个长达五百年之久的印刷文化时代,而这个时代现在已让位于另一个采用更为自然的交流形式的新时代。
拉尔斯·奥利·索尔伯格(Lars Ole Sauerberg)发明了“古滕堡间歇期”这个术语,来表示一个从文艺复兴晚期直到21世纪初期的历史时期。在这个间歇期——从1500年直到2000年——书籍的印刷出版和批量生产成为西方文化的同义词。索尔伯格认为,随着印刷书籍被一个属于数字媒介的时代吞没,借助文本形式进行传播的知识也发生了改变,进而为那些更能同前现代的口传文化的价值观相协调的交流形式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瓦尔特·翁把这一转变称为第二种口传性,意思是书本时代是一个介于此前的口传传统和今天出现的第二种口传形式之间的过渡阶段。

绘画:古滕堡拿到第一次印刷出的《圣经》场景
这种观点将麦克卢汉对新技术力量的崇拜同某些人对中世纪传统的尊崇结合了起来,并由此把古滕堡时代及其代表的现代主义知识传统视为一个已被超越的阶段。“古滕堡间歇期”的主要提出者之一、丹麦媒体理论家托马斯·佩提特(Thomas Pettitt)不仅认为“我们不是在迈向更高级的未来,而是在迈向更高级的过去”,而且还进一步指出:尽管社会拥有了更为先进的技术,但是“我们正在回归很久之前的状况”。按照他的说法,运用新技术的媒体网络使我们有可能复兴一个具有更多的关联性、群体性和参与性,并具有更少的个人主义的社会。这套理论非常符合19世纪的保守主义者埃德蒙·伯克和费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等人的社会理论。然而,不同于古滕堡间歇期的倡导者,这些19世纪的社会理论家们对于恢复此种社会的可能性持有悲观主义的态度。
佩提特以一种非常愉快而又神秘的语气评论道:
按照正确的拼写方法,“媒介研究”(media studies)一词包含在“中世纪研究”(mediaeval studies)一词之中。对于那些正统的神秘主义者来说,一件事情的意义并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它可以激发你的思考:一个中世纪研究者可以成为一名未来主义者,因为古滕堡间歇期的理论告诉我们,未来是属于中世纪的。
佩提特使用了“恢复”(restoration)一词来表示这种试图回归一个具有更少的理性和更多的自然性的交流形式的主张。另一位热衷数字媒介的人士特伦特·巴特森(Trent Batson)则提出,古滕堡间歇期已经走向了终结,“人类正开始通过互联网而再次认识到知识具有共有(communal)的属性”。在巴特森看来,古滕堡时代是一个畸形的时代——它偏离了此前的那个更为自然的和注重口头参与性的文化——而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属于第二种口传性的时代,该时代将“使我们回归到人类始终保持的交流规范和交流过程”。
这种企图回归中世纪传统的幻想导致了对读写能力及书本的文化权威的贬低,因为它认为,在中世纪的时候,知识的形成和传播是更有参与性和交流性的,而在属于古滕堡间歇期的岁月里,知识的形成和传播则是非自然的。汇集在书本中的客观知识的权威性——实际上也包括一切形式的知识和文化的权威性——都被斥为某种试图建立僵化的和非参与性的等级制的企图,而对于书本的权威性的否定则被说成是一种以解放读者为目标的反等级制的民主化进程的动力。这种对于书本的内容及其权威性的贬低是通过一种为读者争取其应有权力的民粹主义语言表达出来的。
为了避免让人感到自己拥有任何形式上的文化权威,维纳以一种谦虚的口气指出,“我们再也不能像洞察一切和知道一切的记者那样,居高临下地对被动的读者发话”,相反:
数字技术几乎在一夜之间便摧毁了等级制,并创造出一个更加平等的世界;在这个更加平等的世界上,读者可以做出即时的回应,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某些读者对于某个特定主题的了解要胜过新闻记者,并且也更有能力去揭穿谎言。
然而,维纳对读者的奉承并不意味着读者受到了真正的重视。她之所以花言巧语地抹杀读者同作者、记者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为了制造一种文化平等的幻象。当她说读者不再是“单纯的读者”,而是能够参与到职业记者和作者的工作之中的新闻制造者与合作者时,她只是在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来贬低阅读的文化价值,并重申过去那套“被动的阅读不具有任何内在文化价值”的陈词滥调。仅仅就读者可以同网络记者分享某些奇闻逸事而言,被动的和非参与性的读者才被她转变成了主动的和具有文化参与性的公民作者(citizen author)。
按照维纳的想象,在长达五百年的印刷文化时代,读者是一个由没有思想的个人组成的被动群体,并且只能消极地接受“无所不知的记者”(all-knowing journalists)所提供的权威知识。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幻想。成千上万的书籍的被焚、国家的新闻审查制度、官僚机构对于阅读可能产生的政治力量和情感加以限制的企图等等,都表明了阅读曾经是并且依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活动。当维纳要求读者变成合作者的时候,她未能认识到阅读——尤其是严肃的阅读——本身就是一种具有文化价值的活动。
自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于1967年宣布“作者之死”以来,所谓的作者之死便开始被用来宣扬读者地位的上升。然而,为何作者之死——无论是存在意义上的死还是数码意义上的死——具有某种积极的或解放的文化属性呢?无论人们如何看待作者的权威,作者都要为自己的作品负责——常见的那些匿名的且不断变换网页内容的作者除外。读者能够对固定在文本中的观点做出回应并展开争论。同作者旺盛的创造意志打交道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和令人愉快,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这种体验,阅读才具有了引人入胜的魅力。
那些对作者之死感到高兴的人士声称,被解构的文本之中并没有什么不变的意义,因而欢迎各种开放的解释:“确定文本中的意义属于读者的责任和特权。”按照解构主义的观点,“通过处理手头的文本(不仅仅是书本),读者成了意义的权威决定者和真正的作者”。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读者总是作者话语的解释者,而且阅读总会涉及对意义的寻求。然而,在阅读一本书的过程中获得的意义并不同于一个具有内在稳定性的文本中的意义。在阅读一本书的过程中,意义是同寻求真理的活动相结合的;在一个具有内在稳定性的文本中,意义则具有片断性和独断性的特征。
试图解构文本并剥夺书本的权威性,导致了对阅读的前提和文化内涵的质疑。正如伯克茨所评论的那样,这种将读者的想象力从“作者施加的全程引导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的尝试意味着“必然性将被随意性取代”。然而,阅读活动最令人兴奋的和最具转化力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读者进行解释并获得意义的过程中,他们可以学会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并最终做出自己的判断。正如诗人弥尔顿曾指出的那样,读者的力量和真正权威都是通过他们自身的判断力而获得的。意义一旦被当成随意性的东西,便会降低读者通过阅读来发展其判断能力和阐释能力的可能性,从而在事实上剥夺了读者的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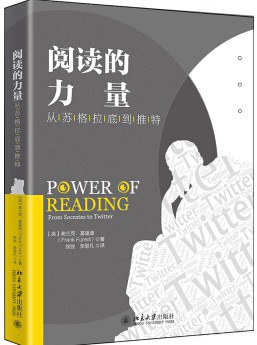
本文摘选自《阅读的力量》([英]弗兰克·富里迪/著,徐弢 李思凡/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版),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