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开放街区|从遛鸟谈“成功老龄化”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空间
在“沿苏州河而行”2021年的试走体验中,我们经过了位于虹口塘沽路和百官街口的昆山公园。虽然因为天气、防疫等原因当时几乎没有人在公园里活动,但有一处功能区吸引了我们的注意——“遛鸟区”。

昆山公园门口的介绍,左边箭头指示处为“遛鸟区”。董怿翎 图

公园里的遛鸟区。董怿翎 图
与一般公园中养鸟人自己找地方挂鸟笼的操作不同,昆山公园的遛鸟区有专门挂鸟笼的设施,可见附近居民有一定的需求。后来,我们重游昆山公园附近,确实在相邻的昆山花园路的老洋房门口看到了悬挂着的鸟笼。

供挂鸟笼的设施。董怿翎 图

邻街昆山花园路上老洋房门口的画眉鸟。董怿翎 图
在当前养猫养狗的人数越来越多的时代,养鸟听上去有些“过时”,城市空间的使用似乎也在印证着社会变迁下人们休闲生活爱好的变化——2020年8月开始,上海市中心已经没有花鸟市场供爱好者淘货或者聚集交流。这不禁让我们思考起城市休闲生活与公共空间以及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
纽约州立大学奥尼昂塔分校( SUNY Oneonta)社会学学院教授梁浩翰于上世纪90年代在香港进行了一项研究,探讨养鸟如何影响老年人的幸福感以及养鸟行为与他们的生活、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关联。近年来,他又关注了过去20多年香港社会快速变化对养鸟行为的影响,并访谈了超过120名养鸟人、鸟市场店主等相关人士。这项最新研究发表于2020年3月的《城市事物杂志》(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根据梁浩翰的观察和梳理,养鸟这一休闲生活爱好在香港逐渐式微主要由四方面原因造成:香港的人口增长及更高效的城市用地需求、非典肺炎和禽流感暴发、地方政府应对疫情的政策、由于内地经济及城镇化快速发展导致蚂蚱等饲料和鸟笼制作等相关手工艺逐渐消失。由于这些原因,传统的“雀仔街”(康乐街)进行搬迁,给养鸟人日常采购带来不便,而他们带鸟上街也不再那么受欢迎。
梁浩翰指出,爱好趋势会由于一系列并行的社会变化而改变,例如城市住房需求、城镇化进程、社会政策、偏好变化,甚至是意想不到的流行病。虽然养鸟绝不是吸引老年人或增进身心健康的唯一可行爱好,但这种传统休闲活动的衰落引起我们思考另一个更广泛的问题:一个社会如何向老年人提供适合其年龄的物质空间,以便其进行必要的休闲活动?
近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就上述问题与梁浩翰进行探讨,以下内容根据采访实录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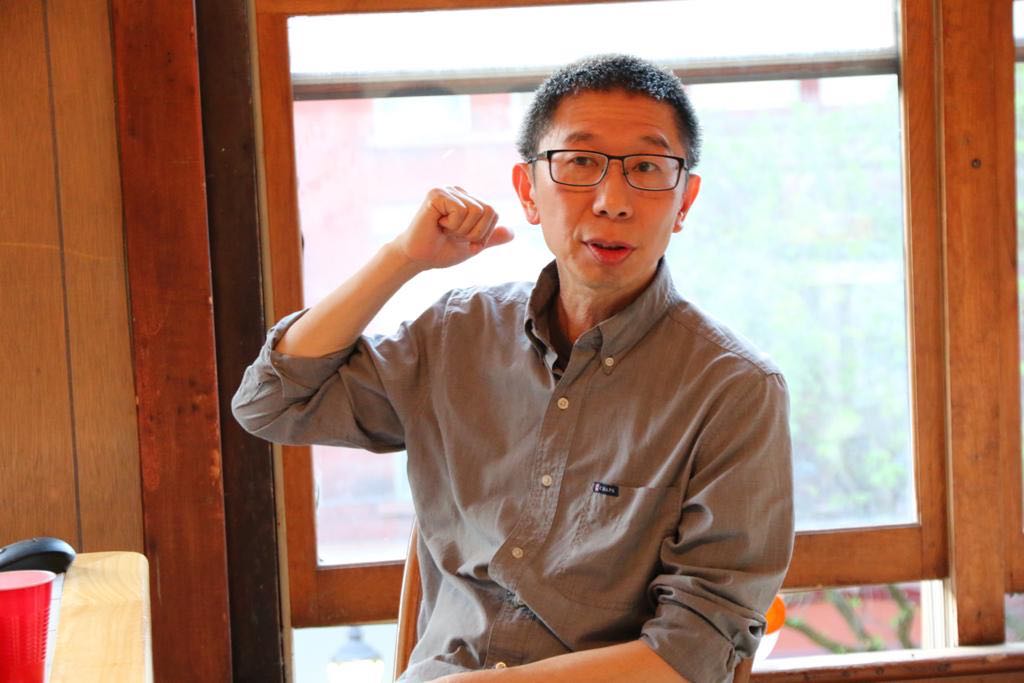
梁浩翰教授
澎湃新闻:您为什么会从养鸟这个角度切入,观察香港老人的休闲生活?
梁浩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居住在香港的公屋。公屋每层都有很多单位和一块公共空间。那时候,有位邻居大伯养了几十笼鸟,每到下午三四点就把鸟拿出来洗,给它们换水、加饲料。我和其他小朋友一样,放学基本没有事情做,就去围观大伯。后来我们自己家也养了一只鸟。
少年时期之后,我就没怎么再注意养鸟的事情,直到在加拿大读社会学硕士期间,我与导师讨论论文题目,提到了以前在香港看到遛鸟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男士,他说这很有趣,然后问我要从什么角度切入。
在老年学中,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假设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会导致老人的经济地位下降。但是,也有学者提出,现代化对老人的影响不一定全为负面,从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等角度可能有积极影响。另外,从文化角度考虑,相较于西方社会,中国传统上更讲究对长者的尊重,因此老人的身份地位也可能有所不同,而不同身份地位的老人受现代化影响的程度也不相同。
基于这些理论,我在暑假期间回香港开展访谈。除了了解受访养鸟人的经济状况外,我也在问卷中探讨他们的家庭关系,从多个维度去看他们的生活,以及养鸟如何影响他们的幸福感(well-being)。
从当时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到,大部分受访者为退休人员,由于退休后经济状况不如从前,不少人放弃了拍照、旅行、看电影、养猫狗等嗜好,转向花费更少的娱乐活动。于是,养鸟成为一种符合需求的选择。有些受访者原本已经在养鸟,也有不少人因为受周围人影响而开始养鸟。
完成硕士论文之后我就没有再继续关注养鸟了,但是对于老人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中。每次我回到香港,看到养鸟文化还在继续。但是逐渐地,城市发生了巨大变化,街头的花鸟市场变身成为豪华旅馆或者商场,原来的市场搬去了更偏远的地方。

2014年,香港九龙旺角园圃街雀鸟花园。梁浩翰 图

2014年,香港养鸟人带鸟一起早茶。允许鸟进入的餐厅已经所剩无几。梁浩翰 图
我也有做城市更新方面的研究,虽然这样的士绅化(gentrification)在许多城市可见,但我发觉这些变化压缩了老人的娱乐空间,对老人有负面的影响,于是我又开始做访谈,也走访了一些旧区,去看以前可以带小鸟进去和喝茶的茶楼,它们都消失了。
时代的变化,加上2003年非典以后鸟类进口受到冲击,整个氛围对于养鸟的老人来说并不友好。所以我决定从城市更新的角度去重新审视养鸟与养鸟老人幸福感的题目。
澎湃新闻:养鸟人是一个多元群体吗?他们是否有一些共有的特点?
梁浩翰:人类养鸟其实并不奇怪,早在农耕社会,人类就开始饲养动物。以前的养鸟人可能比较多元,不同年龄段的人都有,现在越来越单一了。
在我的研究中,养鸟人群大多不是来自富裕家庭,因为这一世代基本都生于二战前,到现在已经七八十岁了,他们没有机会读书。有机会读书的人会有很多其他嗜好,大多不会考虑养鸟,由此看来,养鸟人群的社会经济地位一般不是很高。
从年龄上来看的话,现在年轻人很少养鸟,他们的娱乐选择更多,还有很多家长根本不愿意让小孩养鸟。
而从家庭结构上来看,在香港三代同堂的情况还很普遍,妇人主要负责做家务、照顾孩子,孩子长大以后也有自己的生活,各有各忙,所以丈夫就面临比较冷清的家庭环境,会觉得无聊,想找事做来打发时间,因此他们觉得养鸟是一个很好的社交活动。
鸟要唱歌,也要跟其他鸟聚在一起互相学习,所以要把鸟养好就一定要带它们出去,这就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正面的变化。年龄相仿、背景差不多的爱好者会聚在一起聊天,包括养鸟的心得和生活的其他方面,逐渐形成一个圈子。
澎湃新闻:研究已经证实,饲养宠物对老人至少没有坏处,根据您的观察,养鸟与养猫狗有哪些区别?
梁浩翰:养鸟和养猫狗还是存在一定的区别。首先是环境上的制约,上世纪70年代,香港盖了大量的公屋,占所有住房的约40%,供城市约一半的人口居住,而由于卫生方面的原因,公屋内不允许养猫狗。
其次,养猫狗对人的要求高,需要带它们打针,养狗可能还需要一定的体力,不然遛不动。而且如果遇到下雨天,小鸟不上街是没问题的,小狗还得遛。
但如果从老人对宠物的感情上来说,养猫狗和养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养鸟人和那些小鸟就像朋友一样,有些鸟,比如绣眼鸟,就可以与人互动,你可以用手指跟它玩,它们也会和猫狗一样,对你作出回应。
澎湃新闻:您在论文中提到了华人养鸟与西方人养鸟的差异。在中国,不同地区人们养鸟的主要原因、日常活动或者说在空间使用上是否存在区别?
梁浩翰:从养鸟的爱好本身来说应该没有太大区别,但两地在空间上的安排有一些差异。之前在大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我每年都去内地,有时候也带学生去,每次只要有机会都会带他们到当地的花鸟市场看看。比如在上海植物园,我们看到遛鸟的人很多;一年半前,我跟学生去桂林,那里也还有花鸟市场,但是在香港,这样的市场就越来越少了。

2019年,梁浩翰与Wesley Bernard教授带领22名学生到桂林学习,走访了桂林花鸟市场。Wesley Bernard 图
以前,香港的花市场和鸟市场是分开的,但现在搬迁后的鸟市场就在原来花市场隔壁,大概一条街的距离。政府也有意把这两个市场放在邻近的地方,方便大家走动。另一个鱼市场也在同一街区,但步行距离更远一些。
相对而言,内地的花鸟市场更加复杂,什么都有卖,这可能与传统生意的运作方法有关,因为花鸟市场里的生意大多都与批发有关,香港地方小,很难开辟出足够大的空间容纳所有的货车,所以一开始各市场比较分散,他们本身也有各自所谓的地盘。市场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需求的缩减。
澎湃新闻:根据您的长期观察,城市更新、客观环境因素(公共卫生需求)、家庭需求变化、相关政策、供给变化等因素造成了许多香港老人不得不放弃养鸟的爱好。在您看来,养鸟活动的式微是否不可避免?
梁浩翰:现在在中国,养猫狗是一种潮流,很多人把猫狗当做自己孩子一样。而在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由于气候原因,加上曾经受到非典影响较小、人口密度相对低,还是有很多人养鸟。
养鸟行为本身并不像鸟笼制作那样是一种文化遗产,我们很难做什么去保护它,但如果遇到一些客观因素,城市中心地区花鸟市场需要搬迁的话,可以在公园里开辟一块地方或者开一些店,以满足养鸟人的需求,规模不需要像以前花鸟市场那么大。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每个年代的生活要求或者习惯都在改变。前不久我刚完成了一篇关于大妈跳广场舞的文章,各地政府也制定了一些规则避免广场舞产生噪音给附近居民带来不便,但事实上大妈们会去广场跳舞主要是因为缺少可以使用的空间。
对于管理者来说,更重要的是根据真实需求制定空间在不同时间的使用规则,在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提供不同的资源以满足不同的嗜好,让老年人有所选择。比如,昆明的一个县政府就特意开辟了一块空地将休闲活动规范化,而包括广场舞爱好者在内的使用者都遵守规矩,互相体谅。
澎湃新闻:您提出社会需要思考如何向老年人提供机会和适合其年龄的物质空间,以助他们从事自己喜欢的休闲活动,成功地度过晚年。具体来说,决策者还需要有哪些考量?是否有一些其他国家或城市的经验可以借鉴和参考?
梁浩翰:对老人来说,“在地终老”(aging in place)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因为他们在一个社区住了很久,有熟悉的朋友、店铺,对他们的心理健康有积极影响。在过去五年里进行的一项石库门相关的研究中,我们访问的老先生、老太太都表示自己不愿意搬离原来生活的社区去更远的、陌生的环境。
但现实中,城市中心的老旧区域会因为城市更新项目而改变。虽然现在城市更新以微更新为主,但仍有不少居民已经搬迁去城郊。值得注意的是,在更新项目中,决策者很难完全实现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因为绝大多数更新都以“硬件”改造为主,但由于“人”这种“软件”是充满变化的,因此设施改造之后,人们具体怎样使用设施的效果难以估计。
那我们该如何评估公共空间的质量?事实上就是看它“聚人”的效果,包括空间内的座位、座位的方向、其他配套是否有聚人的条件等。我在社会学课堂上也跟学生一起调研,寻找身边聚人的和不聚人的公共空间的案例,分析什么样的设计才是为人而造。
所以说,虽然有些搬迁是不可避免的,但不管是“在地终老”还是去新的社区度过晚年,公共空间的设计仍然非常关键,首先要让人聚起来,其次就是街道的基层怎么去发展邻里之间的相处,营造良好的邻里关系。
此外,根据老人学中的生命历程(life course)理论,一个人的早期人生会影响其晚年的生活,因此人并不是到60岁才开始终老,从早期开始培养兴趣,懂得怎么去生活很重要。比如现在大家都用手机拍照,但很少有人专注培养拍照的爱好,花时间去研究和思考。像比较简单但系统的摄影入门培训,公共部门可以考虑创造更多大众参与的机会。
至于说在老人休闲生活服务这方面是否有可以参考的经验,我不敢说哪个国家做得更好,但是我自己关注的文献和进行的研究都是多元、跨专业的,很多学者也鼓励更多跨学科的合作。由于不同专业有各自的关注点,研究的内容可能会忽略不同年龄、性别、社会阶层的多元需求,跨学科的合作交流有助于研究者看到问题的复杂性,在解决问题时为决策者提供更全面(holistic)、完整(integrated)的分析参考。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