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为什么必须活得像个男人?建构男性是一个残酷神话
上世纪 90 年代日韩偶像进入中国市场时,男人失去阳刚之气就已经是一些人的心头之患。
《发明男性气概》通过对世界各地的性别文化研究证实,着迷于男性气概的不仅是中国,除了少数例外,可以说是一个准全球性问题。在“结语”部分,大卫·D.吉尔默试图解释大部分社会崇拜男性气概的原因:为了争夺资源或其它整体利益,解剖结构上更适合的男性被夸张地要求展现出极度自信、不畏艰难并具有攻击性。
但建构男性是一个残酷神话。锻造男性气概的过程已经极为痛苦,成为男人还意味着进入一个艰难、充满威胁的世界。吉尔默发现,“男性气概意识形态总是包含着无私慷慨的原则,甚至到了自我牺牲的程度。”因此,我们不应该要求男人必须像个“男人”,而且要拷问,为什么必须“活得像个男人”才能让社会运作下去?
发明男性气概(节选)
撰文:大卫·D.吉尔默
一个男人不能赤条条来又赤条条去,本;一个男人必须做出些什么来!
——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
既然我们已经对大致上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男性扮演活动(manplaying)进行了描述,那么,我们能否回答最初的问题呢?是否存在一种男性气概的深层结构?是否存在一种全球性的男性气概原型?虽然我在开始这项研究时怀疑答案会是肯定的,但是现在我没那么确定了。在回顾了最后两个案例之后,我认为就这个问题而言,没有一个确凿的答案。或许我应该给读者一个“确定的可能”,就像漫画家沃尔特·凯利(Walt Kelly)过去常常针对非常重大的问题所言。
前文的数据证实了不少观点。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社会拥护成就型的男性气概(manhood-of-achievement);其他社会,比如闪迈和塔希提,则满足于让男人们处于放松、被动的状态。我也确定存在男女不分的现象,其他人类学家对此也有所知,我也将很快听闻相关信息。另外,给男性气概施加重重压力的类型似乎更频繁出现。
男性气概在很多社会是一种考验,而且毫无疑问的是,这个统计上的频繁性意味着一些事情。很明显,对男性气概的崇拜与要求男性角色顽强和自律的程度直接相关。或许这种频繁性只是简单地表明了由于大部分地方的生活都是艰辛而高要求的,以及由于其解剖学的构造,男性通常会被赋予“危险的”活计,他们不得不采取行动。男性气概意识形态迫使男性接受剥夺其身份的惩罚,这显然是比死亡还要糟糕的威胁。除非有人能提出存在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男性角色是艰苦的,但是没有男性气概意识形态,否则我们只能总结说,男性气概与男性角色受到的压力直接相关。
其中的因果关系依然是难以厘清的,妄加猜测则是不明智的。然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在男人习惯战斗的地方,男性气概是重要的;在男人习惯逃避的地方,男性气概则不重要。为何大部分社会会选择战斗则在本研究范围之外,但是,原因可能与资源的普遍稀缺性,以及大部分社会的人口难以逃脱至开阔的荒地(如闪迈人那样)有关。

我们可能要对上述结论给出直接推论式的,尽管也是不确定的评论。这关乎对男性气概的需求,而非对男性气概的激励。当然,在某些方面,女性和男性并没有什么不同。女性也必定被迫做出经常是自我牺牲的行为。她们也需要学会自我控制和自律,有时要付出巨大的个人代价。区别在于:女性通常处于男性的控制之下。男性通常行使着政治或法律的权威,因为他们更高大、更强壮,所以如果传统道德无法达到目的,他们通常会用武力或威胁使女性服从。而男性则并非总是在他人的支配下,尤其是在原子化的社会背景下,因此在社会层面上看更难控制。
可能正是因为存在这样一种差异,社会需要一种特殊的道德体系(“真正的男性气概”)以确保男性自愿接受恰当的行为。也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在桑布鲁、安达卢西亚、特鲁克、桑比亚,以及其他男性在其中需要为稀缺资源进行斗争的竞争性的平等主义社会中,男性气概意识形态得到了强调:当形式上的外部限制条件缺席时,内化的规范就必须起到作用,以便确保“表现”。
还有一项观察:像闪迈那样真正中性或男女不分的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相对罕见。这可能指向社会调适的某种进化法则,也即战斗对社会群体而言是一种更成功的生存策略,或某些类似的结论。但是,这些男女不分的文化不只是一道不可改变的法则的例外。我们面对的并非庞大而单一、非此即彼的准则,相反,我们似乎面对着男性形象和准则的连续体,一个变化的刻度范围或一种多变的谱系。
大男子主义代表了刻度上的一个极端。显然,特鲁克、西班牙、桑布鲁、安哈拉(Amhara)、桑比亚,以及其他一些诸如拉吉普特人和美国牛仔的特殊亚群体,都落在这个刻度的大男子主义一端。梅希纳库人、中国人、日本人和现代美国城市人则在刻度中间。或许,对男性气概关注度很低的闪迈人,以及有着玛户的塔希提人,都代表着相反的极端。印度人则拒绝待在一个地方。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男性气概经常会卷入民族主义的或其他的政治运动中,这些运动会暂时性地强化其情感力量。但有时候,顺从于等级制的规则却会妨碍刚毅的男性气质规范,就像在日本和中国那样,由此,情况就愈加复杂了。但我们仍然可以对这种男性气概连续体及其结果得出一些初步的结论。

一方面,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在“真正的”男性气概得到强调的地方,哪怕只是稍加强调,三大道德律令就会频繁得到关注。这种三位一体的诫律呈现出不同的程度,但是足够普遍至表明男性气概是对特定的结构性缺陷和心理缺陷的回应。这些心理缺陷由于劳动的性别分工而得以成型,而劳动性别分工本身也是对环境的调适。
我们首先在地中海地区碰到了这三大律令,在那里它们表现得非常明显。在大部分我们审视的社会中,要成为一个男人,你必须让女人怀孕,保护依附者免于危险,以及为亲属和家人供应食物。因此,虽然可能没有“普遍的男性”,但是,我们也许可以谈及基于这些表现标准的“无处不在的男性”(Ubiquitous Male)。我们可能会把这种准全球性的重要人物称作“男人—授精者—保护者—提供者”(Man-the-Impregnator-Protector-Provider)。显而易见的是,这副三重形象是男性进行角色扮演的标准功能,但是这些论证表明,男性角色或多或少比西方社会养家之人的简单神话要复杂些。
人们期望“真正的”男人驯服自然,以便重建和强化其所在社会基本的亲属关系单位;亦即,通过意志来重新塑造社会秩序并使其永存,从虚无中创造出有价值的东西。男性气概是一种男性的生殖(male procreation);它的英雄主义特质在于其自我引导和自律,在于其绝对的自立——简言之,其行动层面的自主性。攻击性的性态(aggressive sexuality)在这里是重要的,因此不能将这种男性气质说成是纯粹的文化创造,而完全将其与“自然”分开甚至对立起来,就像谢丽·奥特纳(Ortner,1974)的图式——男性/文化,女性/自然。事实要比这更复杂些。
在大多数社会,这三项男性律令要么是危险的,要么是极具竞争性的。它们将男性置于战场、打猎或与同伴的对抗的风险中。因为普遍存在的逃离危险的冲动,我们可以将“真正的”男性气概视为在为稀缺资源而进行的社会争斗中的高效能(high performance)诱因,或一种通过克服内在阻力来推动集体利益的行为准则。在完成其义务的过程中,男人一定会有所失——这是将他们与女人及男孩区别开来的悬在心头上的威胁。他们会失去他们的名誉或他们的生命;然而,如果群体要生存下去、繁荣发展,男人们就必须完成规定的任务。
因为男孩必须让自己刚强起来,以参与这些斗争,所以他们必须经历千锤百炼做好准备。最重要的是,要成为男人,他们必须接受一个事实:他们是可牺牲的。对可牺牲性(expendability)的这种接受构成了他们在各地遭遇的男性姿态的基础;而单单的顺从则无法做到这点。从社会意义上讲,男孩必须对拥有男性气概表现出热情,以及坚忍的决心或者“风度”。他必须公开展现积极的选择,甚至在痛苦中也要欢呼,因为这代表着一种突破万难捍卫社会及其核心价值的道德承诺。因此,男性气概是对幼稚自恋的战胜,后者不仅与成人角色不同,而且与之相对立。

以上所有观点都不是非常新颖:很多作者,既有学院的又有通俗的,此前已经通过使用学术成果或是借助直觉指出了这些观点。不过,男性气概形象与其更为广泛的社会心理含义之间的潜在联系尚未在关于性别的学术文献中有所呈现。
我认为原因之一在于,大多数心理学观察者都是从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角度去解决性别谜团,也就是说,他们聚焦于个体的自我认同或仅仅关注内在过程,没有注意个体行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从性别意识形态是社会事实,是迫使人们以特定的方式行事的集体表象(这些方式常常是约束性的或具有牺牲性的,但是通常会出现存在间接适应性的结构性结果,尤其在男性的例子中,会存在捍卫界限的情形)这样的观点出发,那么我们的看法会略有不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仅可以把男性气概的脚本看作个人强化或心理发展的途径,而且可以将之视为——这一点更重要——让男人融入其所在社会的模式,让其归属一个艰难而且往往充满威胁的世界的一员的准则。
虽然具有象征意味,但男性气概准则似乎是衍生出来的,而非随意生成的。数据显示,生产的社会组织和男性形象的程度之间有着强大的联系。那就是说,男性气概意识形态是对社会环境的调适,而不仅仅是自主的精神投射或放大了的心理幻想。环境越残酷,资源越稀缺,男性气概就越会作为行为动机和目标而得到强调。这种相互关系再清晰、确切和令人信服不过了;虽然它没有证明任何因果关系,但是它的确表明了一种系统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性别意识形态反映了生活的物质条件。要解答起源问题,显然需要进一步研究这样的问题。
为了存续,所有的社会都面临两个基本的正式要求:生产和再生产,也就是经济和生殖。一个群体要想长时间维持下来,人们必须拥有最低数量的孩童,也必须恰当地让他们社会化——这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正如任何一个拥有孩子、了解孩子或记得自己孩童时期的人所知道的那样。与此同时,一个男人必须供养和保护自己的孩子与他们的母亲,否则,孩子及其母亲也要忙着打猎或进行战斗(Friedl,1975)。
出于解剖结构或其他原因,大部分社会中的女性主要负责再生产,而男性负责生产(以及防卫)。在很大程度上,女性和男性的角色都指向复制社会结构,而非通过某种在社会层面中立或微不足道的路径来完成个人的自我实现。社会是一架精妙的永动机,它依赖于其主要结构的复制,尤其是家庭这个结构,因为如果没有家庭,那么就没有了让儿童社会化的语境,进而不会有使文化长存的语境。这要求有足够数量的人做出某种最低限度的牺牲和贡献。
在大多数社会,这一基本的连续性总是受到威胁,无论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它以两种方式遭到威胁:内在方面,是简单熵(simple entropy)的威胁,也就是物质分解成自由的能量、自行“破裂”的过程;外在方面,则遭到大体上人类(和动物)生命中固有的危险(掠夺者、荒野自然、有限的资源)的威胁。正如人类学家们几十年来所辩称的那样,文化是人类调适的工具。文化的道德准则和规范鼓励人们(有时候通过心理的而不是物质的奖惩)在追随他们自己的个人欲望时,也要追求社会目标。这是文化的本领:使个体与群体目标相一致。在这一点上,日本文化是当今工业文明中最显著的代表,但所有依然存在并繁荣着的文化都在不同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

我认为,这样一来,用沃尔特·佩特的话来说,我们可以将男性气概刻画成一种神话虚构,这种虚构使男性的建构(male constructivity)神圣化。其关键门槛在于,男孩所生产的比他消耗的多,给予的比获取的多。男性气概是一面社会屏障,社会必须将其竖立起来以对抗熵、人类敌人、自然的力量、时间,以及所有会危及群体生活的人类弱点。我意识到,这一观点可以从方法论的角度进行批评,因为在反驳一种狭隘的分析个体主义(analytical individualism)时,它几乎滑入了其对立面——方法论整体主义(methodological holism),或者社会中心论(sociocentrism)。
不过,正如史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es,1973),以及近来安东尼·吉登斯(1987)所辩称的那样,完全没有必要认为这些方法是互斥的,并且穷尽了分析上的一切可能性。正如卢克斯(Lukes,1973:117)所言,“就像关于社会现象的事实要依关于个体的事实而定,反之亦然”。而且,我们可以将男性气概观念无处不在的现状视为人类策略的结果,而这些人类策略总的说来在大部分现存环境下都很奏效;于是,那些明显相异的案例,比如塔希提人和闪迈人,变得更加可以理解,而不是更加难以理解了。本书的一个隐含主题是:互惠共生(mutualism),或反馈关系存在于一个社会的物质背景与其意识形态之间,也存在于个体能动性与结构性约束之间,而且在理解“秩序的问题”时,从认识论层面说,作为因果关系并不比协同作用或多重因素的联合作用更有用。
最后,此时此刻,我可能通过引证辩证功能主义(dialectical functionalism)的优点回到我最初的理论陈述。不过,尽管接受了这种多因功能主义(multicausal functionalism),但我认为有人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辩论,说我的观点是“有些”马克思主义式的,而且就马克思主义而言,这也是准功能主义的(quasi-functional)。在我选择来描述我的分析框架的辩证标签中,没有太多与马克思有密切关系,也没有太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论述。虽然我赞成这样的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但是,我更多视它们为问题而非答案——这是一种认识论上的暧昧,当今有很多久经世故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将其看成一个经验问题,认为需要通过经验研究来解释每种情况。
相反,还有一个更微妙的理由让我们可以把这种观点称作马克思主义式的,或者至少是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相符的。这一观点基于一种接近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文化观念。在其社会学杰作《哥达纲领批判》(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1978)中,马克思特别有力地辩称,所有的社会价值都是人类针对自然原料的劳动的成果。我认为,我在此处是支持这种劳动价值论,或者说文化价值的劳动理论的,尽管是经过了修订的。我认为任何持续的社会形成(social formation)都不是一个给定的过程,而是因为其连续性和不断的进展而依赖于一种保持一定水准的工作,依赖于人类不断从自然的变迁中得出秩序和意义的努力。作为一种支持社会价值的组织,文化不过就是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工作:人类的努力,不断地再生使其诞生的种种条件。要让这种工作有价值,它就必须在社会层面上有意义;也就是说,它必须对这种普遍性的建构做出贡献。男性气概的理想迫使男性克服了他们内在的惰性和恐惧,而去“工作”,这既消耗了他们的能量,也显示出了效率和“有用性”。
但是我们也要承认,就像意识形态,工作本身不单独发挥作用;因为就人类劳动而言,身为人类,在文化上也是有条件的。我想给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补充的是一种呼吁,请大家考虑到作为“物质”环境的一部分的文化的方方面面,有表达上的和道德上的,也有经济的和政治方面的。文化的这些方方面面也通过文化人类学家如今所称的“表演”(“performance”,Bauman,1977),或更准确的说法“表演性”[performativity,一如赫茨菲尔德(1985a)在希腊的案例中如此戏剧性地展示的地中海民族的卓越表演]将原因和结果联系了起来。
除了意识形态和环境之外,这种心理学维度还提供了男性气概体系中必要的第三个因素。心理退行是人类劳动的表演性的重大障碍,是对这种表演性的男性建构的主要妨碍;因此,也就有了一种无所不能的、对抗恐惧的男性气质的反应-形成机制(reaction-formation)。退行是一种回到发育的早先状态及逃避现实的趋势。逃离、躲避危险,在母亲身边寻求安慰的愿望可能是人类普遍的倾向。它存在于所有人中,无论男女老少。弗洛伊德将心灵在发展上的“复归”(involution)——退行——看成是所有形式的性格结构和心理功能的一个元素(Freud,1905:208)。在他后来带有形而上沉思性质的作品中,比如《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弗洛伊德甚至将退行提升到驱动力(drive)的本体论层面,后者与他的死亡冲动(death wish)的观念相一致。
对弗洛伊德来说,死亡冲动的恒常目的是退行,也就是从现在的状态回到一个之前存在过的阶段——归根到底就是相当于死亡的生理心理平静(Balint,1968:122)。在临床层面上,安娜·弗洛伊德将退行列于其防御机制的第一位;压抑排在第二位(A.Freud,1936)。她补充道,所有的孩子在受到威胁时都倾向于“退行”,“在共生式的和与母亲的前俄狄浦斯关系中”寻找庇护(A.Freud,1963:139)。这种幼稚的倾向在成年人身上“从未完全缺席”(同上:138)。尽管大部分当代精神分析学家都狭隘地聚焦于退行、阉割焦虑,以及阳具妒羡上,但是他们承认,退行是所有心理过程中一个主要的因素,即便不是唯一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且是所有精神生活的一个“普遍”或“无所不在”的倾向(Arlow and Brenner,1963:16)。
事实上,承认幼稚性的自我复归之重要性催生出了一个完整而全新的精神分析领域,其研究对象是婴儿期自恋(infantile narcissism),就像海因茨·科胡特在关于“双极自体”(bipolar self)的著作中所示,他在这项研究中提供了对弗洛伊德俄狄浦斯情结的另一种解释。根据科胡特的观点,自体的一极源自“母性自体-客体”(maternal self-object),也就是说与母亲共生;另一端则是“承载着具有男性气质的理想的一极”(Kohut,1977:179,206)。于是,在这些科胡特式的术语中,男性气概可以被看成是社会劝诱人们朝着进步的一极成长,并且在成长中用现实原则代替快乐原则,也即要接受工作的责任。因而,对美国式男性气概的攻击的主要途径(至少从不受传统思想束缚的人的来看)是反对锋芒毕露的职业道德也就不足为奇了(Tolson,1977:48;Ochberg,1987)。

沿着这些为具有男性气质的贡献定性的思路,我还得出了另一个观察意见。这个观察可能会让一些更为激进的女性主义者感到意外(甚至愤慨),但我认为数据表明它是真的。当我开始进行本书的研究时,我准备好了再次发现一些陈旧的说法,也即传统的女性气质是养育性的(nurturing)和被动的,男性气质则是自私自利的、自我本位的,以及冷漠无情的。但是我没有找到。我在这里的一项发现是,男性气概意识形态总是包含着无私慷慨的原则,甚至到了自我牺牲的程度。我们一次又一次发现,“真正的”男人是那些付出多于索取的人;他们服务于他人。真正的男人慷慨,甚至能不计前嫌,就像梅希纳库的渔夫、桑布鲁的牧牛人,或桑比亚人或多多斯的“老大哥”那样。“非男人”常常是那些被打上了吝啬、无后烙印的男人。因此,如果我们将男性气概定义为给予的、资助的或利他的,那么它也是一个养育性的概念。这种男性给予区别于女性给予,而且没有那么外露,更加默默无闻,这一点千真万确。
养育的形式也有所不同。女性直接养育他人。她们用自己的身体、乳汁和爱做到这一点。这非常具有牺牲精神,而且慷慨。但令人意外的是,“真正的”男人也养育他人,尽管他们听到这种说法可能会不高兴。他们的支持是间接的,因而不那么容易概念化。男性通过挥洒热血和汗水,提供精子,带食物给家里的孩子和母亲,生孩子,如有必要的话还要前往远方赴死,从而为他的族人提供安全的避风港。在赋予或增加的意义上,这也是养育。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这种男性贡献所必需的个人特质与我们西方人通常认为的养育性人格恰恰相反。为了支撑家庭,男人必须出远门,去打猎或战斗;要变得温柔,他必须足够坚韧以抵御敌人。要变得慷慨,他必须足够自私以积累物资,而这通常是靠打败其他男性获得的;要变得温和,他必须首先要强壮,甚至在面对敌人时残酷无情;要爱,他必须足够有冲劲来求爱,引诱,并“赢得”妻子。关于这一论断,同样重要的是,就其与很多女性主义者所做的工作相联系而言,它通过反驳社会生理学将男性的攻击性视为内在固有的而巩固了其基本论点,因为我在此辩称,男性并非天生就这般迥异于女性,他们也需要变得自信的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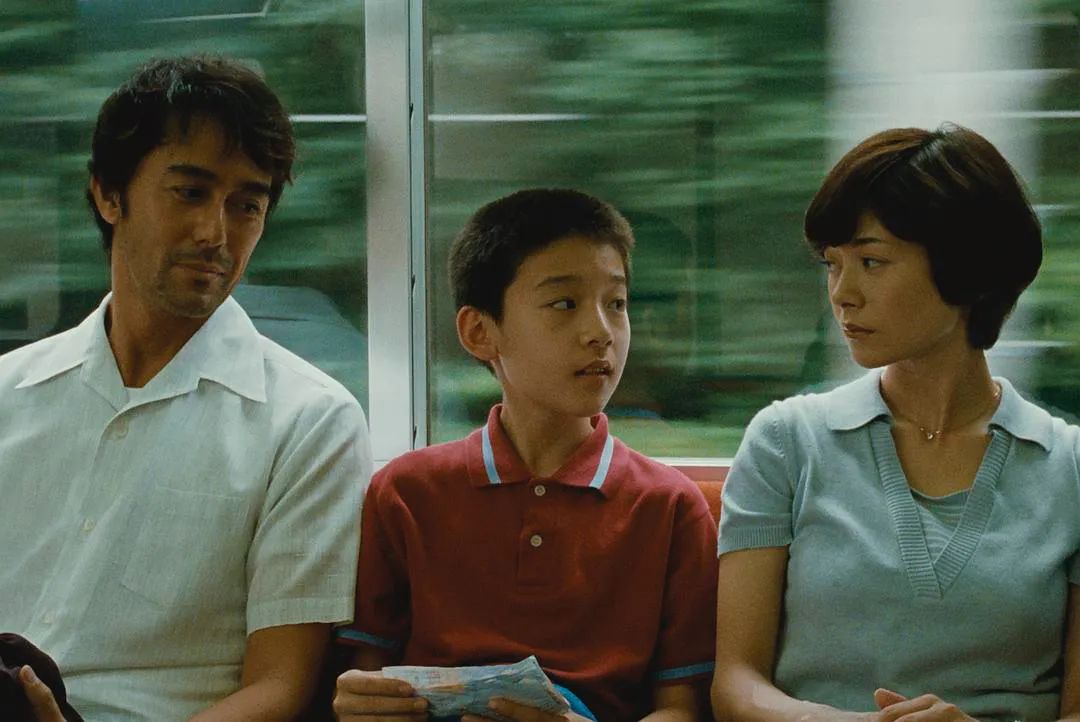
温和的塔希提人和羞怯的闪迈人的例外情形展现出了男性气质的什么方面呢?最重要的是,它们表明,正如我们早先猜测的那样,男性气概是一份象征性的脚本,一种文化建构,变化无常,而且并非总是必要的。这是否意味着正如部分女性主义者和男性解放论者坚称的那样(Blok,1981;Brod,1987),我们西方的男性气质是一场骗局,毫无必要,可有可无?我们是否准备好了将其全悉数抛弃?我们是否都能成为快活的彼得·潘,并全身心投入“自我实现”或“感性”之中,无论这些措辞真正的含义可能是什么?或者在更高的层面上,我们是否都能模仿普鲁斯特,在他软木贴面的房间里写作《追忆似水年华》,将我们的生命用在“婴儿期遗忘”的美丽幻想之中(Kohut,1977:181)?
或者,相反,在我们这个复杂的、相互竞争的世界中是否存在某样东西,它要求我们大部分人遵守男性气概伦理固有的严格纪律?也许存在。但是这样的话我们必须发问,我们究竟为什么必须要有竞争性或要遵守纪律?为什么没有了具有攻击性的带男性气质的性别角色,一个现代工业社会就无以为继、无法发展了?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对具有男性气概的角色的需求?我们能否像闪迈人一样简单地从现代生活固有的挑战中逃离出来?
但这些问题不是我们要回答的,因为我们的角色决定了我们不能从头开始。可能性并不是无止境的。只要还有仗得打,还有战争得赢,还有高度要测量,还有艰难的工作得做,我们中的一些人就不得不“像男人般行动”。那么再问一次,为什么这种律令排除了女性?为什么只有男性被允许成为“真正的男人”,赢得成功克服风险的荣誉?但是我们必须在这里打住,因为这个问题是留给哲学家的,而不是留给社会科学家的。
(本文摘自《发明男性气概》第十章 结语,由浙江大学出版社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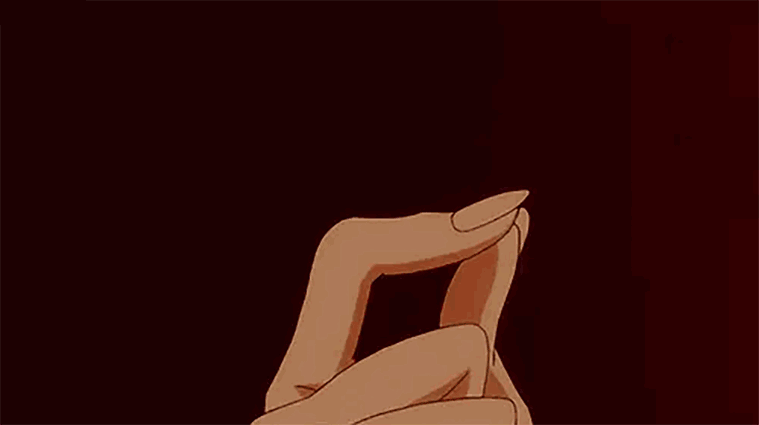
▼阅读解放自己
原标题:《为什么必须活得像个男人 | 单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