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特朗斯特罗姆对游移于日常生活底下的黑暗力量深深着迷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Tomas Tranströmer,1931—2015),1931年出生于斯德哥尔摩。他在大学时期主修心理学,毕业后到韦斯特罗斯(Västerås)成为执业心理学家,在少年监狱辅导受刑人,最后又回到他生长的斯德哥尔摩。他一有空,就跑往斯德哥尔摩群岛的伦马尔(Runmarö)岛,这里有他的许多亲友,让他享受到丰沛且温暖的亲情,可说是他心中真正的家乡。特朗斯特罗姆的诗作融合瑞典自然诗歌的传统与现代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等风格,锻接西方与东方,意象明晰、准确且惊人。他以简洁洗练的文字,生动有力的意象,让想象与创意“如地面之水大量涌进新掘之井”。著有《诗十七首》(17 dikter,1954)、《路上的秘密》(Hemligheter på vägen,1958)、《半成品天堂》(Den halvfärdiga himlen,1962)、《声音与轨迹》(Klanger och spår,1966)、《夜视》(Mörkerseende,1970)、《路径》(Stigar,1973)、《波罗的海》(Östersjöar,1974)、《真理的障碍》(Sanningsbarriären, 1978)、《野蛮的广场》(Det vilda torget,1983)、《给生者和死者》(För levande och döda,1989)、《忧伤贡多拉》(Sorgegondolen,1996)、《巨大的谜》(Denstora gåtan,2004)等诗集。他并非多产的作家,却获奖无数,风格独特的诗作广受世界诗坛瞩目,与他诗作相关的评论、研究,一条一条列下来,至20世纪结束止,已累积成两卷参考书目,厚将近八百页,诗作迄今被译成多达六十多种语言。
诺贝尔奖评审委员、瑞典皇家学院院士马悦然先生是特朗斯特罗姆的好友,20世纪末来台湾花莲时曾告诉我们,特朗斯特罗姆若不是瑞典人,早就得到诺贝尔奖了。2011年,八十岁的特朗斯特罗姆终获诺贝尔桂冠加冕,得奖理由如下:“因为他以密集、透明的意象为我们提供进入现实的新途径。”这迟来的荣耀,于他是实至名归。他的诗看似出奇地冷静,却不时被跳脱联想和情绪的突兀意象打断,可看出他对游移于日常生活底下之黑暗力量深深着迷。他说:“我的诗是汇流点,目的在于将通常被传统语言和观点所割离的不同现实面向做意想不到的联结。乍看像是冲突的事物最后会发展成某种契合。”
在瑞典,他有“鹰鹫诗人”之称,因为他总是能够从制高点以冷静而敏锐的视野观照世界,用意象将幽微的刹那具象化,或将具象的情境抽象化,让大自然或生活周遭的细节相互撞击出奇异的火花。他在第一本诗集《诗十七首》的第一首诗《序曲》里,即已展现出惊人的灵视和精准的语言功力。他将“醒来”比喻成从梦境跃入现实的跳伞,行将睡醒之人是“穿越瞬间”的旅者,以云雀的视角看到了全新的世界:太阳出来了,他自高空向夏天降落,万物充满光热,盘错的树根是摇晃的地底灯火,树木高举手臂站在地面……在他笔下,人人习以为常的醒来的瞬间幻化成兴奋与悬宕不安并存、穿越时空、飞天遁地的奇妙体验。在诗末,诗人语气急转,将读者的想象从一日之初带入一生之终,生与死在瞬间有了交集:死亡,一如醒来,不也是另一次坠入漩涡的速降跳伞?只是届时可会有“巨大的光伞”在我们的头顶张开,让我们安全着地?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似乎暗示我们这些时光旅者对每日的晨醒都要心存感激。
特朗斯特罗姆绝对是意象大师中的大师。他擅长运用简洁、浅白的意象,以明喻和暗喻的手法去呈现生命和情感的诸多面向,仿佛蜘蛛吐丝结网,看似透明无形,实则具有强韧的承载力度。在《记忆注视我》一诗里,他说“绿色住满记忆”,记忆是“纯种的变色蜥蜴”,随时与背景、与田野的颜色融合为一;我们看不见它们,它们的目光却如影随形,再嘈杂的鸟声也无法盖过它们的呼吸声,因为它们已然进驻我们的身体。的确,特朗斯特罗姆的意象有如变色蜥蜴,总是能适切贴合地融入诗作中,不落俗套地传递有效的信息,营造氛围,或传达意念,举重若轻,化有形于无形。“记忆注视我”这个标题后来成为他1993年出版的一本小自传的书名。
他节俭、看似平淡地使用文字,机锋却不时可见,让读者心头为之一震。在他笔下,一棵树“在雨中四处走动”,进行采集生机的任务,雨停后,它静静等待下一场雨水的到来(《树与天空》);一杯纯浓咖啡是“日光下一丁点仁慈的黑”,是不时被灵魂捕获的“一滴滴黑色奥义”,给予生命出发的动力(《Espresso》);对生活乏力而自我放逐的人而言,夜晚无意间停在窗玻璃上的飞蛾是“世界传来的苍白小电报”(《悲歌》);在困顿的人生中,自然是美好的慰藉,夏天的原野是一座“大型机场”,调度员忙着引导冻僵的人自空中降落,向草的“绿经理”报到,生命的寒冬和暖夏如是完成交接仪式(《夏日平野》);冰雪融化,河水泛滥,桥是救命的栏杆,是“飘飞过死亡的一只巨大铁鸟”(《一九六六年雪融时节》);美军大规模轰炸河内和海防地区的越战期间,他是历史的见证者,见证神迹无力赐予希望,人类无法自主命运;是隐形的战争幸存者,为记录人类“大记忆”而存活(《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晚上》);爱是治愈灵魂的药方,让阴郁的生命如萤火虫闪现光芒,让“夜空鸣叫如牛。/我们秘密地自宇宙挤奶,存活下来”,恋人的小宇宙足以击退阴郁的负能量,重新点燃生之欲(《火之书》);幽会后的男士心情愉悦,虽然冬天在两名男女温存时悄然降临,他势必得重回冷峻的现实,但那“超脱痛苦的一个小时”让他相信上帝是存在的,人生还值得活(《C大调》);春日是“长长的兽”,阳光是“透明的龙”,而不断扩建的海滨别墅“骄傲如螃蟹”,大地终有反扑的一日,“倒数计时已开始”(《光涌入》);在异乡,不识中国文字的他成了十足的文盲,身上留存了许多看不懂的购物收据,他觉得自己是“一棵老树,许多不甘落地的枯叶悬挂枝头”(《上海街道》);他将盛宴厅屋顶的水晶枝形吊灯比喻成盘旋天空伺机饱餐腐肉的“玻璃秃鹰”,暗示人类追求名利权势形同走向“喧闹刺耳的死胡同”,一如辉煌的帝国终必极盛而衰,而不居庙堂高位、逍遥在野的银莲花每年春天低调轻盈地绽放,才是大自然为人类开启的“一条通往真正庆典的秘密通道”(《蓝色银莲花》);为了寄出一封内含“密封的真理”的航空信,他穿梭城市之中遍寻邮筒,殊不知“真理就在地上,/却无人敢去拿。/真理就在街上,/无人据为己有”(《航空信》)。这些短诗,文字精练,惊奇连连,知性与感性兼具,细腻的凝视与开阔的视野并存。特朗斯特罗姆试图在充满不确定的现实中捕捉一些可与之抗衡的小确幸,为孤寂忧郁的心灵洒落一些慰藉的火光,也为变调的人世发出温和的慨叹和诚挚的提醒。
三十多年的执业心理学家生涯助他透视人类灵魂与生存困境;二十多年的中风病体教他思索时间的课题,触及幽微的生命层面,更细腻地注视交错于生命中的光和影。他如是描述自己中风后无法行动自如的感受——那是一种“巨大的侮辱”,仿佛孩童时期被人用麻袋套住,动弹不得,只能透过麻袋的网眼,“依稀看到阳光,/听见樱桃树哼唱”,却“无能领受春日的喜悦”(《正如孩童时》);以及想表达却无法言语的困境——“我被我的影子所携,/像一把小提琴/在黑琴盒里。//我唯一想说的/在远不可及处闪烁,/如当铺里的/银子”(《四月与沉默》)。但是,老去的躯体虽是静止不动的爬虫类,老灵魂却可以安静滑行如彗星(《鹰岩》);死亡是黑暗的门槛,人人都得跨过,然而来生是发光的白色文件,人人渴望在上面签名(《签字》);死亡之境是众生终须进入的黑暗森林,我们都是无法抛弃继承权的继承者,但诗人提醒:我们还拥有另一座明亮的生命森林,以及“遗忘大学的毕业证书”,可忘掉生之困顿和遗憾(《牧歌》)。他幽默地把葬礼比喻成市区里频繁设置的交通号志,面对死亡,他不慌张,他会缓缓搭桥,优雅地登天(《雪下着》);他甚至相信永恒是存在的:“骑士与其恋人/化成石头但很开心/在一飞行的棺盖上/超越时间。”(《诗三节》)
1990年11月,将临六十岁的特朗斯特罗姆突患中风,右半身瘫痪,说话能力严重受损。三十多岁时,在《晨鸟》一诗里,他写下这样的字句:“它长大,取代我。/将我推到一边。/将我抛出巢外。/诗作就位。”诗中隐含“肉体萎缩而诗艺成熟”的意念,竟然某种程度预言了他的未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身体的缺憾并未阻挠他的思考能力和创作渴望,1996 年他出版诗集《忧伤贡多拉》,之后他选择讲求文字简练却能激发无限想象的“俳句”诗型,作为修炼诗艺的文学道场。
特朗斯特罗姆在年轻时就对俳句深感兴趣, 一生总共发表了六十五首“俳句诗”(Haikudikter)。1959年,在探访一位在黑尔毕(Hällby)少年监狱工作的心理学家同行之后,他开始写作俳句。2001年,九首“监狱俳句”以书名《监狱》(Fängelse)结集出版。1996年的《忧伤贡多拉》里也有十一首俳句诗。2004年,他出版了另一本写作时间逾四十年的诗集《巨大的谜》,收录了此处译的《鹰岩》至《签字》等五首短诗以及四十五首俳句诗。特朗斯特罗姆的“俳句诗”虽沿用5—7—5 音节数的三行诗型,但他注入现代语法,以自己的方式创新书写内容,探索、实验、开发俳句的可能性。这些三行诗隐喻丰富,有时也建立在抽象概念上,然而不乏我们所叹赏的俳句的特质。这些短诗初始的沉默会自行转化成非比寻常的话语——诗人内在的声音,灵魂的语言。
有批评家将俳句比作一口沉寂的钟,说读者得先学做虔诚的撞钟人,才听得见空灵幽玄的钟声。特朗斯特罗姆《巨大的谜》里的四十五首俳句诗风格多样,他将其分成十一段,每段含一至六首俳句,沉静的表象后面,蕴含饱满的活力与无穷的韵味,带给读者层次丰富的阅读经验。
我们读到诗人以幽默、恬适的笔调传递出俳句特有的闲寂情调,生之野趣、美好,以及人与自然和谐依存的信息。譬如:“在雾中哼唱/一艘渔船在外海:/水上的奖杯”;“你瞧,我静坐/如靠岸的轻舟——/乐啊在这里”;“听见雨的哼唱声/我轻吐出一个秘密/以进入其中”;“山坡上/艳阳下——山羊们/在吃火”;“辉煌的诸城:/歌谣,故事,数学——/样式各异”;“而蓝蓟草,蓝蓟草/乞丐一样/从柏油里窜出”;“灰白色的沉默:/蓝巨人经过,/海上生凉风”……
然而,与生之活力并存的是生之幽暗和难以挣脱的生存困境,时间的威胁,以及死亡的阴影。譬如:“凌迟、折磨人的风/夜里穿过屋子——/魔鬼的名字”;“怪模怪样的松树/在此悲惨的沼泽里:/永远永远……”;“街道被阳光的/皮链牵着走——/有谁在叫喊吗?”;“他写啊写……/胶水流满运河/渡船在冥河上”;“攀爬的影子……/我们迷途于树林中/蔓生的蘑菇间”;“死神弯身向我——/难走的棋局,而他/知道如何破解”。后两首俳句让人联想到瑞典导演伯格曼的两部电影:《野草莓》与《第七封印》。
虚实交错的生命光影中,诗人为读者捕捉住某些神秘的灵视,奇异的镜像,带领我们往返于熟悉的日常以及无法确知却又无法否定的未知世界之间。譬如:“奇妙的森林,/上帝身无分文住进——/墙壁发亮”;“草升起——/他的脸,一块刻着古文字的/碑石,竖立于记忆中”;“突出的岩壁上/隐隐有裂缝通向魔窟——/梦想的冰山”;“屋顶裂开:/死人看见我——/这张脸”;“海是一面墙——/我听见海鸥的叫声/它们向我们示意”……第十段第二首“有事发生。/月光满室。/神知道” 诚然是一首谜一般妙不可言之诗:“有事发生”,发生了什么神妙之事?神之外,大概只有在满室月光中让“某事发生”的恋人们知道了。
特朗斯特罗姆擅长使用意象,以具体的事物传达抽象的意念。他以“没有脸孔的鸽子”隐含和平的不确定性(第一段第二首);他将褐黄的叶子和隐埋千年后出土的古老《圣经》抄本相提并论:“褐黄的叶子/珍贵一如/《死海古卷》”——一方面将自然神圣化(虽不忘指陈其易逝、脆弱之本质),一方面借“重新出土”之意念,提醒我们用新的眼光观看习以为常的周遭事物,从中领受新的意义或趣味。
这四十五首俳句诗的倒数第二首如是说,“风自海洋图书馆吹来/强而缓——/我在此安歇”。特朗斯特罗姆这些诗本身就是海陆、生死、天人两栖的海滨图书馆,在其缓而不减其力的俳风吹拂下,作为读者的我们漫步、安歇,思索“鸟人”与“开花的苹果树”之间“巨大的谜”。
特朗斯特罗姆诗的英译者、苏格兰诗人傅尔顿(Robin Fulton)在谈到广受世界各地读者喜爱的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时,曾说:“很难用任何简单或概括性的言辞去解读这广泛的吸引力。有些读者说他的诗平易近人,的确如此——但只说对了一半——在看似平易的表层之下存在着黑暗的水流,他晚期的某些诗作像谜般神秘难解。另一些读者赞叹他的诗即便反复阅读也能让人觉得惊喜,仿佛它们永远‘取之不尽’。又有另一些读者对其隐喻着迷,这些隐喻未必以全新的视角引我们观看日常事物,但每每让我们自其中发现先前未曾察觉的一些东西。”的确,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有时静美如溪,有时壮阔如海,不但耐读,而且每次阅读,都可能读出不同的外在与内在的风景。
特朗斯特罗姆于2015年3月26日病逝于瑞典斯德哥尔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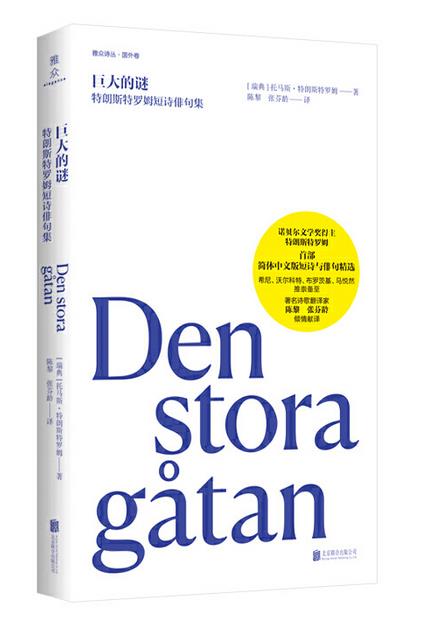
本文为《巨大的谜:特朗斯特罗姆短诗俳句集》([瑞典]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 著,陈黎、张芬龄译,雅众文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12月)一书译序,原题为《巨大的谜——阅读特朗斯特罗姆的短诗、俳句》由澎湃新闻经雅众文化授权发布。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