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追念我们共同尊敬的长辈、熟悉的朋友沈昌文先生
【编者按】
2021年1月10日,著名出版人沈昌文先生去世。1月18日,由澎湃新闻·上海书评、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和草鹭文化公司主办的沈昌文先生追思会,在上海的朵云书院·戏剧店举办。追思会由陆灏主持,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葛兆光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戴燕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汪涌豪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江晓原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荣休教授陈子善,上海巴金故居副馆长周立民,著名作家、上海市作协副主席孙甘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王为松,真格基金创办人、草鹭文化董事长王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前董事长陈昕等学者、作家、出版人、媒体人,以及沈昌文先生的侄外孙女沈锴等出席。以下为部分嘉宾的发言整理。

追思会现场
陆灏:我们今天在这里追念一位刚刚去世的共同尊敬的长辈、熟悉的朋友沈昌文先生。
前年(2019年)夏天,沈公最后一次来上海,在上海书展参加了《八八沈公》的新书发布活动。那天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不忘初心,上海就是我的初心。”我们知道,沈公是1951年3月份从上海去北京人民出版社工作的,他在上海生活了近20年。他早年艰辛而丰富多彩的生活,我们平时听他讲和看他的书都了解得非常多。1949年6月,上海刚刚解放,沈公考入了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采访系,后来他在回忆文章里说,正是因为他进了民治专科学校采访系,“这以后也就跟文科、跟文化、跟新闻出版业务搭界了”。当年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就在我们今天这家书店所在的长乐路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家书店缅怀沈公,不仅是他的初心所在,也是他辉煌的出版生涯的初始点,所以特别有意义。
首先,我大概汇报一下沈公最后的情况。因为在沈公去世以后,媒体的报道说他是在睡眠中安详去世,这个没错,但是并不是无疾而终。我们记得前年夏天沈公来上海的时候,这里大多数的朋友都跟沈公见了面,那时候他虽然耳朵不好,但是身体还是很硬朗,思路也很清晰。那年秋天我又去北京参加了《八八沈公》的宣传活动,在前门Page One书店,我当时看到他拿出了讲稿,写得很多,但他从头到尾没有看讲稿,一直拿在手里,没看,而讲得很风趣,很得体。那天晚上我们一些朋友在北京的徽商故里——沈公比较喜欢去的一个饭店,里面有臭鳜鱼——给他和白大夫祝寿。那天晚上欢声笑语,但是没有想到这是我跟沈公的最后一次见面。
去年一年的疫情,对喜欢社交、喜欢热闹的沈公来说肯定影响很大。经常请沈公出去吃饭的俞晓群也没办法找沈公了。我过一段时间跟他的女儿沈懿联系一下,了解沈公的情况。她说他还可以,每天在家就是上网弄电脑,已经搞坏了三台电脑。去年书展,他没有能来。三联书店的副总编郑勇来,跟我说9月26日是沈公的生日,三联书店想给他搞一个祝寿活动,让我到时候过去。但后来9月份没有举办,一直到10月16日三联书店给他搞了一个祝寿宴,范围很小,就是三联书店的领导加上赵珩、扬之水等几个熟人参加。他们传了照片给我,那个时候照片上老沈就瘦得非常厉害,我说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他们说不只是瘦,脚还肿,有腹水,可能是有病。听郑勇说他们去接他的时候是一辆商务车,他的脚就抬不起来,后来送他回去的时候,换了一辆低一点的车他才能上车。
那天饭后过了一两天他们就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检查出来说是肝癌晚期。沈懿说他住院三天吵了三天要出来,后来很快就出院了,出来的时候看到他照片又很神气了,俞晓群他们还请他出来吃过饭。沈懿告诉我,确诊是肝癌晚期,但并不是最末期,生活完全自理,他们每个星期带他到外面去吃顿饭,还可以,还每天上网,晚上还做点简报扫描之类的事情……
元旦过后,更虚弱一点。一直到1月9日,那天是星期六,沈懿说他有点糊涂,像微醺状态,沈懿用按摩器给他敲背,他摇头晃脑好像很舒服的样子。那晚沈懿就留在了沈公那里住,半夜看看他情况还蛮好,呼吸平稳,但到早晨6点钟去看,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体温还在,所以她赶快打120。120过来说已经去世了,可能是6点多刚刚去世。我们大家熟悉的、喜欢热闹、喜欢胡说八道、风趣幽默的沈公就此永远离开了我们。
离开了。沈公的家人本来也不准备任何的仪式,但是三联书店讨论下来,沈公在出版界的影响那么大,而且那么多人也想去送送沈公,所以他们还是觉得应在八宝山举办一个告别仪式。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发的讣告里面就说,限制五十个人,但是14日上午的告别仪式,据说还是去了两百多人。
沈公去世了以后,纸媒和网络对沈公的报道纪念非常隆重,澎湃新闻不仅做了系列报道,还全程直播了告别仪式。尊重家属的要求,直播没有进入告别厅,在院子里采访了一些参加告别仪式的沈公的朋友。沈公一生喜欢热闹,最后走得那么风光,他自己应该是蛮开心的。
在沈公去世之后,郑勇委托我和扬之水、王为松拟了一副挽联,就是大家看到的三联印的沈公简历后面的那副:“读书无禁区,宽容有情有爱,终圆书商旧梦;知道有师承,溯往无雨无晴,俱是阁楼人语。”用沈公出版的书和他自己著述的书名串起,上联写他在出版事业上的成就,是作为一个书商的成就,下联是他作为一个作者后来写了那么多书,给我们留下的东西。上联的最后一句,原来是“难圆书商旧梦”,后来给吴彬看,她说改成“终圆书商旧梦”,这样比较正面一点。我们觉得非常好。老沈一生轰轰烈烈,创造了那么多辉煌,又高寿,潇洒离去几乎没有痛苦,应该是功德圆满了。
沈公给我们读者留下最大的影响是他主编的《读书》杂志,前两天有人问我,当年《读书》对我的影响,现在回顾,我所知道的老一辈作者、年轻的学者,几乎有百分之八十是通过读了他们在《读书》上的文章才知道的,包括金克木、张中行、黄裳、谷林、吕叔湘、陈原等等;稍微年轻一辈的学人,也几乎是从《读书》上最早了解的,包括今天在座的葛兆光先生,我也是读了他在《读书》上的文章才认识他,1990年代以后去北京,跟葛先生的见面,几乎都是在老沈组织的饭局或者座谈上。作为一名《读书》的骨干作者,跟沈公有那么多年的交往,我们就请葛先生先说两句吧。
葛兆光:今天来谈老沈——我们平常都叫他老沈——其实也有点怀旧的感觉。因为我大概是1986年认识老沈的,也就从1986年开始成为《读书》的作者。大概估计一下,可能在《读书》上写了有40多篇文章,不算太少。但是我是一个没有故事的人,老沈是属于有故事的人,所以我在这儿只能讲一讲老沈在当《读书》主编的那个时代,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1980年代——我说的这个1980年代其实一直到1995年。我一直在想,我们今天来谈老沈,怀念老沈,实际上某种意义来说是怀念一个时代。
我记得以前李泽厚曾经讲过一段话,很多人引用,说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区别是思想家和学问家的不同时代,1990年代就成了学问家上天、思想家落地的时代。我一直不同意这个说法。1995年以前,还是老沈在主持《读书》工作,那时候发表了很多关于陈寅恪、王国维、胡适等的文章,实际上还是在通过学术在讲思想,并不是什么学问家上天、思想家落地。我记得那时候我跟老沈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太多讨论,因为我更熟悉的是吴彬,吴彬的先生曾经是我的一个同事,是编《中国文化》的两个编辑之一,所以我的很多稿子基本上都是通过吴彬拿到《读书》上的。
虽然每次见到老沈,都有一点跟他没大没小地开玩笑,但是我跟老沈其实没有那么熟。我这个性格跟老沈好像有一点不大能擦出火花来,因为老沈是一个嘻笑怒骂的人,我是一个可能过于学院式的人。但是我跟《读书》确实有非常多的交集和往来,所以我想老沈当初开创了中国编辑界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一个没有自己专业、没有自己特定立场、没有特别固执角度的人,也许在那个时代当一个杂志的主编恰恰能够开出一个百花齐放、自由争鸣的杂志。我想老沈最大的作用就是他没有自己的偏见,这是他最大的好处。
陆灏:葛先生说跟老沈没有什么故事,我记得九十年代初有一次他们在华侨饭店讨论一个什么评奖活动,正好我在北京,老沈让我一起过去,有葛兆光,好像还有赵一凡等。讨论请谁当评委主席,老沈突发奇想,说我们这次能不能请金先生出来当。我记得很清楚,葛先生一边摇头一边说:“镇不住镇不住。”最后还是决定请季羡林先生。这个评奖活动后来好像没搞成,但葛先生的这个“镇不住”我印象很深。
陈昕:沈公的成就这两天已经有很多的人从不同的角度谈了,我自己也在两年前沈公米寿之时,写过《智者沈公》一文,谈了与沈公接触的往事。今天在这里追思沈公,我想谈谈沈公最令我钦佩的一点,那就是在错综复杂的环境里,冲破重重阻力,想方设法出版好书、办好杂志,为社会进步作奉献的本事和智慧。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沧海横流”的时代,新的思想,新的潮流,新的学派,新的学科,恰如千重细浪,滚滚而来。然而,要把这些新思想、新潮流介绍给读者又谈何容易,我在八十年代初中期策划编辑出版黄皮书——“当代学术思潮”时深有感触。沈公与众不同,他主要采取的是“向后看”的策略,跳过某些当代敏感的领域,翻译出版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重要著作。据他自己说,这是从李慎之先生处受到的启发。于是就有了《宽容》《异端的权利》《情爱论》等风靡一时的著作的出版,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让大家补足了人类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其实不了解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方思想,是很难真正理解当代学术思潮的。
《读书》杂志在八九十年代的十年间,之所以能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呼应时代的改革开放主题,团结老中青,包容左中右,推出那么多有思想有创见的文章,也与主编沈公尊重表达的自由,文前文中文后的编辑处理相关,他总是把那么敏感的话题消弭在硝烟之间,让读者得到启蒙。他还常给我们讲怎样做检讨写检查的故事,为的是让更多的好书和文章与读者见面。他就是有这样的本事,把一本有着争议的杂志,办成让知识界喜欢、领导也觉得有必要存在的充满浓郁人文气息的刊物,以至在《读书》最困难的时候,连乔木同志都出来,通过投稿的方式以解其困境。
沈公的这个本事不是简单地通过学习便可获得的,他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体验、人生体验。不过沈公另一点本事是可以学到的,那就是广交学界朋友,借用外脑。八十年代初期,新三联的人文风格在我看来,是沈公从陈原先生一辈那里继承下来的,而夏衍、吕叔湘、钱锺书、金克木、黎澍、李慎之等那么多文化名人支撑着《读书》和三联,他们笔端下流淌的人文气息成就了三联。八十年中期以后,甘阳、梁治平、周国平、苏国勋、汪晖、黄平等一大批青年学人聚集三联的大旗之下,提升了《读书》和三联出版物的现代学术思想水准。沈公在其中是一个重要的支点,他的组织才能、包容态度和不耻下问,以及各种各样服务作者的办法,使三联获得了不竭的文化资源。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不耻下问的出版人,八九十年代每次到京看见沈公,他总要放下身段,向我这个毛头小伙编辑了解经济学界的方方面面,更不要说他面对名家大腕时的姿态了。有了这样虚心求教的态度,还会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吗?
沈公作为一个别具一格的出版人,永远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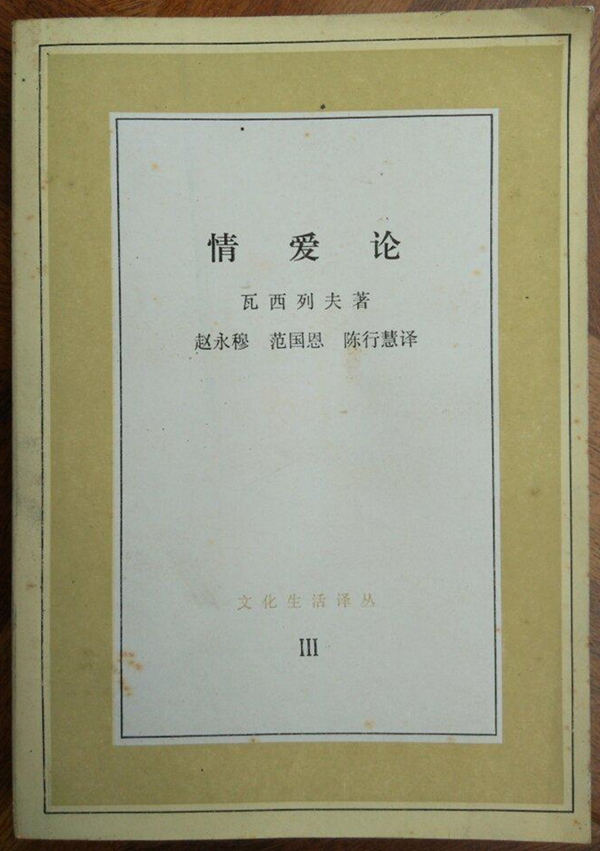
《情爱论》,1984年

《宽容》,198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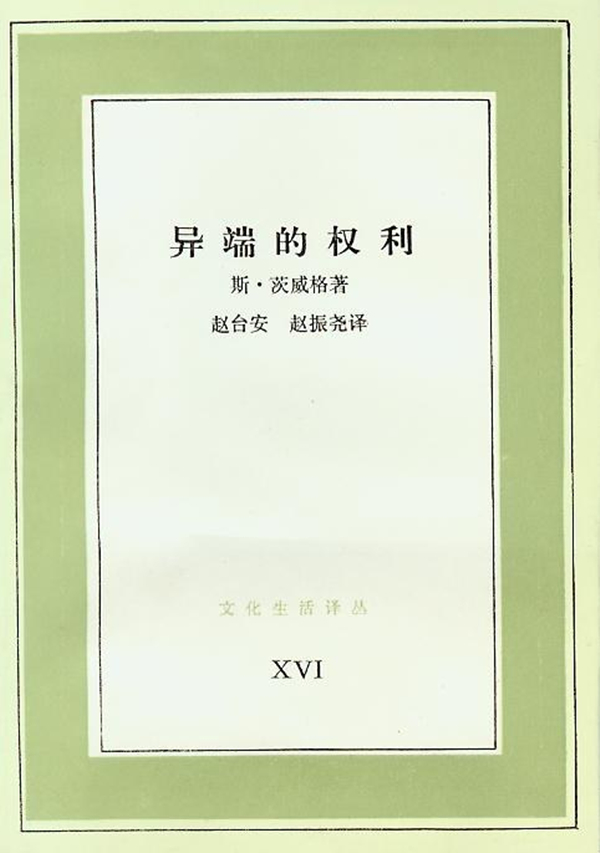
《异端的权利》,1986年
陈子善:刚才大家都讲到沈公对《读书》的杰出贡献,我就想到1990年代俞晓群跟沈公第一次成功合作“新世纪万有文库”也有很多读者,这个书印得很普及了,价钱很便宜,很多人都从这个书进一步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西方文化,这个也值得特别提出来。我也参加一部分工作,接下来的海豚书馆我也参加了一部分工作,老沈都是灵魂人物,具体执行的是俞晓群跟陆灏。老沈的眼光很远大,在他退休以后他的天地更广阔。还应该要提到,他联系中国的香港、台湾,还有美国的很多出版家、作者,金庸是他引进的,蔡志忠也是,都是很了不起的。
在网上看到胡洪侠拟的一副对联,我说我不会拟联,我就八个字:何止知道,真正宽容。他是真的宽容。他接触的人各种各样,有的都不能发表文章的,但是老沈还是欣赏,真正宽容。
王为松:我跟沈公真正有接触很晚,但我进出版界就早闻大名。沈公跟我们上海人民社还真有关系,他自己讲过好多次,1951年3月份上海人民出版社招聘,他来应聘被录取。但他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时间并不长,就调到北京去了。后来我看他的简历里面说是人民出版社委托上海代为招聘,这样算的话,他说他也应该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员工。2007年,在上海书店的海上文库里面,我们出了他两本书,就是《书商的旧梦》和《最后的晚餐》,2011年,我们又把两本合起来出了一本《任时光匆匆流去》,作为给他八十岁生日的贺礼,沈公讲非常喜欢听邓丽君的这首歌。
我虽然很晚才见到沈公,但是对我来说,我们并不陌生,或者说,他是我的一位陌生的熟人。因为关于他的传奇和流言,我早有所耳闻。况且,他主持出版的那些书,我读大学的时候就见一本买一本,至今仍摆在我的书架显眼处。我入行后也一直把能够做几本像这样的书作为自己的目标,希望自己像沈公等前辈一样,做一些能流传下来、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书。但是我很快发现,老一辈做人做事的风范,我们这一代是学不到的。上次范用先生的展览在上海举行,我有幸听董秀玉、汪家明两位前辈讲了不少故事,还是有一点吃惊。当年的编辑为了出书,甚至还要动用各种社会关系,先去帮助解决作者的历史遗留问题,然后才有可能来为他出书。我就想,那时候的出版社真是管得宽啊。
出版因为它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它连接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我记得刚到人民社的时候也听陈总跟我们说,人民社的编辑,在经济学会、历史学会、美学学会等社团组织里往往多是会长或者副会长,起着重要的作用。那时候出版的社会地位相对比较高。后来,我记得我在上海书店的时候,也是和陆灏一起搞过一次“理想的学术出版和学术出版的理想”座谈,当时江晓原先生因为出版过多地关注“项目书”而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我想,这也是出版人的担忧,当一个职业有可能成为市场奴隶的时候,其行业地位就只会往下走。
文化强国必定是出版强国。今天,我们如果要反思的话,那么从沈公等前辈出版人身上,应该看到他们是以一种怎样的态度来做出版的。以前说对一个作家最好的纪念就是读他的书,我觉得对沈公最好的怀念,就是如何把一个好的出版理念,把出版对社会的正向推动作用,发扬光大。

江晓原:大家都把沈公和《读书》联系起来,现在如果要讲沈公的勋业的话,他对《读书》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刚好在这个事情上,我这两年老是研究西方的刊物,所以有那么一点点一得之见。我觉得沈公在《读书》这个事情上所做的探索和贡献,在我们国内是非常罕见的,我相信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在西方像Nature这样的杂志,它的第一任主编干了50多年,一直干到死掉,第二任主编干了30多年,也一直干到死掉。这种长期的主编,给杂志造成了强烈的个人风格。我们的《读书》也是有强烈的风格,这个风格老沈肯定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虽然刚才大家都说老沈宽容,其实宽容并不意味着没有他的个人风格,《读书》肯定是有强烈的个人风格的。这种强烈的个人风格跟我们国内现在的大部分办刊理念是不一致的。我们国内的大部分刊物特别是学术界的刊物,他们总说自己是要做学术公器。什么叫学术公器?就是说这份刊物是为这个学术界服务的。学术公器的标准配置是一个编委会囊括了一些名流,特别强调的是匿名审稿制度,稿件都送到外面请专家审阅。绝大多数学术刊物都是这样办的,国外也是一样。这种刊物是办不成神刊的,因为这样的刊物一定会变成一个平均化的东西。你要想做学术公器,就不要指望这个刊物有强烈的独特风格,更不要指望有主编的个人色彩在里面得到反映。因为学术公器是天然排斥这两个东西的。在西方现在大家所熟悉的Nature这样的杂志,恰恰是反着来的,Nature的主编多次向媒体强调,我们是没有编委会,我的稿件是由我决定用不用的,跟外面的人没关系。我即使让人审稿,他也没有权力决定这个稿件用不用,哪怕他们审完,一致枪毙了,我也还可以用,他们一致推荐了,我也可以不用。这种完全由编辑部来决定的刊物国内当然也有,很多科普刊物就是这样。但是《读书》从创办之初起就没打算当一个科普刊物,用沈公自己的书里面说的,他是要办成一个思想文化评论。《读书》一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跟Nature类似的办刊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读书》40年的那本书里说,我认为《读书》就是中国文科界的Nature,因为从办刊的理念上来说它就是这样办的。沈公自己在那个书里特别说了,他说有一些文章写得很好的人,文章本身的内容很好,但是文本差劲,他就不登他们的文章。他对文本有美学追求,这种对文本的美学追求,完全就是沈公的个人风格。
再后来《读书》经历了一个严重“掉粉”的时期,那个时候已经不是沈公主政了,它让沈公很失望,所以沈公后来对别人说他现在不看《读书》了,只看《万象》,因为对文本的美学追求,那时候又寄托到《万象》上去了,就是在《万象》上仍然有对文本的美学追求。当然《读书》现在又回过去了,又重新开始有文本美学追求了。我那会儿说过开玩笑的话,我跟媒体说,我知道为什么《读书》现在变得不好看了,那是因为李零不在上面写文章了,这个话被沈公在他的书里引用,他说这个话流传很广。当然《读书》后来又恢复了对文本的美学追求之后,李零也又重新在上面写文章了,大家又觉得它好看。这个在《读书》办刊的理念中,沈公非常强烈的个人风格,我认为是非常值得学习的,尽管国内的大部分上档次的学术或者文化刊物,目前看来可能还很缺乏学习的条件,但是至少《读书》坚持了这条,其他的那些刊物也是可以跟上来的。
陆灏:江晓原先生刚刚说到我学沈公,当然确实从我认识沈公开始,就有追随沈公、做沈公的徒弟的想法,但是机会不多,因为他后来退休了。本来《万象》完全是为沈公做的,因为觉得他有那么多资源,那么多精力,退休了,很可惜,再搞一本杂志让他编。结果这个杂志刊号过了两年才下来,那时老沈说这两年我人已经散掉了,你再让我每个月编一本杂志,我没那个耐心了,你拿到上海去编吧。我编杂志确实学了沈公,但是沈公在《知道》那书里接受采访时说了,他编杂志喜欢要有弦外之音、言外之意,但是《万象》不强调这个,说我最不喜欢弦外之音、言外之意的,说我比较喜欢纯净的文化。其实老沈的弦外之音正是我最为欣赏的手段,但是在《万象》那个时候没有机会尝试。后来我协助创办《上海书评》,《上海书评》的领导们比较开明,所以在这份报纸上多少体现了一部分老沈编《读书》时候的那些弦外之音。所以,老沈对《上海书评》评价很好,比较合他的胃口,有点弦外之音。
沈锴:首先还是很感谢今天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大家能够在上海给公公举办这样一个追思会,非常感谢大家。其实之前每次公公到上海来,我也都会像小跟班一样地跟在后面去蹭一些饭局,吃一些饭。
公公喜欢吃这件事是从小到大都这样的,但是我小时候对他的印象就是一个字“臭”。我6岁的时候开始住在西总布,那时候打开冰箱,里面放的全部是王致和臭豆腐,还有他特别喜欢做臭咸鱼那种炒饭。他经常会在厨房里面炒一盘炒饭什么的,又臭又香的那种,他自己特别喜欢吃。后来我妈跟我说,其实他那时候已经炒得很少了,我妈小时候应该是吃他做的各种各样的饭长大的。据说他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做饭,应该是属于酷爱吃的这么一个人。
去年因为疫情嘛,家里面聚餐比较少,10月份查出来他肝癌晚期的时候,按照他的性格,我们就知道他肯定是不住院的,他一定要吃吃喝喝非常开心地过完他最后这一段时间。所以那个时候我爸我妈就给我发消息说,今天我们又去哪儿吃了。当时他们有一个约定,就是每周公公会找我爸去南小街上一个新开的阿文汤包,公公特别喜欢吃这种南方菜,特别是上海菜、宁波菜,那个阿文汤包每周都要去吃。我爸作为一个回请,就会请他每两周去吃一次俄式大餐,或者江浙菜。
他在家里面还有几个比较好玩的事情,他在家里面和白大夫、懿阿姨还有我们之间是一种斗智斗勇又联盟的关系,怎么说呢?他后来耳朵不太好,听不清了,要戴助听器,我发现他戴助听器其实有些间歇性耳背,有的话他就特别清楚地一下子就能听到,有些话就听不到。比如说我们去吃饭,要喝啤酒这件事你只要一说啤酒,他就立马能听见,立马就说好的,来一杯,还可以再来半杯;但是如果说要吃药了,你就怎么说他都听不见了。所以家里的医生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们家里面做什么的都有,做医生的,学化工的,他就会给我们一个一个都起外号,比如说我姐姐学化工出身的,他就说化学家,你什么时候可以研究出一种新药来,是红烧肉口味的药,这样的话我就能顿顿都吃进去了,我就可以就着酒吃了。
戴燕:我要说的是,老沈对于很多人来讲,是在那个特定时代、那个环境一个特别的出版人。其实在同时代跟他一起的,有各种各样的出版家,各种风格的出版家,各有自己的特色和成就,但是沈公是一个可能再也不会有的一位出版人。他所在的那个时代恰逢其时在变动,他真的是用够了空间在做事情。就好像说无知为大,他自己没有一个特别的立场,没有特别放强的一面,反而使得他有一个很大的空间自由活动,借用各种力量,借用各种资源。而且他真的很有本事,你看他在吃饭时胡说八道,其实他在说那些乱七八糟话的时候,心里早想好了他要干什么。这个真的是让人佩服的。我想老沈是特别有定力的一个人,这才让他在饭桌之上,在跟三教九流打交道的时候做成了他想做的事情。
孙甘露: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读《读书》对那个时代的精神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包括后来的《万象》。一个是他编杂志的风格,确实就像刚才几位老师讲的,编法是越出了一个完全学院或研究性杂志刊物的方法。还有刚才江晓原讲了,他不仅是编写得有学术价值的文章,而且是漂亮的文章,通俗讲是一种美文。为什么说对我有影响呢?我后来做的一些事情,包括做读书会也好,编《思南文学选刊》也好,不是说一个单一的文学杂志、艺术杂志,或者说是一个研究性、思想性的杂志,而是希望通过跨领域的,有小说、有诗歌、有随笔,包括艺术史的,也包括研究文字的,中外的,把它们放在一起。这实际上跟当初《读书》杂志,包括后来《万象》、《上海书评》的风格,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后来陆灏、俞晓群做海豚书馆,我也受邀编了一部分,有一个系列是小说。也是受沈公的影响吧,编书的方式以及进入的角度选择,实际上是拓展了,不管从台本上,人的选择上,各个角度,都是在当时的主流出版之外另辟蹊径。一个时代的出版可能确实也是需要这样一种看上去像花花草草,实际上都是在日常生活的角度来丰富,来印证我们关于时代的记忆或完整性。因为这些花花草草真不是简单的事情。像《读书》也好,《万象》也好,后来的《上海书评》也好,实际上是非常丰富的,在文化的主线上,把那些边边角角,人们的想象,人们的日常生活,关于日常生活的记忆,都汇总起来。刚才为松也在讲,再过50年,当我们这一代人都过去的时候后人怎么来看待沈公?换了一代人,隔了一代人的时候,可能就是通过沈公所做的工作,编的这些杂志,出版的这些书。当时三联出了大量的作品,塑造了一个时代的风尚,他的工作或者在饭桌上谈笑风生,这些看似是闲话的东西,其实都是有深意的。
最后我打个比方,当然也是借用别人的说法,《艺术的故事》说的,一个时代的艺术的精神风尚就像旗帜一样,你看见旗帜在飘,但实际上是风在吹,但你直接是看不到风的。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艺术风尚,是背后有这个东西在驱动,沈公就是做的这个工作。
王强:我当年在《八八沈公》里写了一篇文章,叫《思想的邮差》。其实沈先生作为一个出版家,最大的贡献就是思想的邮差,这个邮差非常敏锐准确地递送思想的包裹,这是我写那篇文章起这个题目一个非常清晰的印象。因为大家知道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邮差是所有人翘首以盼,最重要的一个人了。后来我一想沈先生无论是编《读书》的时候,还是《万象》的时候,或者陆灏他们后来做的《上海书评》,我为什么愿意投稿,就觉得他们实际上是把思想做成了集市、庙会。这个集市充分体现了一种自由的东西,体现了自由、美、高尚道德。
汪涌豪:沈昌文先生与整个1980年代文化的新生是密切相关的。一个人的工作和整个时代变化发展,文脉、气脉相关联,这是何其了不起,而且他死后这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纷纷怀念他,他的身前是非常精彩的,他的身后也有足够的哀荣,这是很了不起的。
从他的身上我感到,出版绝对不是和书打交道的问题,出版从本质上说是和人打交道的问题。在这点上沈昌文先生堪称模范,以前孔子说是有教无类,我认为沈昌文是有交无类,而且交的过程中显出了难得的识力、判断力、亲和力。为了做成书,他可以屈就、宽容、顺从,可以屈己从人,这里面有很大的学问。专业之外要能够分别事项,体会人情,要能够应付领导,激励员工,这些东西都是干出版的人所必备的,但是今天似乎这些都在慢慢消失。
周立民:刚才大家听到范用跟沈公的事情,恩怨我们不评论,最近我是越来越体会得到,确实他们两个人是两个传统。沈公在他的回忆录里说,有革命家,有学者,他是学徒。我们可以不这么看,如果从两个传统来讲,沈公的传统应该是出版里面比较务实的传统,范用先生大概是一种精英或者更文人化的传统。范用的传统跟巴金、鲁迅更接近,他们是不管书卖不卖钱的——当然也不是完全不管。但是他们这些朋友办出版社,自己不拿工资的,鲁迅也是,书不卖钱我自己掏钱印。沈公的传统可能更接近于邹韬奋的传统,老的生活书店是很注重成本,包括跟大众之间、市场的需求,所以说鲁迅跟生活书店闹掰了很正常,他们的理念就是不一样的。在这两种传统里面,我们这些所谓的文人,肯定更喜欢范用的传统,因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说实话,这些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认为这两个传统是不可以偏废的,也是不可以分割的,甚至某种程度上来讲,沈公的很多传统更值得我们重视。
今天再谈三联也好,谈沈公也好,谈《读书》也好,我们不应该把他们从那个时代剥离出来,不然的话,可能年轻人或者后辈仅仅把他们当做一个个人的传奇故事来讲。他们是这个时代里面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在这个时代里面,能够抓住时代提供他们的条件大有作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也不必抱怨今天怎么样,过去怎么样,未来怎么样,时代提供给我们的条件,我们是否充分地利用,或者尽我们知识分子可以发挥的东西,或者坚持的底线,这是在前辈面前需要我们来叩问自己的良心的。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