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林语堂看《浮生六记》:边缘文化人的西方视角解读
《浮生六记》在经俞平伯推介流行约十年后,1935年,又被林语堂译为英文介绍给西方。林氏在此书的译序中对此书做了评论,在此前后发表的其他多篇谈论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生活的文字中也多次引述此书内容。在林氏围绕此书的这些议论中,对于沈复夫妇的生活方式所代表的这一民间传统,做出了与俞平伯颇为不同的解读。
林语堂(1895~1976)也是成长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人,但他的身世和文化背景却与俞平伯有很大不同。他出生于福建乡村一位基督教牧师的家,生长于基督教圈子中,稍长即入教会学校读书,由小学而中学,后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不久他又赴美国及欧洲留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在北京各大学教授英文。据他自言,只是回国在北京居住以后,他才开始真正接触中国社会和民族文化,这时他已是接近而立之年了。他自幼就被基督教隔绝了民族传统文化,甚至连像一般孩子那样看戏和听说书的机会都没有。他为自己身为一个中国人,连妇孺皆知的“孟姜女哭长城”之类的民间故事都不知道而惭愧,为自己被西式教育割断了民族文化之根而愤怒,于是决然放弃基督教,倾心于民族文化,并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1924年新文学刊物《语丝》创刊,他与鲁迅、俞平伯等并肩作战,以该刊为阵地发表了系列文章,激烈抨击军阀统治和守旧势力,活跃一时,成为以立场鲜明、文风犀利著称的“语丝派”一员大将。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后,在政治高压和个人生活优裕等诸种因素的作用下,他的立场发生变化,与政治和激进文化活动逐渐疏离,转而提倡幽默、闲适。他创办《论语》《人间世》等杂志,写幽默小品文,宣扬闲适生活,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被时人称为“幽默大师”和“闲适大师”。由于正处于日本侵略我国东北并觊觎内地、国民党加强独裁统治的内忧外患时期,因而他提倡的这些被鲁迅等左翼文人斥为脱离现实、脱离社会的“小摆设”文字。在此期间,他还用英文撰写介绍中国文化的文字,并在美国发表,赢得一定声誉。所以,林语堂虽然身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却因特殊际遇而深受西方文化濡染,成为一个处于中西之间的边缘文化人。在当时新文化人中,他以“洋派文人”的形象名于时,是当时西式教育和留学出身的洋派文化人的一个典型,而且由于其教育背景及职业性质,西方文化在他的知识结构中处于基础和主干的地位,并成为其观察问题的文化底色。

林语堂
在这种背景下,林语堂1935年将《浮生六记》译为英文并在美国出版。他对这本书感触至深,将此书列为“足以代表中国生活艺术及文化精神(的)专著”之一,他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译序,首先在国内刊物上发表。他还在多篇谈论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生活的文字中屡屡引述该书的内容,如在此后两年写成的英文书《生活的艺术》中,不仅大段摘录了《浮生六记》的内容,加以赞许,还专门写了题为“两个中国女子”一节,称赞芸和《秋灯琐忆》中的秋芙是两个“最可爱的中国女子”。这些文字表达了他对此书所代表的一种家庭生活方式的看法,反映了他的家庭观念和生活理想。
林语堂的视角与俞平伯有一点相同之处,就是他也赞赏沈复夫妇舒展个性、追求个性自由的生活态度,而反对大家庭制度对个性的压制,因而与俞平伯一样,他也属于当时新青年倡扬的“个人本位”新家庭观念的阵营,与个性解放的启蒙思潮方向是一致的。但他的视角又与俞平伯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俞平伯对沈复夫妇伸展个性的肯定,重在批判大家庭制度摧残个人才性的罪恶,强调个人才性伸展与民族群体强盛的共生关系,目标在使中国“天才挺生”而民族自强,从中可以看到传统家国情怀和民族群体主义观念的延续。而林语堂对沈复夫妇生活方式的肯定,则更偏重于对个人幸福的追求,是一种更彻底的个人本位观念,从这一点来说,他更接近于西方的个人主义。
林语堂在这种比较彻底的个人本位观念的观照下,所关注的就不是像俞平伯所注重的沈复夫妇个人才性伸展受到大家庭摧残的悲剧,这种悲剧性只在他的文字中一笔带过,他关注的重心并大加赞赏的是沈复夫妇充满个性才情和闲情意趣的生活态度。他赞美这对夫妇“爱美爱真的精神和那中国文化最(具)特色的知足常乐恬淡自适的天性”。他在多篇谈论生活艺术的文章中,引述沈复夫妇对庭院房间的布置、插花的艺术、享受大自然等种种怡情悦性而富于艺术情趣的记述,赞赏“他俩都是富于艺术性的人”。他特别赞美芸具有“爱美的天性”,她与丈夫一起赏景联句,亲手制作美食等,使日常生活充满了艺术情趣。所以他认为,既有才识雅趣,又具爱美天性的芸“是中国文学中所记的女子中最为可爱的一个”。赞美她“虽非西施面目,并且前齿微露,我却觉得是中国第一美人”。他同情芸“爱美的天性与这现实的冲突”所造成的悲剧,认为“这悲剧之原因不过因为芸知书识字,因为她太爱美”,在林语堂看来,“这对伉俪的生活是最悲惨而同时是最活泼快乐的生活”。可见,林语堂所赞赏的沈复夫妇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与他这一时期所倾心提倡的闲适生活品味正相契合,甚至沈复的写作态度和写作风格,即“一个不出名的画家描写他夫妇的闺房中琐事的回忆”,也与他提倡的被讽刺为“小摆设”的文字风格颇相类似,反映了他在个人主义生活态度上与沈复有某种相通。

《浮生六记》
林语堂对《浮生六记》的解读,表现了他崇尚个人主义和闲适生活的家庭观念,反映了他的家庭生活理想。他对芸爱美天性的赞赏,即是他理想的女子(妻子)形象;他对沈复夫妇情趣相投的赞赏,即是他理想的夫妇关系;他对沈复夫妇充满艺术美感和闲情逸趣的生活方式的赞赏,即是他理想的家庭生活样式;他对沈复夫妇知足常乐、恬淡自适的生活态度的赞赏,即是他推崇的生活态度。因而,沈复夫妇成了他崇尚的“闲适生活”的一个符号,他的理想家庭的一个例证。
林语堂对《浮生六记》的这种解读,蕴含多重意义,反映出在林语堂眼光的过滤后,该书内含传统元素的某种变异。概而言之,有以下三层。
第一,林语堂将沈复夫妇作为理想的个人本位家庭生活的一个典型而推崇,从中体现了西方个人主义人生观的影响。
林氏赞赏沈复和芸沉醉于夫妇生活的小天地,享受恬淡自适的小家庭生活,体现了他崇尚彻底的个人本位家庭观念。林氏之所以推崇这种家庭观念,主要缘于他自幼深受西方基督教文明影响的个人主义人生观。他自幼过着基督教氛围浓厚的生活;至大学毕业前,一直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曾有志于做神职人员,基督教文化已深深植入他的心灵。他在晚年回顾自己的人生时说过:“我是在基督教的保护壳中长大的,圣约翰大学是那个壳的骨架。我遗憾地说,我们搬进一个自己的世界,在理智上和审美上与……(中国社会——引者注)断绝关系”。他自述这种教育“令我树立确信西洋生活为正当之基础”。基督教关于个人直接面对上帝、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个人主义观念,自然深入他的意识里。他对于沈复夫妇追求个人(夫妇)幸福,以夫妇幸福为中心的家庭观及男女平等的夫妇关系的肯定,体现了这种西方个人主义的人生价值观。他对沈复夫妇爱美爱真天性的赞美,特别是对芸这位艺术气质的女性的赞美,也充满了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气息,与强调伦理秩序、道德自律的中国传统人生观迥然不同。
从外部而言,他这种个人主义人生观,还与其生活环境对中国社会的疏离有关。他的生活与一般中国人不同,他自幼随父母住在父亲布道的偏僻乡村的教堂侧房里,入学后又住在教会学校里,因而疏离了传统的家族制度、大家庭生活及乡土文化,缺乏对中国式群体生活的种种体验及了解。及至他留学回国后,在大学执教,并常在国内外发表文字,收入颇丰,生活优裕。这些都使他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中国社会实际,不了解民众疾苦,更助长了他头脑中的自我中心及个人主义意识。他在20年代积极参与抨击军阀政治的社会活动,表达的就是反对专制压迫、争取个人自由这种个人主义的强烈诉求。他后来提倡闲适生活,只是这种个人主义的不同表现而已。所以,林语堂对于沈复夫妇个人(夫妇)中心的生活方式大加赞美,而对他们如何调处与大家庭的关系,在这种调处过程中的困难、无奈和失败等等一般中国人必须面对的社会生存问题这一面,林氏则不感兴趣,也不加注意。因此,在林氏这里,沈复夫妇的个体幸福与大家庭束缚的矛盾关系便被割裂开来,只剩了前面的一半,成为林氏歌颂个人本位家庭理想的符号。
第二,林语堂对沈复夫妇恬淡自适的生活态度的推崇,体现了中国自然主义和乐生主义人生观的影响。
林氏对沈复夫妇个人本位的家庭生活理想的定位,又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基督教的个人主义,因为从中虽然我们可以看到与西方个人主义相通的内核,但同时还可发现其中又缺乏西方基督徒对上帝的敬畏之心,以及基于基督教原罪、救赎观念的个人责任意识和苦行意识,而是更多地看到与此相反的自然随性、从欲放达、享受世俗之乐的倾向,而这些正是中国道家所提倡的无为、随性的自然主义,及儒家乐生知命的人本主义的传统因素。
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林氏的思想里也是自有来源。他虽然自幼被圈在基督教文化圈子里,但毕竟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生活在中国人中间,他与民族乡土文化虽有疏离,但又有割不断的血肉联系。他不仅在少时也听父亲讲过《四书》《幼学故事琼林》等本土蒙学读物,而且他的婚姻也是由父母做主的旧式婚姻,是父母出于经济考虑而选定的一位钱庄老板(也是基督徒)女儿。他的这位夫人虽然也上过教会学校,但却是一位颇为传统的贤妻良母式的妇女。林氏的这些生活背景,使他的人生观也必然会被打上中国文化的烙印。也正因如此,他在由西式教育培养成熟而在留学归国后开始正面接触民族文化时,很自然地对儒家的人本主义和道家的自然主义,以及儒道均有的乐生主义感到亲近,于是幡然放弃基督教,成了一个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的推崇者。他赞赏孔子人本主义的社会观念和家庭观念,他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以赞赏的口吻写道:“依孔子的见解:政治的最后理想原是异常属于生物性的。他说:‘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孔子意欲使一切人类天性都得到满足,以为必须如此方能使人在满意的生活中得到道德的和平,而只有道德的和平方是真正的和平。”他也赞赏道家的自然主义,在中年后写的自传中说:“也许在本性上……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或道家。”他在老年回忆中也“以道家老庄之门徒自许”。他还推崇中国传统的乐生观念,认为:“一切中国的哲学家在不知不觉中认为唯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要怎样享受人生?谁最会享受人生?”他提倡顺乎本性的自然主义:“对自己而言,顺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因而他的理想,就是使“个性自然之发展”,“叫国人取一种比较自然活泼的人生观”。这是一种排除秩序、社会、群体的个人中心的自然主义。
林氏认为,沈复夫妇正代表中国传统的人本乐生的自然主义人生态度,即所谓“中国文化最(具)特色的知足常乐恬淡自适的天性”。他欣赏沈复夫妇这种中国文化特色的生活态度,称他们是过着“恬淡自适的生活”的“两位平常的雅人”,“知道怎样尽量地及时行乐”。他欣赏沈复夫妇的生活理想,说“我相信淳朴恬适自甘的生活,如芸所说‘布衣菜饭可乐终身’的生活,是宇宙间最美丽的东西”。
可以说,林氏眼中沈复夫妇所代表的个人本位家庭观,既有与西方个人主义相近的一面,也有与中国儒家人本主义、道家自然主义及儒道共通的乐生主义相近的一面。他的观念与西方个人主义不同的是缺乏责任伦理,与儒家不同的是排斥群体秩序伦理。所以可以说林氏推崇的沈复夫妇的小家庭文化,是西方个人主义与中国自然主义的混合物。在他眼中,沈复夫妇正是他崇尚的这种个人本位的自然主义的理想家庭生活的典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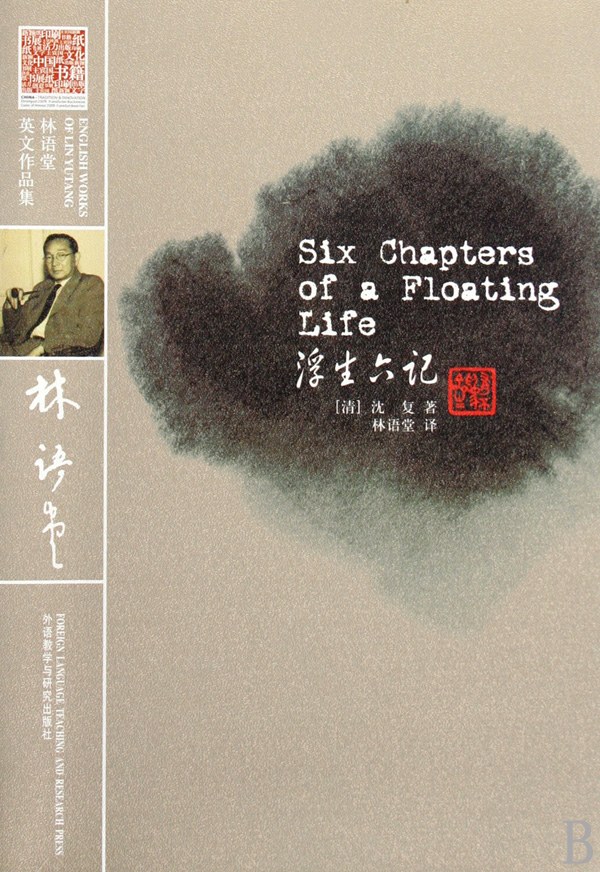
林语堂译《浮生六记》
第三,林语堂对沈复夫妇“闲适生活”的推崇,体现了他作为一个中西文化边缘人的西方视角和民族主义情结。
林氏推崇沈复夫妇的生活方式,把他们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态度的完美典范介绍给西方人,反映了林氏“两脚踏东西文化”的边缘文化人心态。林氏受西式教育,西方文化是其知识结构、思想观念、价值系统的基础和主干,因而他理智上认同西方文化。但他又身为生长于中国本土的中国人,对本民族及其文化有着天然的血脉联系,因而感情上又依恋民族文化。他曾自言:“自我反观,我相信我的头脑是西洋的产品,而我的心却是中国的。”“我常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我曾作了一幅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这种边缘文化人的心态,使得《浮生六记》的符号意义被他置于理智与情感、中国与西方的双重文化视域下。
林语堂的西方文化背景,使他习惯以西方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为基准,特别是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时,会从受众的角度考虑,着眼于为西方文化补缺而凸显中国文化之长,这些都形成了他解读《浮生六记》时采取西方文化的视角。这一视角使他观察中国文化时,以一种“局外人”的眼光,从外部审视,以西方价值为基准,以西方文化为坐标,以西方现实需要为着眼点,进行以西方为中心的价值评判。如他自言:“这基本的西方观念令我自海外归来后,对于我们自己的文明之欣赏和批评能有客观的,局外观察的态度。”刘志学主编《林语堂自传》,第22页。他对于中国文化以局外人的眼光,做有一定距离的观察,能够从互补角度比较出相对于西方文化的优缺。正是在这种视角之下,他推崇沈复夫妇所代表的中国人“恬淡自适”的人生观。他曾对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生活态度做过比较,他说:“美国人是闻名的伟大的劳碌者,中国人是闻名的伟大的悠闲者。因为相反者必是互相钦佩的,所以我想美国劳碌者之钦佩中国悠闲者,是跟中国悠闲者之钦佩美国劳碌者一样的。这就是所谓民族性格上的优点。”他认为理想状态应当是中国的人生哲学和西方的工业文明互补融合:“机械的文明中国不反对,目前的问题是怎样把这二种文化加以融合——中国古代的人生哲学和现代的工艺文明——使它们成为一种普遍可行的人生哲学。”他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现在的弊病,就在于机械文明使人们的生活过于劳碌,这有违人类的天性。他相信,随着机械文明的发达,人类谋生的重负会逐渐减轻,因而也会更倾向于接近天性的悠闲生活。他说:“机械的文化终于使我们很快地趋近于悠闲的时代,环境也将使我们必须少做工作而多过游玩的生活。……当物质环境渐渐改善了,疾病灭绝了,贫困减少了,人寿延长了,食物加多了,到那时候,人类决不会像现在一样的匆忙。而且我相信这种环境或者会产生一种较懒惰的性格。”在他看来,沈复夫妇所代表的中国人“恬淡自适”的生活态度,正是矫正西方人过于劳碌之弊病的良药,因而是对美国今天之缺陷有所补益的中国“民族性格的优点”。这就是他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坐标下,对于沈复夫妇所代表的中国人“恬淡自适”生活态度的定位和价值判断。在这种价值判断之上,他极力予以推崇之、揄扬之、赞美之,也确实颇合西方读者的口味,因此他的书在美国畅销,他也在西方人中声誉鹊起。
林语堂思想观念的另一面,是他对于民族及民族文化的感情依恋,这种依恋隐藏于他凸显中国“民族性格的优点”来反衬西方弊病的意识里。正是这种感情依恋,使他对于中国文化的评判,并不完全如他宣称的是“局外人”的客观态度。他虽然理智上认同和崇尚西方文明,但身为中国人,他与自己的同胞血肉相连,对祖国长期受西方帝国主义欺压有着切肤之痛,心中有着因民族命运而生的屈辱感、挫折感、自卑感和自尊感交织激发的民族主义情结。作为现实国际关系中弱势民族的一员,他从民族文化中挖掘出“民族性格的优点”,凸显其相对于西方的优越,并预言其对于西方弊病的矫正及人类未来的正面价值,极力向西方人宣扬,就是要通过这种对本民族文化的肯定和宣扬,来对抗与西方比照之下的国家落后与民族屈辱感,寻求民族自尊的依托。也正因如此,他的那些原本只是以西方人为读者的文字,再译回中文于国内发表之后,在国人中也赢得了一定赞誉。但是,这种貌似与西方对抗的民族主义情结,实际上也是西方视角的派生物——被殖民心态的体现,是西方中心主义坐标下的产物。
此外,林氏推崇沈复夫妇“恬淡自适”的人生态度,融合中国人生哲学和西方工业文明的理论,以及关于后工业时代悠闲生活的人生观,还具有“后现代性”意义,与工业时代被异化的人们自然产生回归人类本性的方向一致。正因为如此,他对沈复夫妇赋予的“闲适生活”的符号意义,具有一定的超国界性和超时代性,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会得到一些共鸣。《浮生六记》在30年代重印中常被列入“美化生活丛书”“娱情小品撷珍”等,也是这一脉的和声。及至我国改革开放后,林氏《生活的艺术》《人生小品集》一类文字与《浮生六记》一起,在加速工业化的喧嚣中又再度重印、流行,也是这一流脉的体现。
但无论如何,林氏当年对《浮生六记》的解读,毕竟还是应当还原到当时的语境中去评判它的历史意义。从当时的情境而言,林氏对沈复夫妇生活的评判,他的“闲适生活”理论,是对应于当时西方的现实需要,而非中国的现实需要。众所周知,在他向西方人介绍《浮生六记》、赞美沈复夫妇“闲适生活”的1935年前后,中国正处于外敌进逼、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对于广大中国人来说,他的这种“闲适生活”议论不啻梦中呓语,显得多么遥远、奢侈和不切实际,自然受到鲁迅的抨击和人们的非议,他也自感在同胞中间难以立足,遂于全面抗战前夕的1936年,带领全家移居美国,去专门为更喜爱他这些论调的美国读者写作了。
由林语堂对《浮生六记》的解读,我们还可以看到,林氏这种理智上认同西方与感情上依恋中国、西方知识结构与民族主义情结交织的边缘文化人心态,使他在西方工业文明价值与中国人生哲学价值之间,在中西不同的现实需要之间,常常陷于矛盾,左右失据的状态,在交替使用两种文字与面对中西双方听众之间,也常陷于互混与错位的窘境,有时甚至连他自己也被搞糊涂了,因而他在晚年自传中称自己的一生是“一团矛盾”。他到晚年又回归基督教,也是其文化心理“一团矛盾”而寻求解脱的体现。这种自我定位上的混淆与矛盾,使他在西方文化坐标下看待民族文化,评判民族文化的价值时,却与中国现实需要之间错位。应当说,中国现代文化建构的基本元素多由西方移植而来,故易于造成中国文化人的这种心理“迷失”与认知错位。这种边缘文化人心态与错位的认知方式,在当时文化人中并不少见,在许多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林氏只是其中一个典型。而且直至今天,其余脉犹在,仍常见一些向国人讲述西方话语的“边缘文化人”,也患着与林氏同样的水土不服之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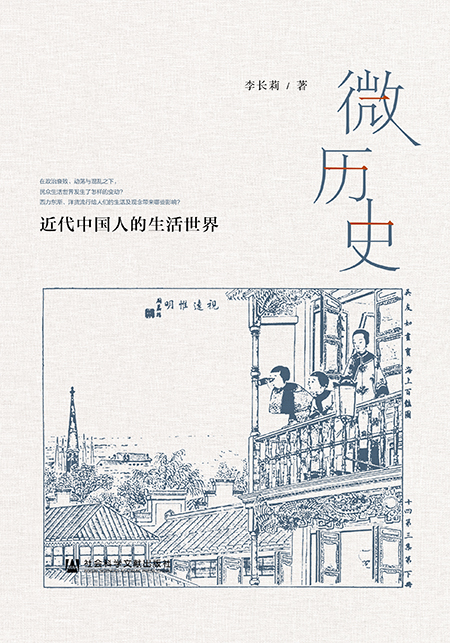
本文节选自《微历史:近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李长莉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月版),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摘发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