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张旭东:如何理解当代文学
【编者按】
本文根据张旭东教授在2009年由上海大学和纽约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整理而成,原刊于《学术月刊》2009年第10期,收录于最近出版的《批判的文学史:现代性与形式自觉》,澎湃新闻经授权刊载,原题为《当代性与文学史》,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这个题目涵盖很广。但是它背后有一个特殊的含义,不是一个泛泛的、国内当代文学学科意义上的当代文学史,而是借用了保罗·德曼的一篇很著名的文章《文学现代性与文学史》(Literature Modernity and Literature History)。这里我不打算详细介绍这篇文章,而是想在“重新考虑当代性和文学史这两者的关系”的理论层面上,借助德曼的思路提出一些我们自己的问题。问题的核心,就是我们如何理解当代文学,如何把握最高意义上的当代性和文学性,进而把握批评和文学史写作的内部矛盾和理论挑战。
首先我想谈谈“当代性”的问题。我们必须——或者说不得不——把一切有关我们自己的经验——包括文学经验、政治经验、社会经验、个人经验等——高度当代化,也就是说,作为当下的、眼前的瞬间来把握。此刻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也并不在一个历史主义(historicism)的时间轴上思考,这是单纯的经验和体验的本质,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的冒险”。“当代”的第一层意思就是仍然在展开的,尚没有被充分历史化的经验。“当代”不属于已知的过去,甚至可以说它悬置在历史之外,因此具有一种特定的紧张感和不确定性。没有当代化或者当代性的基本含义,我们就没有当代文学这个问题,而只有文学史和文学研究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经验。我从来不觉得当代文学是现代文学的弃儿,被现代文学所排斥,这种被边缘化的感觉大概只有在一种狭隘的专业主义氛围里才有可能。相反,在一个更高的意义上来说,当代文学却是要有意识地把现代文学排斥出去,把它作为“历史”归入另册,从而为把作为当代经验有机组成部分的当代文学经验从“过去”分离出来,把它保持在一种特殊的思想张力和理论可能性之中。通过这种非历史化的自觉意识,当代把自己变成了所有历史矛盾的聚焦点,当代文学则把自己变成了所有文学史的最前沿和问题的集中体现。尼采曾说,“所有的历史最终都来到了现代性”,这里的“现代性”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代性”。我们也可以说,所有的文学最终都来到了当代文学。
最高意义上的当代,必然是现代性的最激烈、最充分、最政治化的形态;而最高意义上的当代文学,必然是文学本身最政治化、最具有矛盾性的状态,这种状态不仅仅界定当代文学,它事实上在一个特定的意义上界定着文学性本身,由此回溯性地界定一切关于文学和文学史的思考和讨论。当代文学自身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具有批评和理论的蕴涵,除此之外,一切都属于历史,属于过去,属于当代意识的对象领域。现代文学也好,古代文学也好,作为知识的文学理论也好,都只有“史”的含义,而当代文学总体上同“历史”和“知识”对应或对抗,因为它存在的本体论形态是行动,是实践,是试验,是冒险,是选择、判断和决定。文学虽然是一种表象或再现,但就其最内在的想象力和赋形能力来讲,它不属于反思和观念的谱系,而是属于一种不确定的、尝试性的生产性或创造性活动,即一般意义上的艺术活动,并通过这种自身的内在属性而进入了广义的“当代”和“当代文学”所包含的文学本体论和政治本体论。这是我想谈的第一点。

保罗·德曼,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文学理论家
其次,一旦把当代性最为历史的对立面确立起来,它马上就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当下”把自己非历史化或形而上学化之后,马上会意识到自己仍将面临下一个当代、下一个此刻、下一个把此前的一切视为过去的再历史化倾向。这里的矛盾类似于保罗·德曼借用尼采的《历史对人生的利弊》(Use and Abuse of History to Life)所指出的问题。尼采讲的是整个欧洲意义上的现代性要摆脱历史的重负,可是当它把自己作为一个创造的瞬间建立起来的时候,又不得不随即把自己历史化,在一个历史的过程中审视和反思自己。这个张力,我觉得在当代文学里存在和展开得最充分的,但在当代文学研究界对此好像恰恰也最缺乏理论性的反思。相对于即将到来的下一个此刻,下一个当代,这个“此刻”只能是历史。所以在“当代性”内部,又必须不断地产生“作为历史的当代”或“当代史”意识。因此,“当代文学史”在严格意义讲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因为“当代”不应该有“史”, “当代”就是一个永恒的“当下”,它有一个张力,而一旦当“永恒的当下”不得不自己把自己历史化了的时候,实际上是自己把自己否定了,我们所能获得的不过是一连串既相关又彼此割裂的过去的“当下”和“此刻”,它们被文学捕获、赋形,而所谓当代文学史,在罗列这些文学作品和文学事件之外,不过是将过去历史化的努力,包括将正在展开的当下作为过去历史化的努力。比如说我们今天上午讨论80年代先锋派的问题,先锋派当年对我们在座的很多人来说是进入当代文学的切口,而正因为它们是当代性和文学性本身,它在当时对于我们来说是无历史或非历史的,因为它是我们正在展开的存在的命运、语言的命运、思想的命运的组成部分。但是现在它不得不被历史化,被作为历史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对象,被作为一个过去时代的主观幻想、神话和偏见来审视。如果我们还要把先锋文学或实验小说包含在当代文学的范畴中的话,我们就必须承认,当代文学本身包含着把自身历史化的倾向,这是意识把自身对象化,即作为认识和批判的对象的努力。
今天我的引言时间越短越好,因为讨论会更有意思。所以在这个开场白之后,我接下来想简单地谈那么几点:
第一个问题, “当代”是怎么来的?开会前我翻了一下陈晓明送给我的他写的《当代文学史》,前面有一些非常有用的讨论,比如“当代文学”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有些事情我以前也不知道。但是我想在一个摆脱学科意义的层面上,就“当代”这个字眼所具有的理论可能性谈谈“当代”从哪里来。肯定不全面,但以下是我目前所想到的几点:首先我就想到俄苏传统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以及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强大的影响。我们知道俄国文学变成一种世界文学的起点是普希金,后来有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直到19世纪后期的小说和戏剧。在俄国文学当中一直存在一个问题即如何在自己的文化中做世界的同代人。“当代”在英语里叫做“contemporary”,晓明的书里面也提到这个问题,它本来的意思就是同时代的,我们大家都共享的这个东西。我们是当代人,是同代人,所以我们享有同代人的文学。俄国文学第一次带来了这个问题,即我们如何在自己的文学和时间里做世界的同代人。这个“世界”当然不是指任何一个地方,而是特指西欧,即怎么做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的同代人,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跟他们处在同样的世界历史的时间当中,思考同样的普遍性的问题,面对同样的自由和不自由,但却是在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我们自己的文学。我们的文学怎么样能把我们同最先进民族的(因为我们是落后的,这是俄国和中国相对于西方的一个共同的相似的位置)文学放在同一个“当代”的时空中,或者说,通过文学把这个想象的时空产生出来,再反过来用这种时间概念来理解自己的经验。这个世界历史的时间差及其克服的问题,我想可能是“当代”概念的一层未曾言及的含义。与新中国和革命新人同步的当代文学,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这种世界文学和世界历史的诉求与梦想。我们似乎从来没有把这层意思提出来讨论,但或许值得做一些意识史的考察。至少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同时期,这种世界文学和世界历史的冲动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内容和指向。

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2009年版4月版
第二,随着近现代日本文学思想和批评,包括竹内好、丸山真男,以及鲁迅研究里面我们很熟悉的一些日本文学研究者进入当代中国的知识视野,日本思想界所作的近代和现代的区分,在中国的语境里面,也许已经成为常识性问题。简单地说,日本意义上的“近代”,就是明治时代以来的“文明开化”“脱亚入欧”,一切以西方为圭臬的行为和意识范式。而日本意义上的“现代”,则是在亚洲建立殖民势力范围,最终以太平洋战争和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为手段,挑战欧美现代性,建立作为“世界历史”的日本的主体性的失败的努力。可以说,即便在今天的,在日本“近代”自由主义主流思想下面,仍然涌动着种种“现代”的骚动,如左翼和右翼的反美情绪、文化保守主义、和比日共更激进的批判意识,等等。在中国语境里,现代和当代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结构上类似于日本近代和现代的一个紧张关系,即19世纪与20世纪的交叠和对抗。现代或“现代化”(包括“改革”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对应于“文明开化”的追求,如工业化、政治改革,建立制度上的理性化等等。但中国的“现代”同日本的“近代”相比,包含着更为深刻、更为激烈的现代性的自我否定和自我颠覆,它最终是通过毛泽东主义的大众革命完成的,并由此而进入它更高的“当代”阶段。所谓19世纪与20世纪的冲突,也就现代性内部矛盾的激烈化和政治化,它的结果是“当代中国” (人民共和国)的确立。但在今天,我们的当代其实又是一个被重新历史化了的当代,是一个把革命的当代(新中国)放回到一个更长的历史过程之中,对之作历史主义的非政治化和理性化处理的“后当代”。这个历史构造和价值冲突也在“当代文学”里表现出来。“新时期”文学的基本母题,实际上是从人道主义到现代主义先锋派的整个的19世纪布尔乔亚文学传统的快速回放。文学在这里的社会意识形态作用,可以说是一种“回到19世纪”的想象的媒介。所以今天中国思想领域的论争,是内在于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因为当代文学在“根子”上就有19世纪和20世纪的矛盾和冲突。从这种矛盾冲突的角度看,“当代文学”概念的原始含义和政治激进性首先来自“当代中国”的前三十年,这是一个英雄主义的、创造性的“非历史化”过程,是“当代性”的正面含义;而后三十年则是这个当代性本身的历史化,或者说颓废化和神话化——我们应该看到,这个克服了20世纪的19世纪,本身又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是“历史终结论”的一个版本。目前年轻一代当代文学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关注前三十年,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当代”含义的第三个组成部分,也是最主要的部分,当然是20世纪中国自身的革命经验,以及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现实在“新人”的意识构造上留下的持久印记,或者说对新中国人的主体性的赋形在作用。在我很高兴看到陈晓明在他的《当代文学史》里面建议把当代文学的起点放在1942年,而不是1949年。在最近一个访谈里,我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如果从鲁迅1927年黄埔演讲里从革命现实和革命人的向往出发,那么我们会觉得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起点,因为针对新文学来说,讲话标志着基于一个实现了的革命现实和革命人的具体而实在的确立。这与鲁迅这一代对于新人、新现实、新文学的想象有本质的不同。在这些意义上我们可以回到一开始谈的一点,即针对严格意义上的当代文学或当代文学研究来说,现代、现代史、现代性,现代文学、现代文化,都只是当代文学的史前史,它们都最终来到了当代,也就是说当代性涵盖了所有这一切,把它们统统都作为自身发展的环节,包含在它的内在矛盾之中。换句话说,一个扩大了的当代文学的含义,包含着现代文学,甚至包含着古代文学,也包含着外国文学,它把这一切都视为自身经验和自身实践的必要元素,包含在自己的结构当中,作为自身矛盾和问题性的一部分,包含在自己的批评空间和概念空间当中,包含在自己时间的构造之中。
话已到此,我干脆就用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说法来表明的我的立场:现代文学是被当代文学生产出来的,正如历史是被当代生产出来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文学其实最终都是当代文学。当代文学无论在研究的意义上、还是在批评的意义上、还是在“史”的意义上,都在把整个文学现代性的从自身内部不断地、反复地生产出来。最好的现代文学乃至古代文学研究,应该是由当代文学的人去做,因为只有搞当代文学的人才能真正地把握现代文学,这是在批评和批判(这既是康德“判断力批判”意义上的批判,也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意义上的批判)意义上的把握,而不是历史主义、经验主义和学科专业主义的把握。反之,做现代文学的人,如果本身不处在当代文学的激流中,对当代文学无话可说,那么他们对现代文学或古代文学,其实也说不出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来,除了基本的资料整理和语文教学意义上的知识传授。当代文学如果不仅仅把自己看作一个教研室或专业行会意义上的“界”,就不会有什么焦虑感,因为当代文学,就我们的有生之年来说,其实就是文学本身,或者说是我们通向真正的文学和文学的全部丰富性的唯一的通道。
说到当代文学生产出整个文学性,就不得不再次谈到德曼借尼采的说法谈的文学现代性和文学史之间的张力。德曼的逻辑我们通过文学批评把握文学现代性,特别是把握文学内部的“此刻”性和本体论层面的拒绝历史,在同混乱、激情、死亡相对峙的过程中产生的现代性。这种文学现代性一方面带来文学的永恒,但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悲剧性地把自己交给历史,即文学史。我觉得这里面最有意思的部分并不在于历史最后的胜利,哪怕是反讽性质的胜利,而是这个问题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所谓“文学本质”的反历史、超历史特性,虽然这种反历史、超历史的形式本体论最终也仍将以历史和知识的方式流传下去。这个观察可以让我们再一次较真,一步步去追问“什么是文学”这样的堂吉诃德式的问题。这种追问方法当然只能有一个答案:文学概念必须由文学本身来界定,而不是由文学史来决定。这也就是说,没有当代文学意义上的第一线批评,没有当代文学或文学当代性意义上的面对文学文本的阅读经验,一切都无从谈起。当我们第一次与一个陌生的文本遭遇,我们要去分析它,要去阐释它,要去对它下判断,这时候我们不得不调动起所有的情感、知识、智慧、能力和资源;这时我们是脆弱的、不安全的,因为我们要为我们的判断力负责,此时我们同自身环境的政治性关系是完全暴露在他人眼前的,正如第一次被我们阅读的文学作品,它文学自身的不稳定性,脆弱性,也暴露在我们眼前。文学的概念,说到底是在这个边缘地带一次一次被重新生产出来的。如果种种当代文学经验出了问题,我们实际上就没有文学概念了,因为它成了无源之水,只能借助于死板的文学史、学术史、或文学概论式的教条苟延残喘。这样的文学概念自然是没有生气的、没有内在问题、没有内部的紧张感和问题性的东西,只能是个伪文学的概念。而当代文学生产出的文学概念则是有机的,总体性的。它最终是政治性的文学概念,因为我们所有的生存危机凝聚在当下,文学和这种存在的危机是共生的,它们在同一个空间里。所以我的第二个观点,就是当代文学研究通过批评不断地为文学提供定义。
这个“文学”包括文学的分析,文学的阐释和文学史的写作这三层含义。这里可以稍微展开一点点,被定义的文学是什么呢?是文学的单纯的文本性,当我们第一次面对文本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今天上午所谈论的格非——我还记得我第一次面对格非的文本,我之前并不知道格非这个作家,某天香港三联的编辑林道群忽然从香港寄来一本书,格非的《迷舟》,请我为香港的《八方》杂志写一篇长篇评论。我那时对格非一无所知,面对这样的文本,第一次去看,那个感觉是非常奇妙的。我有时候怀旧,怀的是第一次面对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不确定的文本的旧。在当代性的问题里面,我们直接可以面对文学单纯的文本性,它的陌生性,不确定性,它的绝对的个别性,不受任何文学史、知识结构、意识形态干扰。与此同时,这时候我们又是被结构的,处在各种关系之中。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把这种单纯性和直接性这种当代文学的经验的原点分离出来。这种单纯性也决定了批评的单纯性,因为这样的批评是一个直接的单纯的批评,这样的批评是一个绝对的中介,通过这样绝对的中介,单纯的文学概念走向了一个文学的总体概念,也就是说它会跟社会发生关系,会跟政治发生关系,会跟我们自己的潜意识、无意识、焦虑等等的一系列意识形态的,所谓的政治无意识发生关系。但发生关系的前提,是文学变成了文学研究的材料,意识形态批判的材料,它的前提是要经过单纯的批评的中介,而这个单纯的批评的中介的前提,又是要有文学的单纯的文本性,而这种单纯的文本性又必然是被当下这种经验方式决定的。

格非《迷舟》,作家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昨天晚上跟蔡翔在咖啡馆聊天时谈到今天的圆桌讨论会该怎么开,他问了一个关于“批评的中介”的问题,蔡翔对我说,你要把当代文学最后落实、植根于批评,是不是想从批评里开拓出一个当代文学的空间,开拓出当代文学史的空间,一切都基于批评?我说确实这样。这是我第三个希望能引起讨论的观点,就是批评是第一性的,文学史是第二性的。我在另外一个场合,在谈鲁迅的时候我也曾半开玩笑地说,如果硬要分学科的高下的话,那么美学,即康德意义上的判断力、审美判断是一级学科;文学批评是二级学科;文学史只能是三级学科,因为文学史在文学或判断力的范畴里已经比较边缘,一大半已经在知识领域,而非判断力领域。但蔡翔马上提出一个疑问:如果批评这么关键,这么重要,这么核心,那么批评的前提是什么?凭什么批评,拿什么批评?批评的原动力又是什么?要详细地回答这个问题会说得非常复杂,但我今天可以把结论直接跟坦白一下:我觉得批评最根本的前提,就是存在的政治性。我们面对文本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时代存在自身的政治性决定了我们的批评冲动,不然的话没有必要去批评。我们不妨想想30年代左翼作家和批评家,他们为什么会进行文学批评的活动?是因为他们在一个大的政治环境里面,需要有政治性的行为、判断和行动。这种存在的政治性把一切都调动起来,因为你对一切都有一种牵扯到利害、美丑、真伪、对错的关心。我们今天同样如此:存在的政治性决定批评。以这样的政治的甚至是意志论的方式谈当代性和当下,人们或许要问,难道你的当下不会整个是一个错觉或错误吗?有什么能保证这个当下和你对这个当下的投入不是个错误?还有什么比“过去”“知识”和“历史”更安全呢?这确实曾是尼采的问题,即这个被当作存在本身接受下来的当下会不会整个就是一个幻觉?也许这个问题是跟哈姆莱特关于人死以后还会不会有噩梦的问题一样没有解。对这样的质疑,我想我们只能从另一个角度来回答,即把它还原为存在的政治性本身。所有的危险其实都在这里,因为谈政治性就不得不面对可能的错误。这不是会受惩罚和处分这个意义上的错误,也不是有可能会遭受重大经济损失意义上的错误,而最终是一个生死问题。牵扯到政治范畴,人犯的错误就可能是致命的错误,你的存在就可能会被毁灭,这个意义上的错误也许不是个人在有生之年可以克服或被宽恕的,而错误的代价可能是你的全部的存在。因此这个“当下”的确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但当代文学最有意思的地方正在于它是一个不安全的领域,而脱离当下的东西都是一个安全的:历史、知识、文化、理论、观念,都是安全的,但当下或当代性是个不安全的,它需要我们用自己的整个的存在去努力、去判断,去行动。当代文学内的政治性和文学性,都来自这种努力、判断和行动。
对当代和当代性的强调尽管最终是政治性的,但它离不开对历史复杂性把握。我非常同意蔡翔所说的要避免凭感觉,凭印象,凭小聪明和即兴的灵感去界定当下。感觉有肤浅的感觉、深刻的感觉,但即使是再深刻的感觉,海德格尔式的感觉,它还是一种感觉,一种所谓的决定主义(decisionism)。所以我们对存在主义的批判其实非常好。但这个问题并不复杂,而原因正因为任何对于当下的形而上学的、审美的、判断意义上的定义最后都会被无情的带入历史。尼采要价值重估一切,但尼采现在自身已经是历史的一部分了,是现代性历史的一部分了。我们刚刚谈到的关于“当下的错觉”问题,我想借此回到刘复生上午的发言。我觉得这个发言很有意思,也很有启发性。对先锋文学的批评,是我自己批评活动的开始,而格非、余华、苏童这些人,我是把他们作为同代人来看的。我在文学史的意义上,我们当时对于先锋派的把握,的确是对于一个“当下”的把握。那个当下是有未来指向的,是有政治性的,甚至是有真理性的,它表明的是我们个人的存在、对世界的想象、对未来的期待,对某种历史真理性到场的兴奋。它早已不只是一个文本的问题,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批评和文本的合谋,而是一个更大意义上的文本和批评的合谋,即批评与一个时代根本的政治可能性的合谋。但在今天,我觉得先锋文学在80年代后期所表象的当下的真理,在今天只有神话意义了,因为在今天很难不把它看作是某种主流意识形态——个人自由,私有财产,等等——的想象性的符号预演。正因为是想象性的审美预演,所以它在当时仍然是“非功利”的。但在今天,它的非功利性和形式创新色彩就不得不被放在一个历史语境里,作为一个大的历史趋势的注脚来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很同意刘复生的阅读,那个时候的当下在今天已经被历史化了。这是对当代性的冒险和自我神话倾向的历史批判的克服。刘复生的文章里还引了我早先的一段话,我都忘了自己在80年代,在激赏几个同代人的写作的时候,还说过那么刻薄的话——我说这些先锋派的小说家,他们想象和经营文本自律性的方式,其实同个体户、小老板经营私有经济蚕食公有经济,建立自己在经济领域的尚未充分合法化的自由的方式是差不多的。在没有私有财产权、没有国际化、没有全球化的时候,在文本里已经游戏性地出现了,这是康德意义上的审美愉悦。但是,在今天,一切已经昭然若揭,一切已经在充分历史化的过程中被充分政治化,我们还能够为那种审美游戏作什么样的辩护?当我们已经可以通过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严格分析把“自我意识的童话”理解为“私有财产的神话”的时候,我很想问复生和晓明,也想问自己,这些文学经验究竟在文学史材料之外给文学留下了什么?如果先锋派只不过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神话,只不过是当时的一种中产化的以艺术自律的形式,语言游戏形式的一个预演,那就很可悲,因为那说明我们的文学最后只有历史意义而没有文学意义。而当代文学的内部张力是一方面要把文学历史化,另一方面是要在历史化的过程中为文学作出一个解释,什么是好的文学,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什么经验,这个经验不只是要强调我们曾经多么想做中产,而是要在今天一部分人终于已经做到了的时候,回过头去审视我们个人奋斗和集体奋斗的轨迹,看看那些东西仍让我们自豪,而哪些东西让我们羞愧难当。我的意思并不是当代文学一定要给文学史流下一些正面的东西,而是说我们如何在文学的当下性中,不断地提示出文学和存在的可能性。
一个常见的关于当代文学的质疑,是当代文学缺乏伟大作品,以至于它不值得我们为之付出过多的精力。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简单:我们谈的不是《楚辞》《红楼梦》或鲁迅作品是否在价值上超过同代人的作品,我们谈的是即便经典文学的判断,仍旧来自当代经验对传统的接受和理解,而这种当代的接受和理解同接受和理解的当代的意识和经验出自同一个时空。至于伟大的文学怎么来,今天的中国文学何处去,还有没有“真正的文学”,大众消费意义上的虚构作品、网络写作还算不算文学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我觉得,我们根本不需要考虑。我前面提到文学的单纯的文本性,前提就是我们要承认它单纯的自发性,只要我们承认存在是政治性的,存在是一种斗争,是一种想象,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指向未来的冲动,那么这种政治性的存在就一定会找到文学,找到不满足于现状的东西、指向内心的东西。如果我们承认基本的存在的政治前提,文学就是这种存在斗争的一部分,它的命运不用我们去操心:文学会有的,伟大的文学会有的,虽然不一定在这个月或今年,甚至不一定在这个十年或下个十年,但这不是我们该操心或能操心的事情。现在有多少人写小说读小说,还有多少文学刊物,有多少文学奖,这不是我们需要关心的问题。同样,读者最多的东西并不一定是文学,韩寒安妮宝贝之类,并不在我们讨论的文学范围之内,而实际上是属于大众娱乐和文化工业,倒是同时尚、传媒、消费等归在一类,值得研究,但它们并不需要文学研究的方法和方式。
最后,我想回到当代性自身的时间构造问题。这里面又分两点,一个是它的时间构造。当下虽然是一个瞬间——永远的“此刻”,这是我们当下最严格的定义——但是这个瞬间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瞬间,这个当下的概念之所以能够确立,是因为这个瞬间必然已经是一个构造,这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这个瞬间只能是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紧张关系中形成的。也就是说,一个激进的当代概念,不仅仅明确地来自一种历史意识,而且能够把历史意识激进化,也就是说,把变成当代问题的内在组成部分。每一个“当下”都要被历史化,但每一个当下在出现的时候,当它把自身同历史分离开,对立起来的时候,都改变了历史本身,改变了历史化的整体格局。这是本雅明所说的“历史天空的星座”的含义。更进一步地说,也就是第二点,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当代的未来指向。当代文学和文学史的关系是非常暧昧的,因为当代性既要把自身非历史化,又要产生出自己的当代文学史,要把自身历史化。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不会被历史化掉,不会在被历史化、文学史化的过程中完全被消解掉的,或者被完全异化的,这就是当下始终的未来指向。当下对下一个瞬间的开放性,是任何文学史都没有的,现代文学没有,古代文学没有,或者任何文学史化的对文学的理解也不包含这个东西,只有当代文学,最严格意义上的当代文学、批评意义上的当代文学,直面文本的,直面文学生产的政治性的文学概念始终包含一个强烈的、根本性的未来指向。我想这是当代性和当代文学的一个终极含义,也是它最终回到历史的唯一通道和全部意义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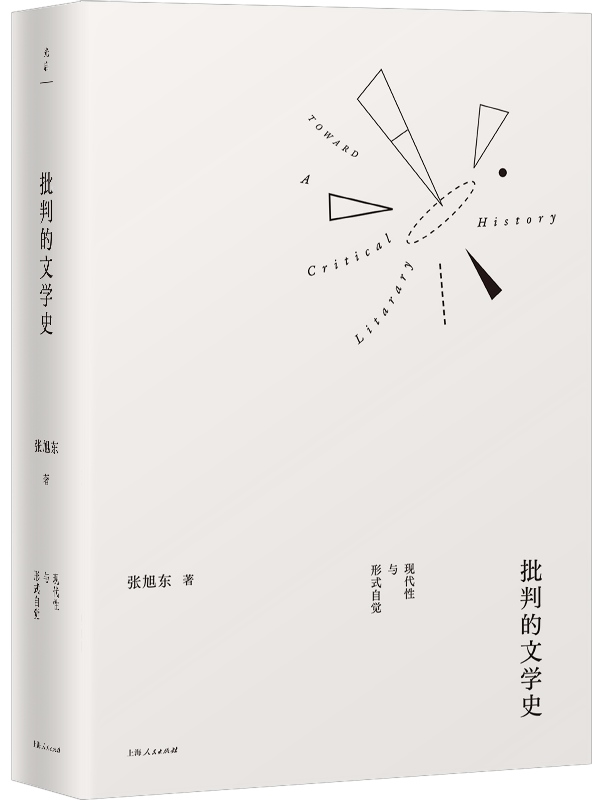
《批判的文学史:现代性与形式自觉》,张旭东/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2020年11月版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