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图书2020|2020年巫术类著述经眼录
我去年曾整理《2019年巫术类著述经眼录》,得到了一些师友的肯定和支持,今年勉强接续去年的工作,整理2020年巫术类著述书目。需要特别交代的是:以下书目,仅是本人有限的阅读范围所及,而未及寓目的相关著述定然不少,决非有意忽略之。2019年岁末所出版的著作,未及列入去年书目者,也尽量补入。本书目抱持“宁滥勿缺”的原则,修订、重版、重印的著述,以及书中部分涉及巫术内容的著述,也尽量搜罗其中。每本书下零星有所点评,乃是仓促浏览后的粗浅看法,自然是挂一漏万,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正之。
一、西方巫术类译著
1.《巫师:一部恐惧史》
[英]罗纳德·赫顿(Ronald Hutton)著,赵凯、汪纯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9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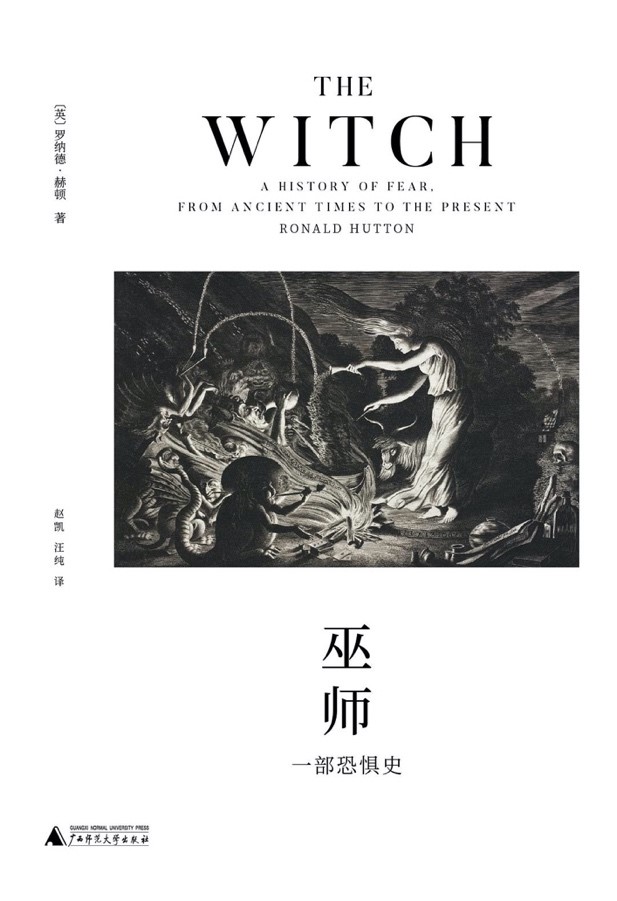
英国学者罗纳德·赫顿(Ronald Hutton)花了25年时间写成的《巫师:一部恐惧史》,是西方学界有关巫术研究最新的集大成之作。本书首先梳理了学术史上有关巫师的几种看法:一是“以神秘手段伤害他人的人”;二是“使用魔法的人(为了有益的目的而使用魔法的人通常被称为‘好巫师’或‘白巫师’)”;三是“某种基于自然的非基督宗教的修习者”;四是“独立女权和反抗男性统治的象征”。本书采用的是第一种定义,即把巫师用来指称“使用破坏性魔法的人”,而将其他把巫术用作善意目的的人称为“服务型魔法师”(service magician)。本书又列举了巫师的五种类型特征:巫师以离奇的方式造成伤害;巫师对社区内部造成威胁;巫师施术有某种传统;巫师是邪恶的;巫师可以被抵抗。本书的分析,新见迭出,尤其是将巫术及巫师放置于文化、社会、社区等结构中去思考其利弊。比如说,书中专门提到猎巫事件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通过对异常或反社会行为的阻止,它可以强化文化规范,从而加强社区团结。”巫术有时会成为弱者的武器和社会的矫正剂。
尽管作者也提到他对东方巫术关注较少,但他所强调的欧洲巫术的独特性,恰可以作为比较巫术研究中的关注点。本书尤其谈到欧洲巫术的两个特点:一是“欧洲大陆的居民在巫术与本质的恶(essential evil)之间发展出了一套普遍公式(common equation),这是其他地方都没有的。他们认为巫术代表了某个反宗教的异端组织,崇拜宇宙中某种邪恶的化身。”二是欧洲“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传统上笃信巫术存在,又(至少在官方意识形态上)自发地拒斥这种信仰的地区。”欧洲有关巫术和宗教的认识,随着传教士传到中国,自然地也被运用到对中国宗教的理解上。在此意义上,此书对于研究中国巫术,亦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2.《猎巫:塞勒姆,1692》
[美]斯泰西·希夫(Stacy Schiff)著,浦雨蝶、梁吉译,上海:文汇出版社,2020年8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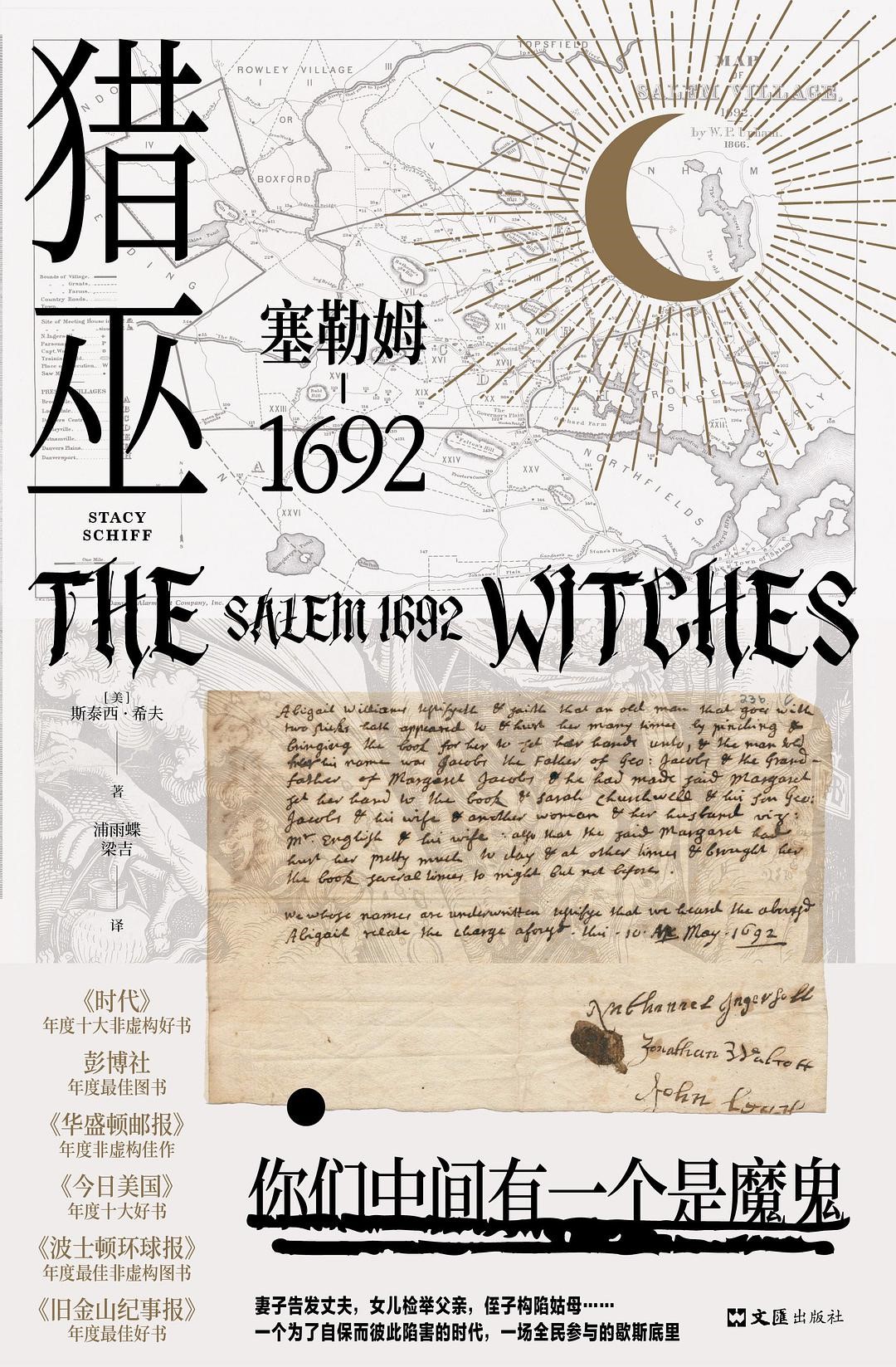
2020年出版的巫术类著作中,最受关注的当属斯泰西·希夫(Stacy Schiff)所著的《猎巫:塞勒姆,1692》。此书在美国出版后,随即登上诸多图书榜单,引起广泛的关注。中译本出版后,已有多篇书评发表。此书的魅力首先在于塞勒姆女巫案的情节如同一幕制作精良、悬念丛生、离奇曲折的戏剧,能满足现代人猎奇的兴趣。中译本的“编辑说明”就吊足了读者的胃口:
1692年的冬天,在波士顿附近的塞勒姆,一位牧师的外甥女开始抽搐、尖叫,随后他的女儿也陷入同样的状态:扭曲、颤抖、打滚、吐白沫……医生闻讯赶来,牧师查阅卷宗,邻家妇人占卜,都指向一桩古老的罪行:巫术。很快,恐慌蔓延至整个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所有人都被卷入了声势浩大的猎巫运动。邻人之间互相指控,亲子之间彼此出卖,牧师、富绅、高官也难逃一劫。这场猎巫运动历时九个月,二十余人最终惨死,另有近两百人被指控为巫师。风浪平息后,塞勒姆仿佛失忆了一般,陷入长达一个世纪的沉默。……
其次,此书的魅力还在于作者的写法,行文如同一部精彩的小说,史料考证精细入微,同时也不乏言之有理的想象力发挥,背后亦有精辟的理论分析。
3.《萨勒姆的女巫》
[美]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著,梅绍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8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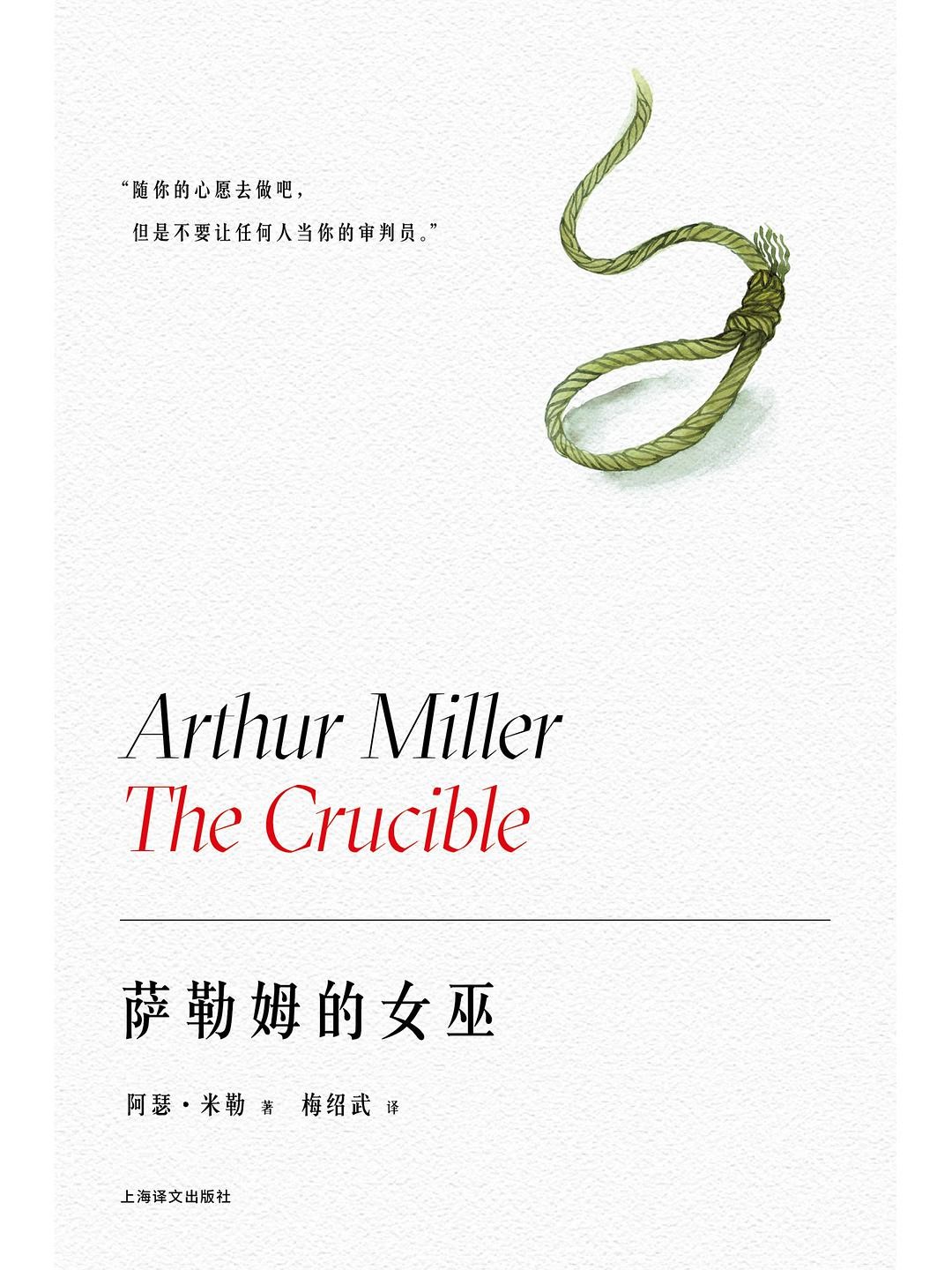
本书中译本初版于2011年,此为重版。萨勒姆女巫案的故事性和戏剧性,可由诸多据此题材创作的文艺、影视作品体现出来。在这些同题材作品中,最有名的恐怕就是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的剧本《萨勒姆的女巫》(The Crucible)了。据说米勒创作此剧是“有意识地借这部关于宗教迫害的剧本影射当时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对无辜人士的政治迫害。”但米勒本人认为此剧“具有远比只是针砭一时的极右政治更为深远的道德涵义,旨在揭露邪恶,赞颂人的正直精神。”(梅绍武《导言》)由历史事件改编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引发有关“本事”和“故事”的讨论,亦可从中观察文学和历史对于事件的不同处理方式。另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米勒曾来华访问,后来还写过一本《访问中国》。1981年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计划演出米勒的作品,他亲自推荐了这部《萨勒姆的女巫》,由黄佐临先生执导。当时中国刚走出“文革”,剧中的内容在中国观众那里得到了广泛的共鸣。
4.《巫术的历史》
[英]蒙塔古·萨默斯著,陆启宏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9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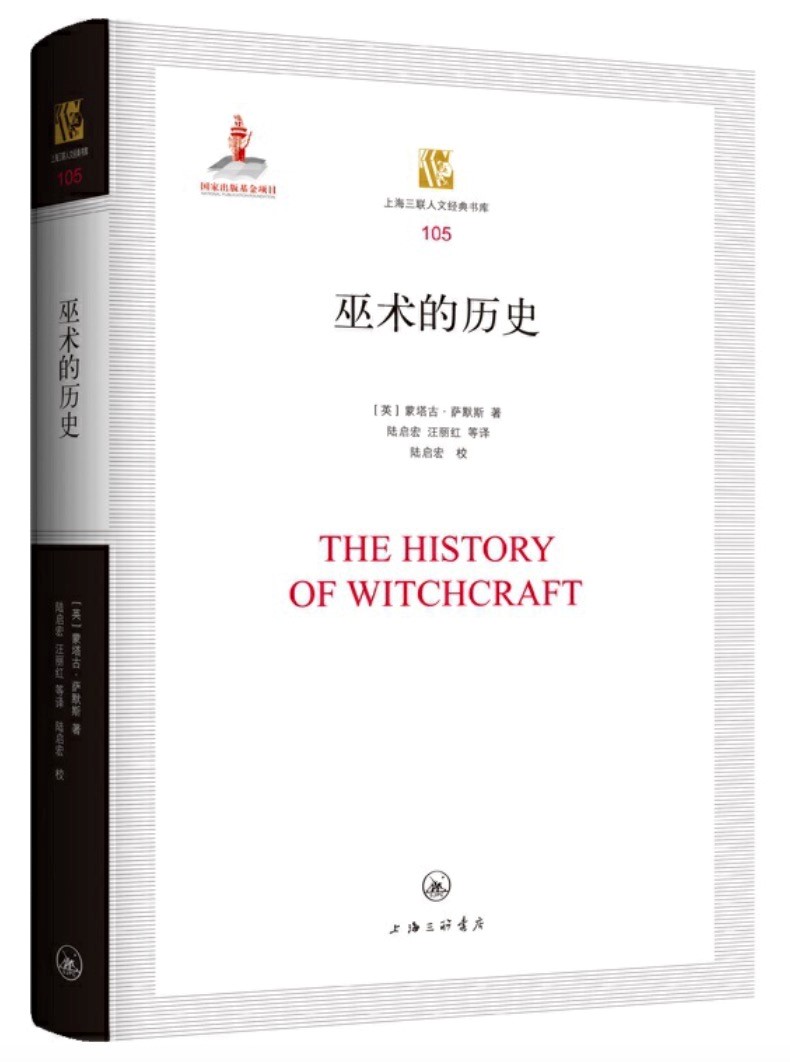
本书是一本颇具分量的欧洲巫术史著作,但本书更值得关注的与其说是其观点,毋宁说是其立场。作者是一位天主教徒,但他并不赞同天主教会在巫术问题上的官方主张。而且作者的观点与许多学者亦有不同,他自己强调说:“我与我所尊敬的一些大学者,在许多细节上有所不同。”这种不同立场尤其体现在对于中世纪猎杀女巫运动的态度上。书中多处引述的默里(Miss M. A. Murray)的观点,在学界有一定的接受度:“在巫术的名义下流传下来的是一种被基督教战胜的宗教,它的术语及对其仪式的描写都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基督教征服者将打败的宗教的核心归纳为与撒旦签订契约。”(第2页)但本书作者并不认同这一立场,而是认为学界对于镇压巫术的历史充满了偏见,而文学艺术中则又将女巫不切实际地浪漫化了。真实的女巫其实是这么一群人:
邪恶的存在者;社会的寄生虫;一种令人厌恶的、淫秽的教义的信奉者;善于下毒、勒索和犯其它罪行的人;一个与教会和国家对抗的强大秘密组织的成员;言行上的亵渎者;通过恐怖和迷信控制村民的支配者;江湖骗子;老鸨;施堕胎术者;求爱和通奸的黑暗顾问;邪恶和堕落的代理人。
在作者看来,猎杀女巫及宗教裁判所在某种程度上说有其必要性,巫术和异端往往会卷入对社会秩序的攻击,他们总是无政府主义和政治性的,异端有时是依据民法而被处死的,而非出于宗教迫害的原因。为本书做序的费利克斯·莫罗(Felix Morrow)对作者的许多观点并不支持,相反支持被作者反对的默里的一些看法。但莫罗也肯定了本书的价值:
如果我们将这样的极端言论放在一边,那么萨默斯的观点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它们提供给我们这些现代英国人罗马天主教版本的关于巫术和教会反对巫术历史的最好叙述。
5.《灵魂猎人》
[丹麦]拉内·韦尔斯莱夫(Rane Willerslev)著,石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6月版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俄罗斯科累马河(Kolyma)上游的一个西伯利亚土著狩猎小民族——尤卡吉尔人(Yukaghirs),作者以猎人的身份参与了当地人的狩猎和生活,经过了18个月的田野调查,并以此为基础写成此书。作者以“万物有灵论”观察尤卡吉尔人处理猎物和神灵的各种实践和巫术,作者写道:
对我们西方人而言,习惯上假定人的属性包括具有语言、意向、推理和道德意识,所有这些皆人之独有。动物则被理解为是一种自然物,它们的行为被典型地解释为是自发的和本能的。但在尤卡吉尔人之中却流行着不同的假设。在他们的世界,人(persons)可有多样的形式,人类(human being)只是其中之一。他们可以变化为河流、树木、灵魂和神灵,但总体上都是哺乳动物,尤卡吉尔人视之为“非人类之人”(other-than-human persons)。而且,人和动物从各自的视角可以互相进进出出并暂时取代对方的身体。
人类学对于原始文化的研究成果已有很多,但本书绝非只是在诸多案例中增加一个族群的例证而已,其中涉及到的一些问题,颇能补以往研究之空缺,比如对于尤卡吉尔人萨满信仰的研究。尤卡吉尔人的萨满其实已在20世纪70年代消失,尽管现在的生活中还有萨满文化的遗存。萨满消失的原因,主要是来自于18世纪初东正教在西伯利亚发起的第一次宗教改革,使得“东正教圣徒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古代尤卡吉尔人的神灵”,在后来的语境中,萨满被称为“撒旦”。另一个原因是社会主义思潮,以当时的社会主义立场来观察,尤卡吉尔人虽然在土著民族中最落后,但却是最纯粹、最简单和最具有社会主义特性的民族,因此被认为没有自己的萨满。斯大林时期对于宗教的系统性迫害并没有波及到尤卡吉尔人,但这种运动的威慑力足以让他们自觉放弃掉萨满信仰。
6.《魔法、节日、动植物:一些奇异文化传统的历史渊源》
[英]莫尼卡-玛丽亚·斯塔佩尔贝里(Monica-Maria Stapelberg)著,高明杨、周正东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0年9月版

这是一本视角很有趣的书,正如作者所言:“人们通常意识不到,我们日常观察和表现出的某些特定行为、姿态及礼仪规范,实际上是基于早已被人遗忘的远古信仰、仪式魔法、祭祀传统或者可怕的迷信思想。”在这些久远的历史渊源中,巫术是最重要的内容。按照弗雷泽在《金枝》中的说法,巫术分为两种类型:模拟巫术和接触巫术。相应地,这两种类型的巫术在现代社会中亦有遗存。比如说,到现在为止有些文化中还存在的照片禁忌,就源自肖像巫术。这是一种模拟巫术,其原理为:“根据某人形象制成的肖像如果受到伤害或毁坏,这个人本身也会受到相应的伤害,这是由于人与其肖像之间存在身体上的同感。”在历史中,经常有破坏他人人像或人偶以达到伤害他人的巫术事例。在照相术产生的初期,有关照片神秘性的观念,亦与之有关。许多文化中,“人们处理自己的身体代谢物时十分谨慎”,这源自接触巫术的观念。西方曾流行君主触摸治病,也是一种接触巫术,这一现象在马克·布洛赫的《国王神迹》一书中有充分的探讨。本书也谈到了这一事例的巫术观念基础:“人们认为,君主和统治者至高无上的地位给他们带来了与众不同的、卓越的能力。因此,君主和统治者被认为拥有治愈能力,而一般百姓认为,这种治愈效果可以通过触摸传递到自己身上。”(9页)书中提到的例子非常之多,如打喷嚏禁忌、刀叉不能交叉放置的习俗、影子禁忌、名字巫术等,都是现代人所乐于了解的。
7.《自然史》
[古罗马]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著,李铁匠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8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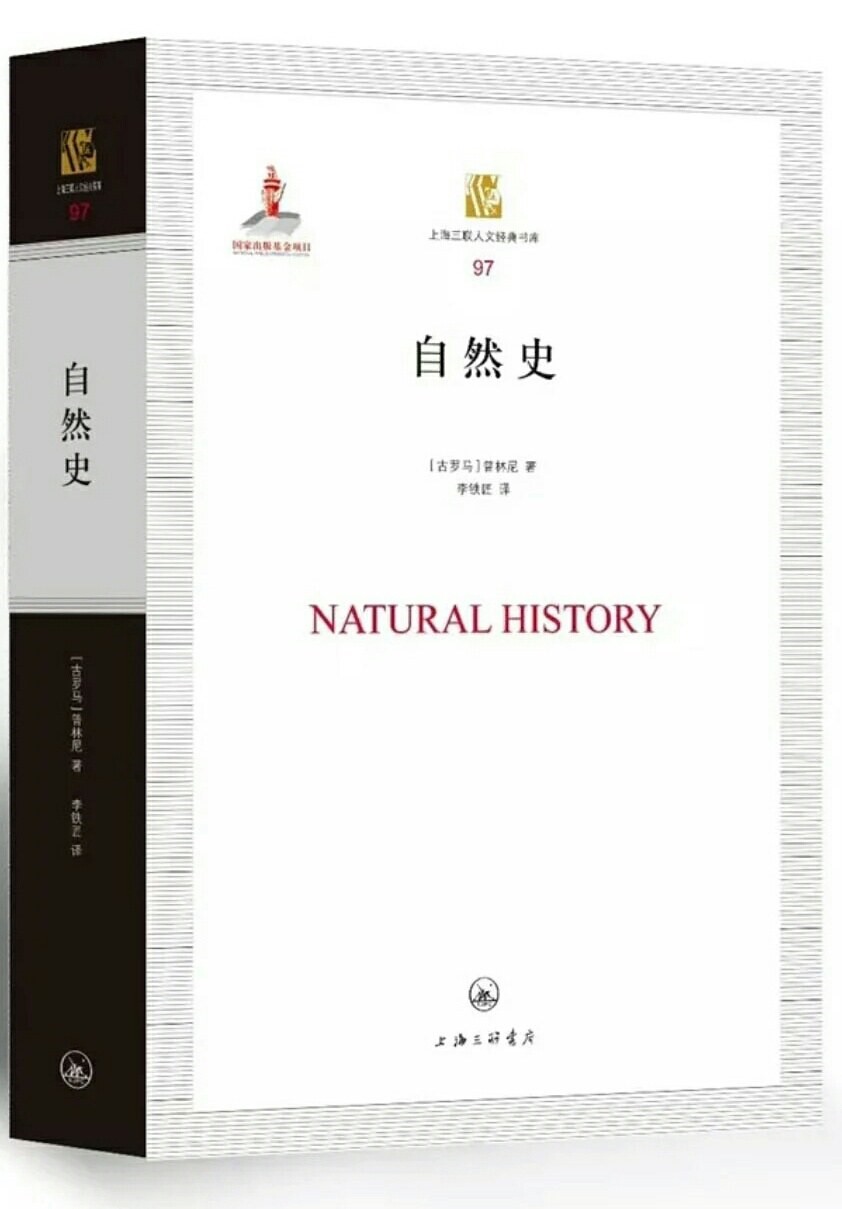
老普林尼的《自然史》是名副其实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该书引述的学者有473位,引用资料达34707条,涉猎广泛,非现代某一个狭隘的学科可以容纳。至20世纪,《自然史》已有222种译本。此书涉及巫术的内容不少,尤其是第三十卷专章论述巫术。他提出巫术是以“三重镣铐控制着人类的情感,即医学、宗教和占星术”:
没有人怀疑巫术起源于医学,也没有人怀疑它是打着促进健康的旗号偷偷地、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的。它似乎是医疗艺术更高尚和更神圣的形式。它以这种方式获得了宗教界诱人的、无限的允诺,而即使现在,宗教对于人类而言,仍然是一本合上的书;此外,它还控制着占星术,因为没有人不渴望知道自己的命运,也没有人不相信最准确的方法就是观天象。因此,巫术以三重镣铐控制着人类的情感,竟然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以至于今天它还有力量控制着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统治着东方的众王之王。(第291页)
普林尼对巫术的态度很清晰:“巫术是虚假的,不论在何时、何理由或何原因,它们都是虚假的。”(第291页)“巫术坏透了,它什么也得不到,毫无用处。”(第295页)书中其他地方散见的关于巫术的内容亦有很多,可使我们得以窥见那时的生活和文化。
8.《通灵者之梦》(第二版)
[德]伊曼努埃·康德著,李明辉译,新北:联经出版公司,2020年4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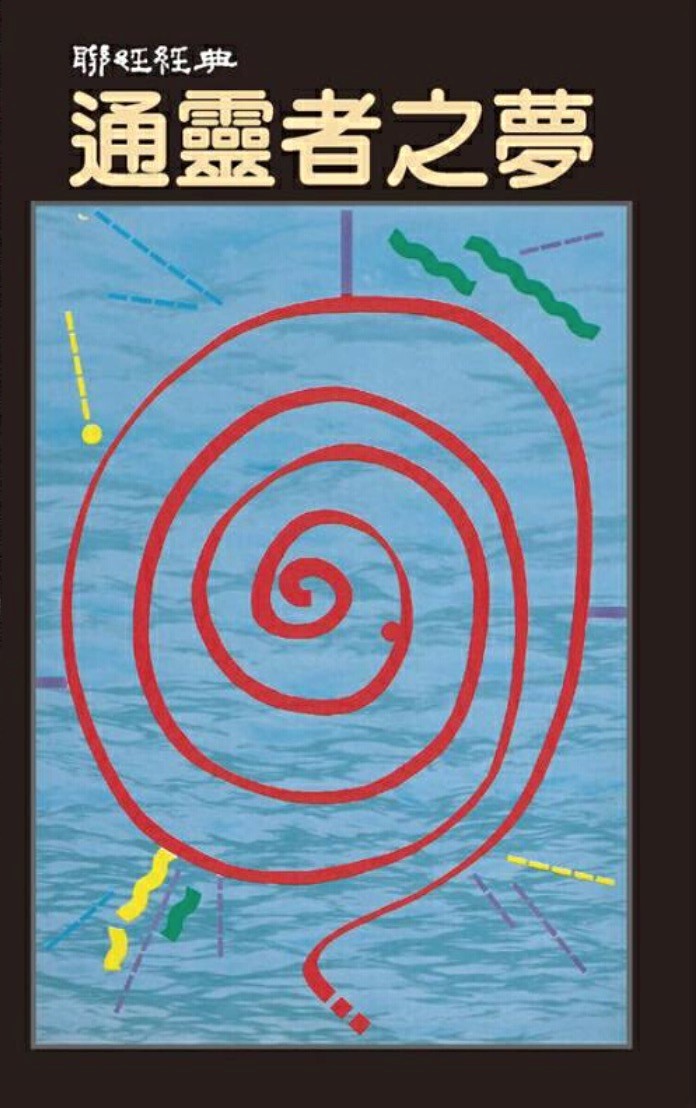
康德的《通灵者之梦》,是一本在康德诸多名著中不太受关注的小书。台湾的联经出版公司在1989年出版了李明辉先生的中译本,这也是第一个中译本。李秋零先生翻译的《康德著作全集》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收录了此书,译名为《一位视灵者的梦》。联经出版公司2020年推出了李明辉先生译本的第二版。本书是康德在看到瑞典通灵者史威登堡(Emanuel Swedenborg)通灵事迹之后的即兴之作。史威登堡是当时知名的科学家,晚年在经历了一场信仰危机后,走上了神秘主义的道路,自称“上帝赋予他异常的禀性,可随意与死去的灵魂交通。”并把这些神异之事写成了八巨册的《天上的奥秘》(Arcana coelestia),在当时颇有影响。康德看了此书之后,深觉受骗,于是写了这本《通灵者之梦》。此书的主旨正如李明辉先生总结的:
康德在此书中故意将形上学家与通灵者相提并论。在康德的全部著作中,此书的风格是独一无二的,其笔调亦庄亦谐,类乎游戏之作。但在其讽刺性的笔调背后,实寓有极为严肃的意义。此书一方面批判西方传统的形上学,而重新规定形上学的任务与界限,并且为之寻找新的基础;另一方面则试图为知识、信仰和迷信三者划定界线。它包含康德日后形成的批判哲学的基本哲学构想。
9.《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法]涂尔干著,渠敬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6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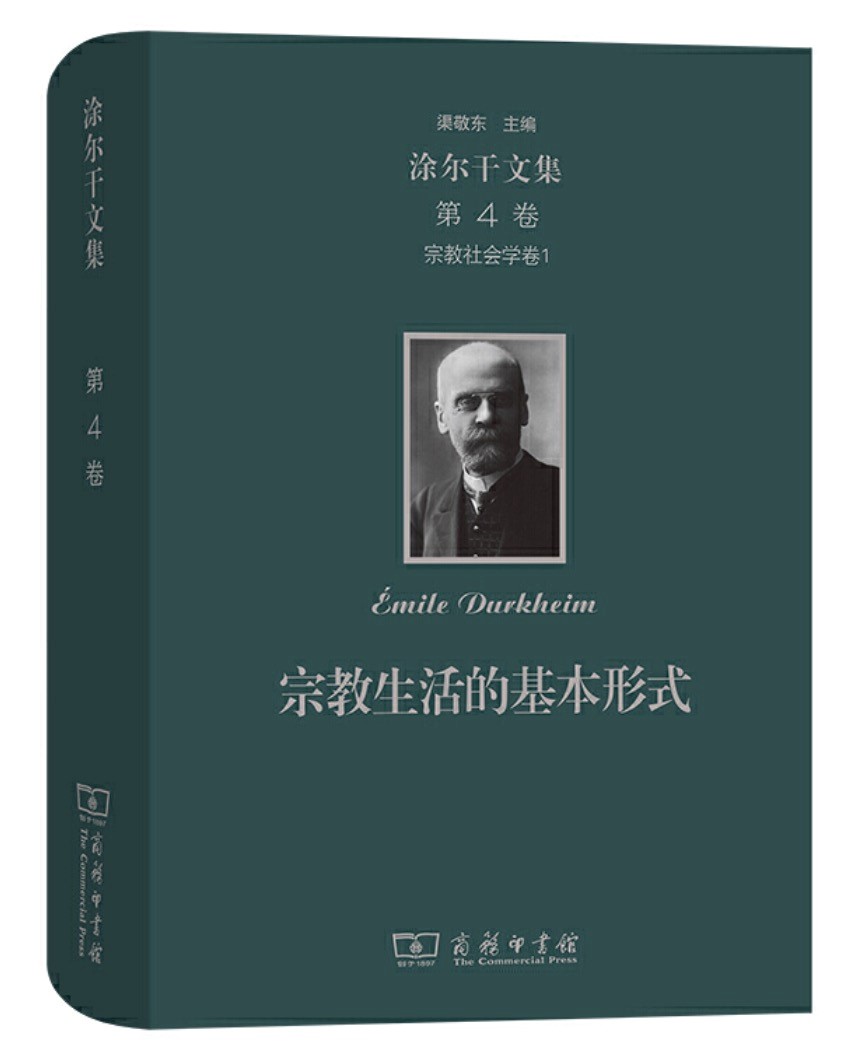
本书中译本已出版多年,今年收入“涂尔干文集”再版。《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是一部学术名著,广为学界所知。在涂尔干看来,巫术与宗教有诸多相似之处,如信仰、仪式、神话、教义等,“巫师所乞求的存在及其所调动的力量,与宗教所专注的力量和存在不仅性质相同,而且往往是一码事儿。”(第54-55页)两者之间真正的区别在于,“真正的宗教信仰总是某个特定集体的共同信仰”,但巫术虽有追随者和普遍性,但“这并没有使所有巫术的追随者结合起来,也没有使他们联合成群,过一种共同生活,不存在巫术教会。”(第57页)巫术所缺少的就是宗教那样的共同体。正是在与巫术的对比中,涂尔干提出了他关于宗教的定义:
宗教是一种与既与众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与仪轨所组成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与仪轨将所有信奉它们的人结合在一个被称之为“教会”的道德共同体之内。(第60页)
10.《北欧神话:世界开端与尽头的想象》
[德]保罗·赫尔曼(Paul Herrmann)著,张诗敏、许嫚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0月版

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没有处在欧陆历史舞台中心,再加上基督教直到11世纪左右才传到这里,所以“北欧神话有足够的空间发展,产生显著的变化,并且获得重生。”(导论)在很大程度上,基督教所覆盖的地方,其原有的神话与巫术都会逐渐被压制、吸纳和转化,而在北欧这样的地理和文化环境中,神话和巫术都得以充分发展,“在长久且缓慢的发展中,北欧人已经知道如何天马行空地想象他们身处的大自然,使其更加生气蓬勃,并将其中的图像氛围以韵文的方式相互联结,优美地呈现于诗歌中。”(第9页)如女巫传说,广泛地存在于北欧神话中,女巫可以是死者的灵魂,也可以是现实中的女性,女巫有着变形的能力,也能通过灵魂出窍附身到其他生物上:
作为死者的鬼魂,正如其他灵体,女巫特别会在沃普尔吉斯之夜(Walpurgisnacht)、5月1日,或是施洗者约翰节前夕,甚至在隆冬之时,跑出来到处作祟,她们会召唤恶劣天气、狂风、骤雨、冷气团、闪电、雷鸣、冰雪以及酷热,侵袭田地和牧场。霜害冻坏花朵、冰雹摧毁谷物、瘟疫肆虐农民或牧人的牲畜,人们会把这些现象归咎于女巫的法术。……到现在仍然有民间信仰相信这种女巫的存在。(第62页)
北欧的文学以想象力著称,神话就是其生长的土壤。
11.《稻、鸟和太阳之道——追寻日本文化的原点》
[日]荻原秀三郎著,李炯里、刘尚玉译,贵州:贵州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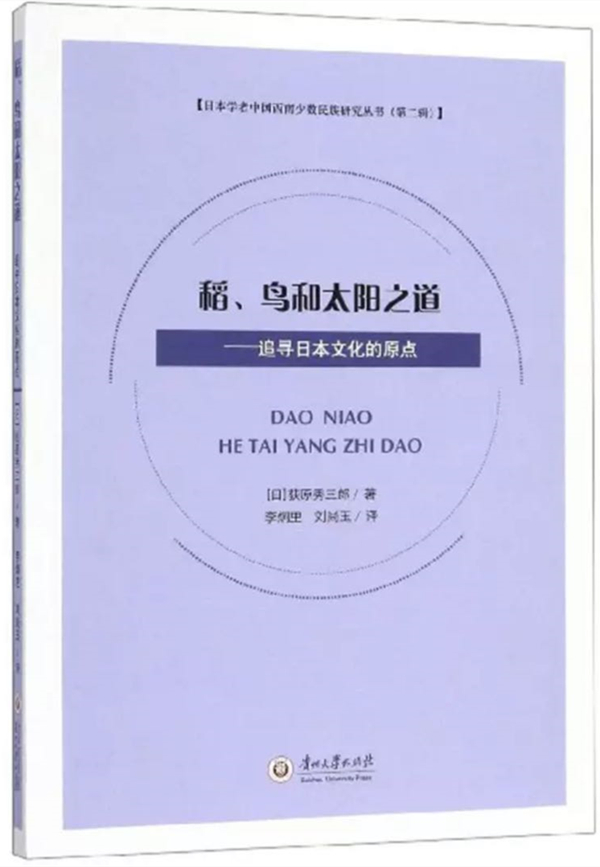
本书认为日本文化是以稻、鸟、太阳为原点的复合型文化。日本稻作文化源自中国云贵地区,太阳信仰(如射日神话等)在东亚地区有一定的相似性。书中专门分析了日本常见的鸟装习俗和鸟巫现象,“鸟能在天空中自由飞翔,所以被认为更容易到达祖先灵魂,和神灵居住的世界。同时也被看作是神的使者,能运送灵魂,因而倍受崇拜。”(第6页)作者还认为东亚巫术在谱系上存在着关联性,通古斯的萨满教与中国文化相互影响,“对于西伯利亚的巫师来说必不可少的铜镜和铃不正是从汉代流传而来的东西吗?也就是说包括东北亚和朝鲜、日本在内,萨满教的文化应在中国寻根问源。”(第72页)作者有着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书中提到的许多习俗,让本书读起来颇为生动有趣。
12.《黑魔法手帖》
[日]涩泽龙彦著,蕾克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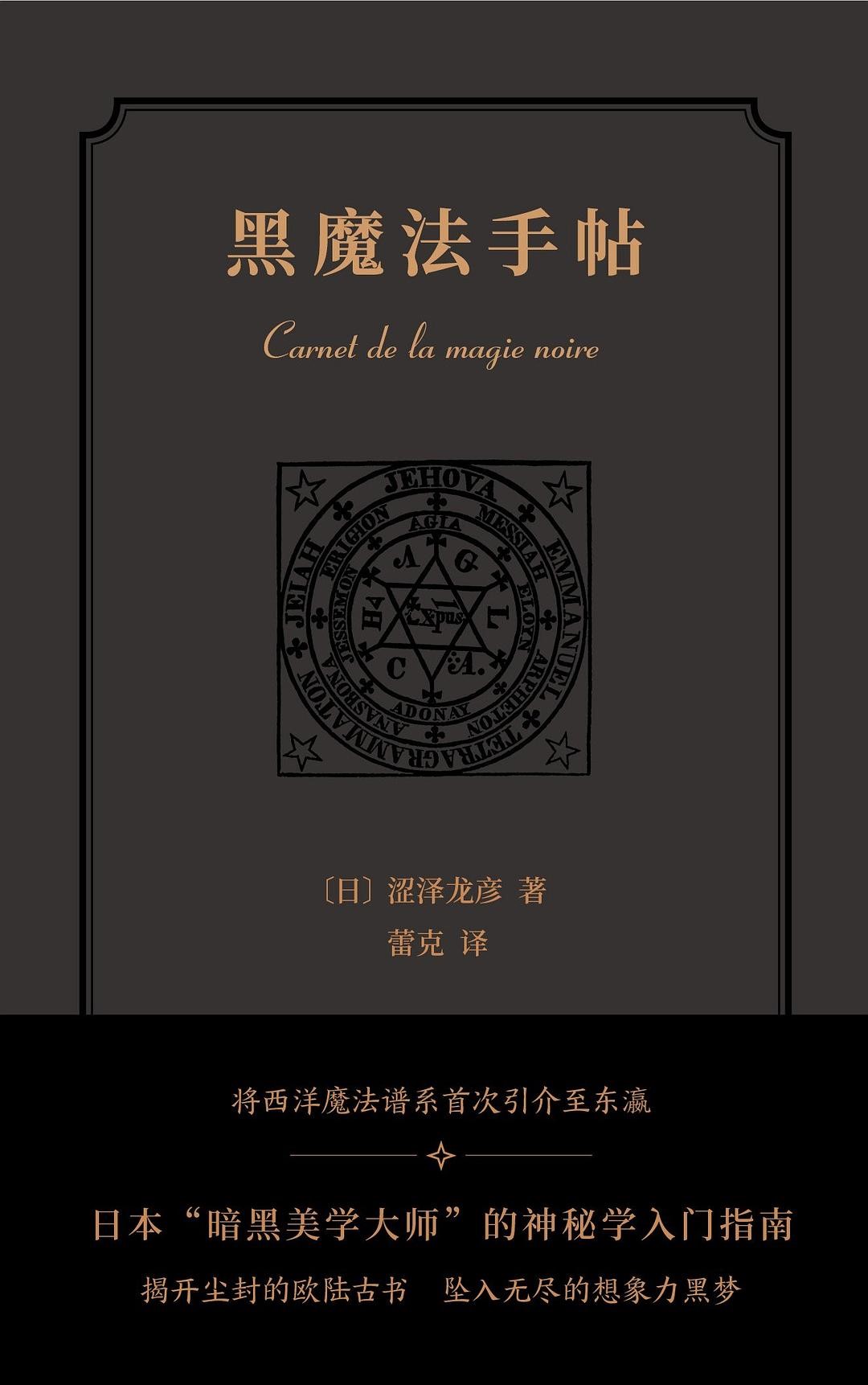
近几年,涩泽龙彦有多种著作被译成中文。涩泽龙彦被称为“暗黑美学大师”,本书被称为其“神秘学入门指南”,三岛由纪夫曾评论此书,充满“职业杀手的纨绔主义(Dandyism)”。书中除诸多神秘学的内容,巫术占据了较多的篇幅。如其中专章论述“巫魔会幻景”,这是在西方巫术史中经常谈及的话题。尤其在猎巫运动中,女巫被认为能在夜间飞行,去参加巫魔会。流传下来的关于巫魔会的资料,“几乎都是宗教审判时的巫师自白,其中大部分又是在严刑拷打下的胡言乱语。与其说是自白,更像是巫师在混乱之中产生的幻觉和迷梦……所以,所谓‘巫魔会’,也许只是昏迷谵妄导致的痴梦幻想。而近代的鬼神论者们,却努力想把这种状态解释成借助灵媒等神秘之力后的浮游飞翔。”(第92-93页)这些光怪陆离的内容,对于现代人来说,充满着猎奇的趣味。
13.《成神:早期中国的宇宙论、祭祀与自我神化》
[美]普鸣(Michael Puett)著,张常煊、李健芸译,李震校,北京:三联书店,2020年1月版

在这部极富反思精神的著作中,作者首先梳理了自马克斯·韦伯以来有关中国研究的两大范式:理性化与特殊化。前者将理性作为历史演进的标准,后者则强调中西文化各有其特殊性。这两种范式分别以冯友兰和葛兰言为代表。此后两种范式又在进化论模式(雅斯贝斯、史华慈等)和文化本质主义模式中得以发展。尤其是文化本质主义死模式,继葛兰言之后,又在李约瑟、牟复礼、张光直、葛瑞汉、郝大维、安乐哲那里得以发展。此处难以对其中复杂的脉络做详尽梳理,但需强调的是,在文化本质主义者那里,中西之间存在着文化和思维的根本差异,前者是关联性思维,后者是分析性思维;前者是连续性文明,以萨满式宇宙观为基础,后者是断裂性文明,发展出了西方特有的文化与宗教。有关萨满的理论,伊利亚德曾有系统性地阐述,张光直、秦家懿等学者以此来阐释中国早期文明,在学界有较大影响。本书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反思。书中涉及到的关于巫术的诸多话题,都值得做进一步的专门探究。
14.《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占卜与表意》
[法]汪德迈(LLéon Vandermeersch)著,[法]金丝燕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0年10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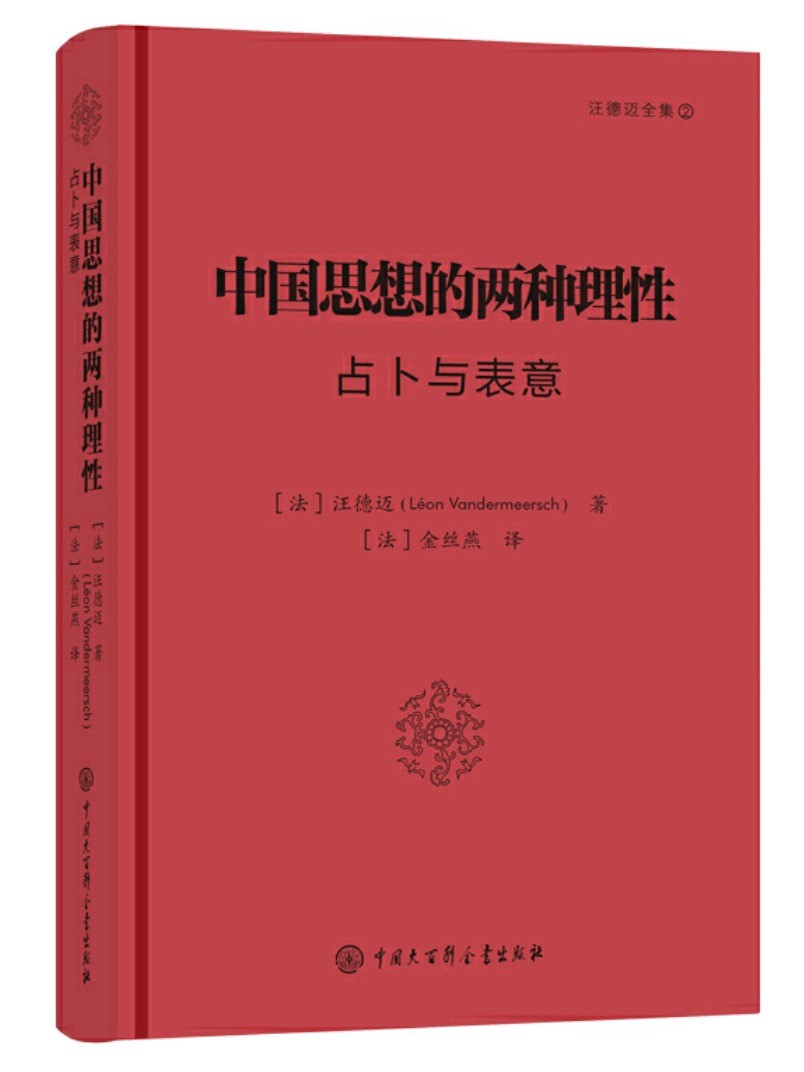

本书2017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此次收入“汪德迈全集”,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修订再版。汪德迈是法国著名的汉学家,关于中国研究的成果颇多。本书所论述的核心问题,就是从中西文字的不同起源和特征,来看文化和思想间的差异。在书的开头作者就提到:
此书就如下论题展开:中西文化间有着深度的不同,两者尤因表意文字与字母文字相去甚远而相异,其对立之源在于,中国一方,思想最初以一种极为讲究的占卜方程式为导向,希腊—拉丁并犹太—基督教一方,思想最初以宗教信仰为导向。(第1页)
在作者看来,中国文化最深的根基就是表意文字,基于此形成了关联性思维方式,这与西方的因果思维不同。早期中国文化受到萨满教的深刻影响,萨满师即是甲骨时代的占卜师,萨满师将巫术信仰理性化为占卜学。萨满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乃是因为萨满的作用被国家化了,萨满从而承担了类似其他国家神职人员的作用。本书由文字比较上升到文化与思维模式的比较,有不少分析颇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二、中国巫术类著述
1.《中国方术考》及《中国方术续考》
李零著,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12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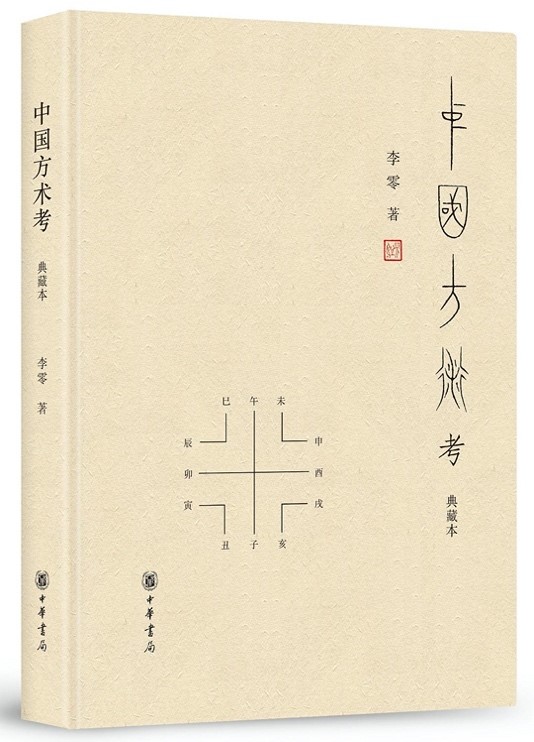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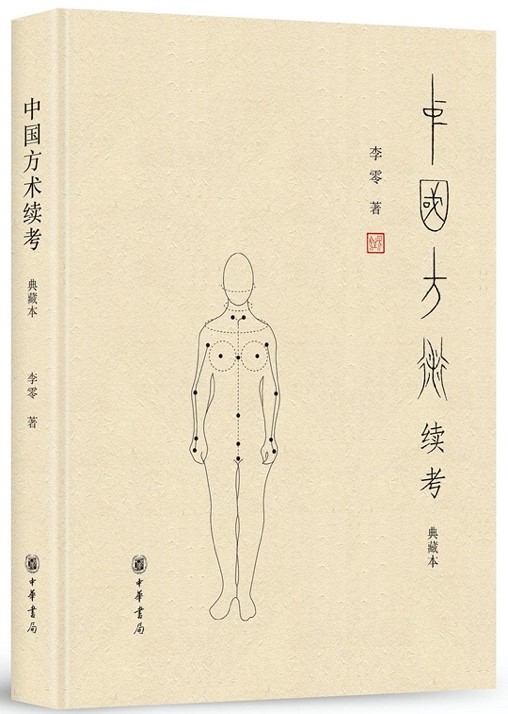
2019年末,中华书局推出李零先生《中国方术考》和《中国方术续考》精装“典藏本”。从文字上来看,较之此前中华书局2006年版,并无变化。《中国方术考》初版于1993年(人民中国出版社),2000年由东方出版社推出修订本,并同时出版了《中国方术续考》。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新的修订本,只是《中国方术考》改名为《中国方术正考》。2019年的“典藏本”则改回原名《中国方术考》。
李零先生在“新版前言”中提到,自己写过十几本书,这两部书是其代表作,其特点,“不夸张地说,用考古材料填补空白,系统总结中国早期的方术知识(主要是战国秦汉的方术知识,或道教、佛教以前的方术知识),这是第一部。”这部书在中国巫术研究的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巫术研究,始于晚清民国时期,刘师培、王国维、周氏兄弟等开其端,巫术研究在民国时期亦出现一段热潮。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这段时期,巫术研究基本被排除在正常的学术研究之外。而在八十年代之后,随着当时出现的文化热,巫术研究重新兴起,出现了一批有份量的研究著述,如裘锡圭《说卜辞的焚巫尪与作土龙》(1983)、宋兆麟《巫与巫术》(1989)、张紫晨《中国巫术》(1990)、王振复《巫术:周易的文化智慧》(1990)、高国藩《敦煌巫术与巫术流变》(1993)和《中国巫术史》(1999)、李泽厚《说巫史传统》(1999)等。李零先生的《中国方术考》(1993)及其后续的研究,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对后来的巫术研究影响深远。
2.《人鬼之间:宋代的巫术审判》
柳立言著,上海:中西书局,2020年10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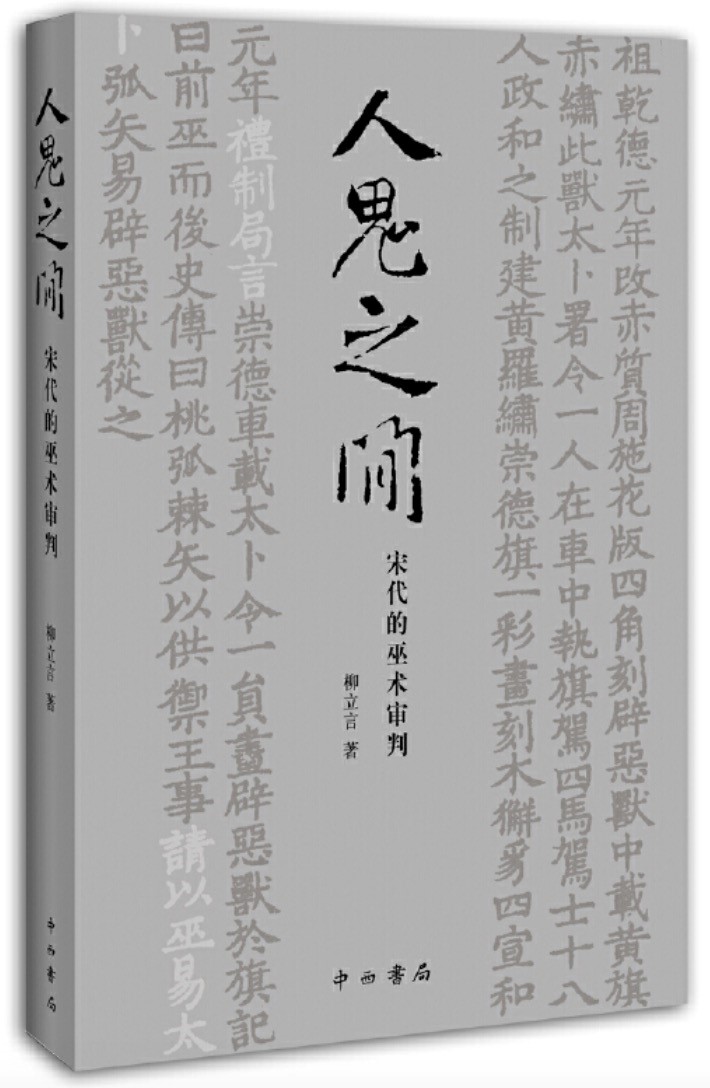
就中国巫术的断代研究而言,宋代大概是被研究最多的朝代。本书为宋代巫术研究的最新力作,作者精于法制史研究,以此学术背景来研究宋代有关巫术的法律政策和判例,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全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宋代是否禁巫?依照作者的考察,关于宋代禁巫的说法,起自日本学者中村治兵卫,其后学界多沿袭了这一判断。但本书作者意在申明,“宋代在立法上不曾禁巫,我们不能把局部看作全部,把政府禁止巫的某些非法行为视为禁巫。”(本书70页)作者主要的论证方法是辨析“巫”的群体构成,按照行使巫术功能的角度来说,巫大致包括僧尼、道士、术士等,而并非只是狭义的巫觋。“宋代所打击的,不是巫教作为一种民间宗教,而主要是某些巫师的非法行为,如诳惑、淫祀、异行和妖术等,只能泛称为‘惩巫’(其实是惩罚坏巫)而非‘禁巫’。”以此来看,“禁巫”所禁的乃是某些不当的巫术行为,而非所有的巫,所以“禁巫”之说难以成立。这一论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改变学界对于宋代巫术的一些认知,至少可以提醒学界关注某些被忽视的角度。但作者的观点或有可值得商榷之处,作者所理解的“禁巫”的“巫”,似仅指狭义的巫觋而言,真实语境中似乎可做广义的理解,将此处的“巫”理解为“巫术”。“禁巫”即是在禁绝一些不当的巫术行为。若照此理解,言宋代“禁巫”与本书的观点并非截然矛盾。
3.《扶箕迷信的研究》
许地山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8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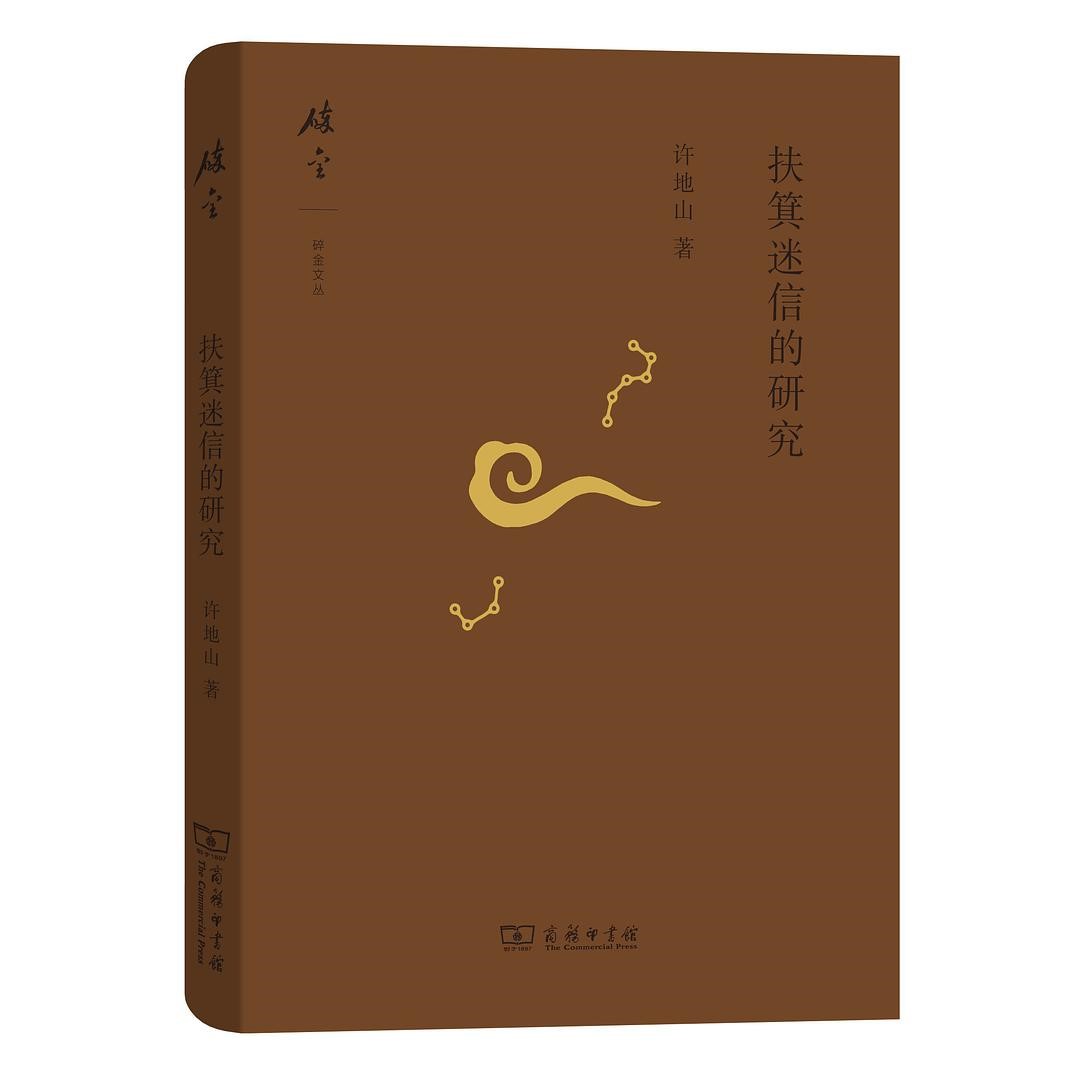
本书初版于1946年,商务印书馆曾多次重印,2020年收入“碎金文丛”再版。许地山先生是民国时期巫术研究领域代表性学者之一,《扶箕迷信的研究》是其代表作之一。扶乩(箕)是一种占卜的形式,属于预测巫术。扶乩源自古代的紫姑信仰,在明清时期颇为流行,因为要借助文字,文人们尤热衷于此。本书从各种文献中收集有关扶乩的资料132则,比较系统地梳理了扶乩的起源、形式、功能和目的等,同时从心理学角度进行了解释,尤其强调“扶箕并不是什么神灵的降示,只是自己心灵的作怪而已。”算是利用现代理论研究古代巫术文化的开创性著作。
4.《闻一多全集》
闻一多著,朱自清、郭沫若、吴晗、叶圣陶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20年1月版

闻一多先生去世后,朱自清、郭沫若、吴晗和叶圣陶主持编订了《闻一多全集》,1948年由开明书店出版。1982年三联书店重版,上海书店新版据三联版重印。闻一多先生治学涉猎很广,在古代文学、民俗学、神话学等领域均有建树,在他诸多研究著述中,涉及巫术的内容不少,对此学界已有专门的研究。如他对于道教的看法,就认为道教“实质是巫术”。更著名的是他运用巫术观念对楚辞的研究,认为《九歌》中的九神“实际是神所‘凭依’的巫们”,也同时指出《九歌》中的“巫音”与“巫术”是不同的:
《吕氏春秋·古乐篇》曰:“楚之衰也,作为巫音”。八章诚然是典型的“巫音”,但“巫音”断乎不是“巫术”,因为在“巫音”中,人们所感兴趣的,毕竟是“音”的部分远胜于“巫”的部分。
闻一多先生的许多研究,都开后来研究之先河,在巫术研究方面的影响也延续至今。
5.《儒门内的庄子》
杨儒宾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8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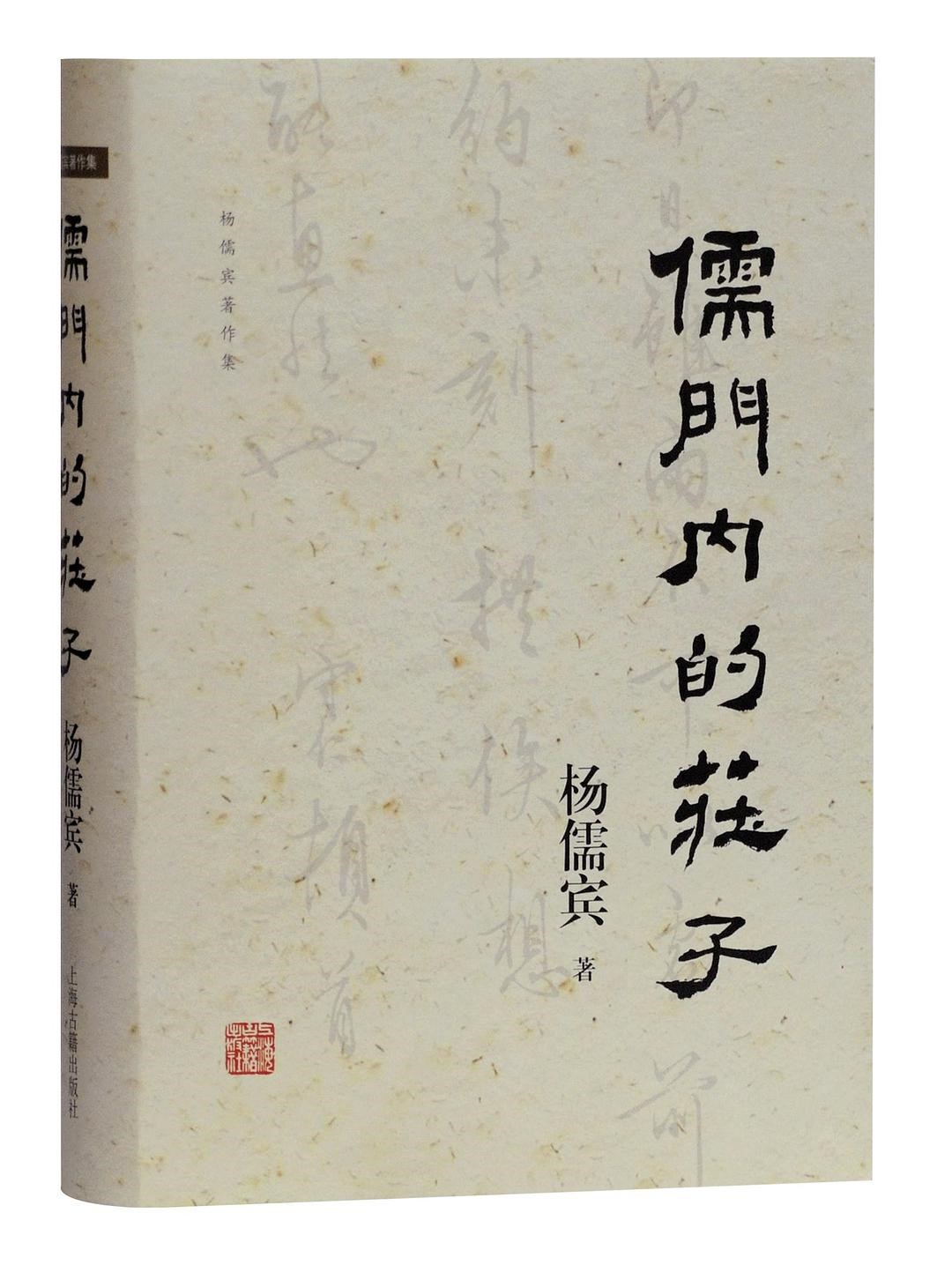
杨儒宾先生的著述陆续在大陆结集出版,在其多种研究中,均体现出对于巫术主题的重视。本书对庄子的研究,就特别重视庄子的巫文化背景。书中第一部分“庄子与东方海滨的巫文化”就是关于这一主题的专论。在上古文献中,巫术是思想和文化的背景和底色,但在轴心转型之后,人文理性成熟,使得巫术逐渐褪色。但是诸家学说中仍旧保存了许多巫术文化的内容,巫术思维虽经过了转化,但仍有遗存。对于这一思想转型,近年学界颇多关注,尤以余英时先生的《论天人之际》为代表。本书关注的是庄子思想中被湮没的巫文化要素。《庄子》文本历经改删和净化,据今人所搜罗的《庄子》古本佚文来看,其中涉及到巫术的内容所在多有。本书从巫术空间(姑射山、昆仑山)、人格型态(天文知识与升天)、神话飞禽(鸟与凤)、生命基质(风气)等方面,分析了庄子与巫文化的关联。作者最后认为庄子与殷商文化有关联,“庄子浸润甚深的巫文化乃是燕齐海滨的类型,这是种典型的萨满教型态的文化。”(本书第120页)这一思想史线索的梳理,对于学界探讨庄子及道家文化,以及中国哲学的轴心转型过程,都有着诸多可资参考的内容。
6.《中国医药与治疗史》
[美]艾媞捷、[美]琳达·巴恩斯编,朱慧颖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版

上古时期,巫医不分,两种历史差不多就是同一个历史。本书所研究的中国医药与治疗史,其中关于巫术的内容,自然也非常多,其中极为精彩的便是巫医关系的历史变化。书中非常扼要地概括说:“商、周、秦时期,人们普遍认为疾病是由超自然,尤其是诅咒造成的。自然世界里日常的相互作用、远祖或近祖的不满,都有可能使人得病,因此古代的治疗者对于地方传说,病人的家世和医学技术不得不了如指掌。治疗者主要的治疗工具是占卜,主要的治疗方法是驱邪逐祟。随着周代宗法制度及相应的变化莫测的祖先神灵的等级制度渐趋衰落,尤其是在春秋时期(前770—前476),对病因的解释逐渐从超自然的力量转向自然的因素。”(本书第9页)汉代巫者在治疗中的权威地位逐渐下降,“到了汉末,学者所著的医书已开始嘲笑巫者不了解新的医学知识,对其病人一无所知,并嘲笑巫者想必也没有合适的医书。”(第58-59页)后来随着宗教团体(佛教、道教)医学功能的提升,巫者在治疗中的地位更加边缘化。正如本书作者之一的林富士先生曾指出的那样,汉代是巫者地位变化的关键时期,巫者的医学权威地位也是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转变。但亦需强调的是,在现代医学兴起之前,巫者也从未在医学治疗中缺席,直到非常晚近的时期,民间的治疗中亦还有巫术的影子。
7.《死与重生:汉代的墓葬及其信仰》
李虹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版

墓葬是宗教和民心信仰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本书是对汉代墓葬及信仰的系统研究,其中涉及到巫术的内容实属不少。书中提到:“春秋以降,巫对祭祀的垄断权的消失使他们远离神权中心和政治中心,转而向下层发展,成为专事鬼神的神职人员。同时由于古代巫医不分,巫也是医,他们在无法医治好病者后,只好再承担包办死者入葬的任务。”(本书第14页)巫觋参与葬礼,尤其是处理解除术。“解除术又名解适或解谪,是秦汉魏晋时的一种避祸除殃方术,也是汉代墓葬信仰的核心内容。”(第74页)解除术主要有墓门区域的解除术和墓室内部解除术,后者又有以下几种类型:假人代形,药石厌镇,符箓劾鬼,使用解注瓶等,其中的许多形式都是典型巫术中常用的手段。
8.《唐宋民间信仰》
贾二强著,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年2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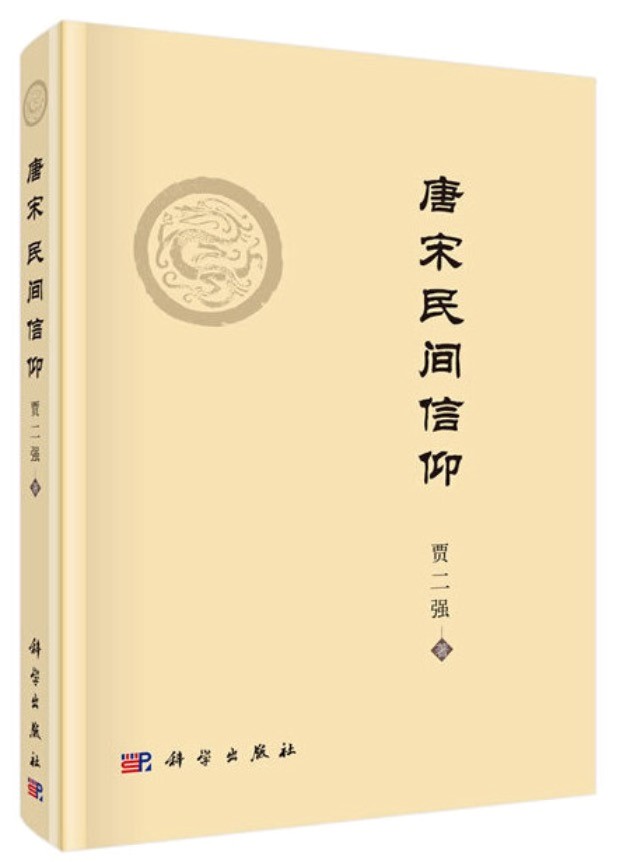
本书专论唐宋民间信仰,直接论及巫术的内容不算很多,但其中所探讨的问题却大多与巫术有关。作者指出,“所谓民间信仰,是相对于正式的宗教或得到官方认定的某些信仰,是一定时期广泛流传于民间或者说为多数社会下层民众崇信的某些观念。”(第1页)民间信仰有几种特征:信仰的多样性、神秘性语言多变性。这些都与巫术相似。如在民间信仰中的自然神和人格神,经常会在巫术中出现,如扶乩就起源于紫姑神信仰。又如道教中的许多方术,都源自于巫术。
9.《笔记语境下的宋代信仰风俗》
范荧著,郑州:大象出版社,2020年10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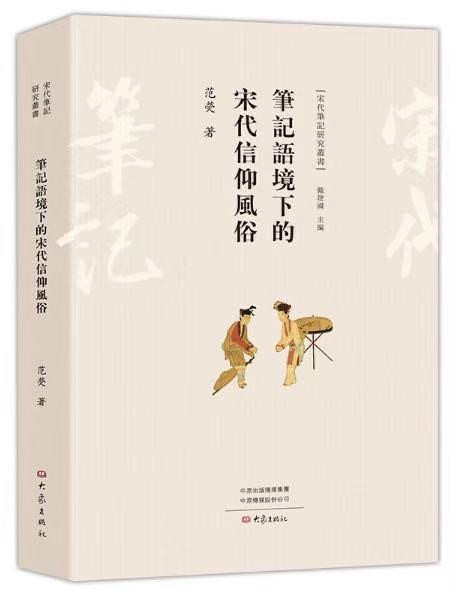
本书是“宋代笔记研究丛书”之一,以《全宋笔记》为基础,对宋代宗教观念和信仰习俗进行了比较系统地梳理。笔记资料对研究宗教及巫术有着其独特的价值,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因语涉鬼神而难登‘大雅之堂’的民间信仰习俗,在正统史书中实难见其错综复杂、丰富多彩的本来面目。”而笔记资料恰好可以补正史之不足。作者亦专门提到两宋时期信仰习俗变化的新特点:城市发展与经济多元化,信仰习俗之趋势与世人现实诉求关系密切;原始崇拜所具有的神秘虚妄色彩淡化,增添了许多世俗情趣和生活气息等。这些特点在宋代巫术中均有所体现。
本书从自然与自然物崇拜、鬼魂信仰与祖灵崇拜、佛教信仰习俗、道教信仰习俗、俗神信仰与淫祀、巫术与禁忌等六个方面展开,巫术虽只是宋代信仰习俗之一种,但实则其他一些方面亦与巫术有关密切的关系。在对巫术的具体分析中,本书聚焦于两种类型的巫术:预测巫术与祈禳巫术。虽有代表性,但略显简单。
10.《权力的黑光:中国传统政治迷信批判》
王子今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11月版

本书初版于1994年,此为修订本。巫术虽非本书中心论题,但谈及“政治迷信”,巫术必定是核心话题之一。在早期文明中,巫师均是知识和权力精英,“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国语·楚语下》),这样的人物,自然也有领袖的才能。所以巫师与首领往往兼具一身。著名的例子如大禹,他是君王,又是大巫,因为他巫术能力的强大,其步态被称为“禹步”,成为后世巫师效仿之对象。后来巫师和君王两种身份逐渐分离,但巫术与政治的关系一直很密切。本书提到的例证如西汉著名的巫蛊之祸,东汉末董卓军中的巫术活动,唐代王玙以巫事致位将相等。政治人物常借助巫术以建立政治迷信,以确立政治权威,但正如书中引述弗雷泽的话:“没有一种仅仅是建立在迷信,也就是建立在虚伪之上的制度是能持久的。一种制度,假如不是适应了人类某些实质性的需要,假如它的基础不是牢牢地建筑在事物的自然属性之上,那么它就一定会灭亡,灭亡得越早越好。”这种政治迷信最后必定以败局收场。
11.《中国色彩史十讲》
肖世孟著,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11月版

近年有关色彩史研究的著述已有多种,对上古时期颜色的研究,往往就涉及巫术的内容。巫术中的色彩,具有法器之功能,依照的是相似律原理,如汪涛在《颜色与祭祀:中国古代文化中颜色涵义探幽》(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中所言:“针对不同的祭祀对象和祭祀目的,要选用不同颜色的牺牲。白色、赤红色和杂色动物,经常用于祭祀祖先,黑色的羊经常用于求雨,黄色动物专门用于祭祀四方或土地神,也可以说商代已经有了一个成形的颜色体系。”比如本书专门分析了朱砂在巫术中的应用情况。朱砂因颜色与血液接近,常“被当做血液的代用品,具有血液的神力,在墓葬中呼唤生命,在盟誓中对神灵作出保证、在祭祀中向鬼神鲜血。”(本书第25页)朱砂在早期巫术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书还提到了殷商之之前在巫术中所常用的其他色彩颜料,如赤铁矿粉(赭石)、石绿、石膏、炭黑(百草霜)等,都值得做专门的研究。
12.《广东民间信仰文化探析》
贺璋瑢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9月版

广东古为越地,该地域自古即流行巫鬼信仰,至今仍有遗存。本书专门分析了广东地区巫鬼信仰较之其他地方盛行的原因,一是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广东地处热带,尤其春夏之交炎热潮湿,流行“瘴疠之气”,容易引发疾病,得病之后,多求助于巫术来治疗;二是岭南民间信仰多保留了百越民族原始宗教之遗风,以巫觋文化为之底色。“越是受中原文化影响小的地方,巫觋传统的特色越是浓郁。”(第161页)书中还专门分析了客家人的民间信仰,巫觋信仰是其中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客家文化中主要的巫术有:请神、招魂、问仙、扶乩、喊惊、认契娘、卜卦、测字、看相、算命、求签、画符等。客家的巫术文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客家人的巫术文化与北方的萨满巫术非常相似。巫术之所以能顽强地生存于客家聚居地,可能因为古时山高水险的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求生存、求发展的强烈愿望和当地原住民本崇尚巫鬼的习俗间的相互影响及交融所致。(第86页)
13.《元代风俗史话》
陈高华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10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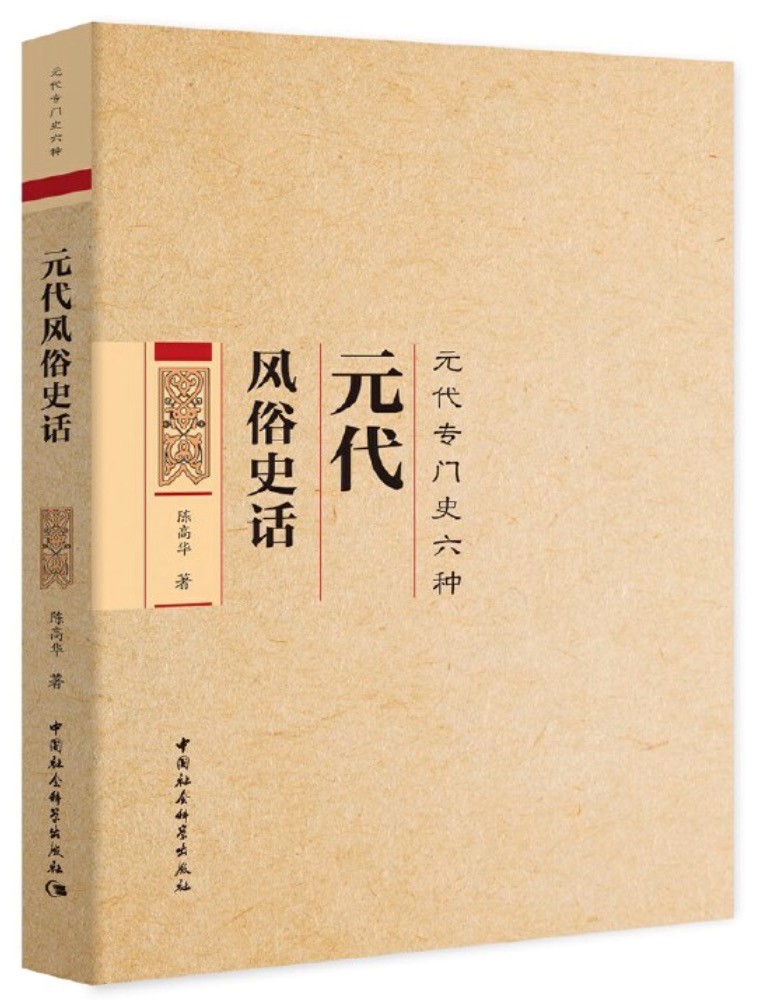
在有关巫术的断代研究中,元代相对是比较薄弱的。本书作者元史专家陈高华先生说,有关元代巫术,“还没有人对此作过研究”。“元代的巫觋与巫术”,是本书之一章,篇幅不大,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中按照以巫为医、以巫为害两个部分,列举了元代的一些巫术事例。结构比较简单,梳理也过于简略。尤其重要的是,关于元代巫术,必定要涉及到蒙古萨满与汉地巫术文化的关系问题,书中也没有提到,让人意犹未尽。
14.《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动物形象变迁研究》
张瑞芳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10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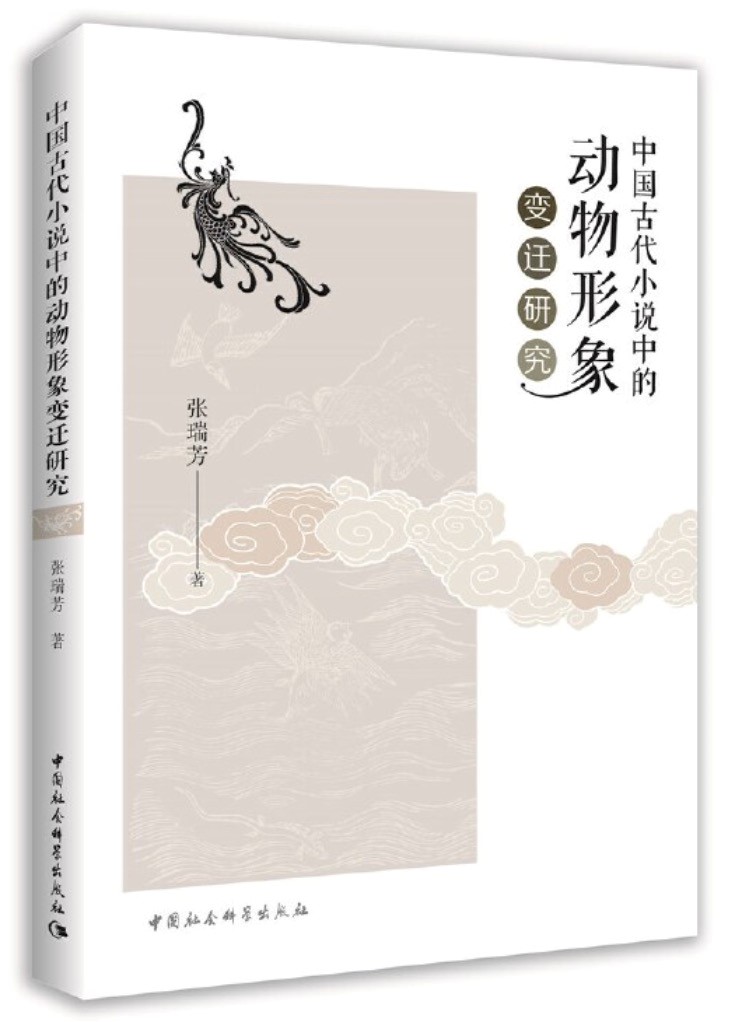
巫术与动物的关系,是巫术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卡西尔尝言:“原始思维中人与动物的基本关系,既不是彻底实用性的,也不是经验-因果性的;而是一种纯粹的巫术关系。”本书聚焦于古代小说中的动物形象,其中涉及到巫术与动物关系的内容,尤其是在先秦时期作品和六朝志怪小说中。在巫术中,“利用动物来实施巫术或将动物作为灵物以辅助巫术,成为动物在巫术文化中具有的特殊意义。”(第77页)《山海经》中有十几则关于巫师珥蛇、双手操蛇、足下践蛇的记载,蛇即是一种典型的巫术灵物。又如作者在书中所谈到的,古代巫师均有“头上长角”的装扮,高国藩先生将之看作是古代巫师最主要的特征。或因本书所处理的时段跨度太大(从先秦一直到明清),有些问题并未完全展开。
15.《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第2版)
杨念群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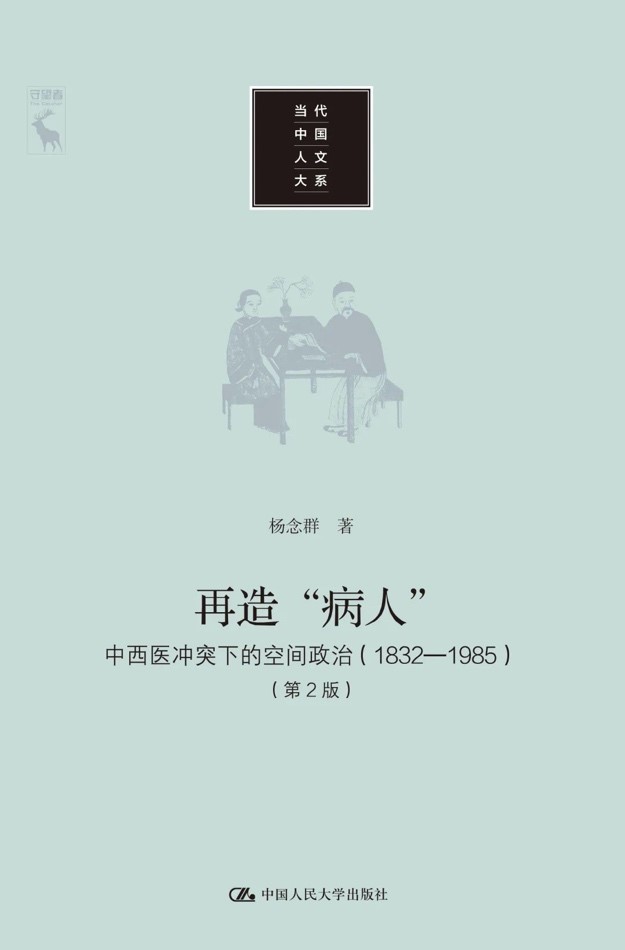
本书初版于2006年,此为最新的再版。全书探讨的核心话题之一,是西方医学进入中国后,中西医之间产生的观念与实践冲突。这自然就涉及到巫术,尤其是巫医问题。在传统社会中,巫医不分,有时民众反而是“信巫不信医”,甚至到了晚清民国时期,巫术仍在治疗活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民间社会中,医生与巫者虽在医治理念和技术上有所不同,但都是针对身体出现异常状况所可能采取的治疗选择之一。”(第208页)普通民众会把治疗效力作为选择的依据,而影响治疗效力的诸多因素中,文化与信仰的因素是很重要的。而且,“治疗疾病不是一种单独的行动,而是属于整体社区事务的一个组成部分。”(第244页)所以治疗亦依赖于书中所提到的“地方感觉”。但随着西方现代医学知识的传入,卫生现代性观念及城市治理理念的传播,“追剿巫医”逐渐成为普遍现象,“地方感觉”也逐渐消失,人们对于疾病、身体、治疗等观念也发生了改变。
16.《精神的复调: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
张邦彦著,新北:联经出版公司,2020年4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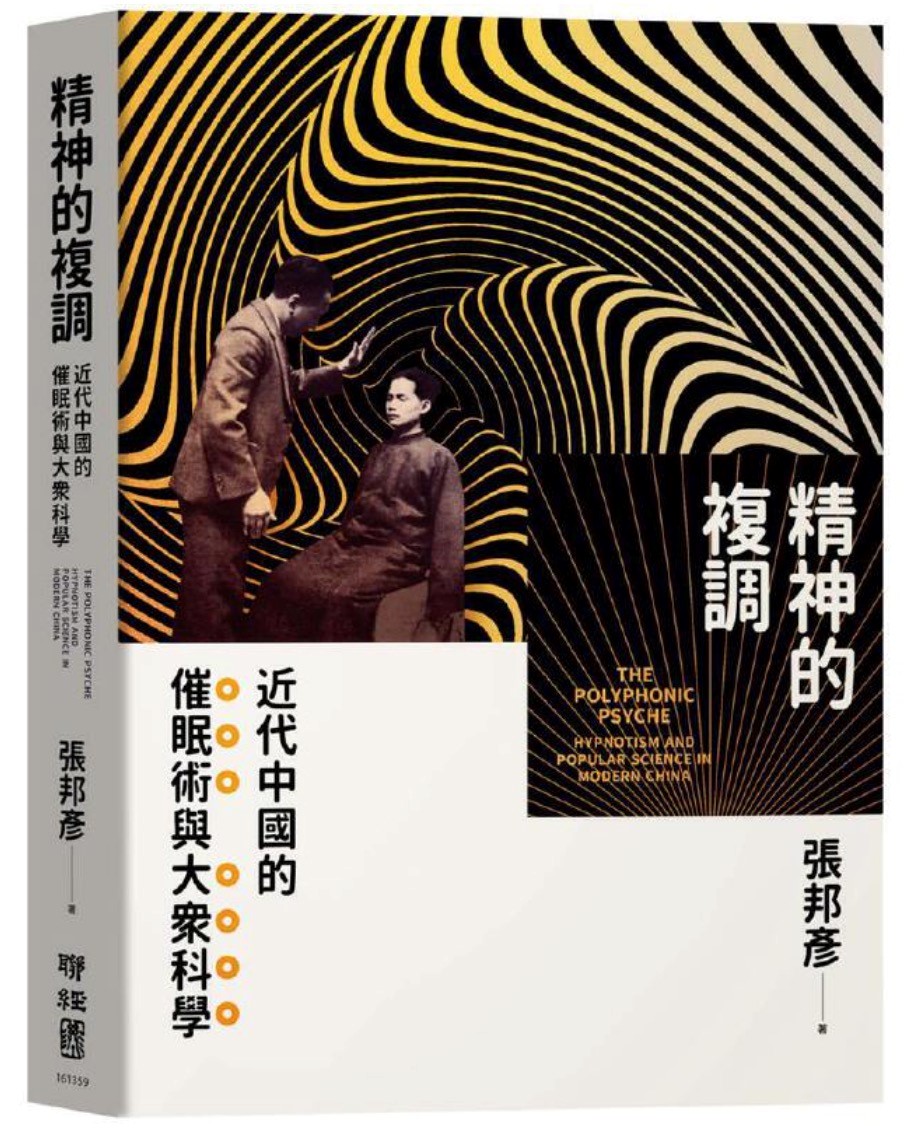
本书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巫术研究著作,但涉及的一些问题却与巫术有着极强的关联性,尤其是对于思考巫术的古今转变问题。近代中国曾有一段催眠热潮,广受社会大众所关注,催眠术的神秘感让人顿觉“脑脏中有一种不可思议之变化”。当时学界组织了“中国心灵研究会”之类的诸多组织,来研究催眠术。同时代中国也有灵学会等研究组织,这与西方的通灵论(spiritism)、灵学研究(psychical research)、超心理学(parapsycholgy)等研究相类似,都希望借助“科学”来研究灵魂、心灵沟通、特异功能、死后世界等诸种“不可思议”之问题。作者在书中强调了当时社会中对“科学”内涵的多重理解,形成了“科学的复调”。当时也有许多传统的巫术形式,在利用“科学”来完善巫术实践(如扶乩)和原理阐述(如灵魂显形)。此书所探讨的内容,在科学话语盛行的语境中,尤其能引人去思考有关科学、宗教、心理、迷信等议题。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