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一个人类学家的艺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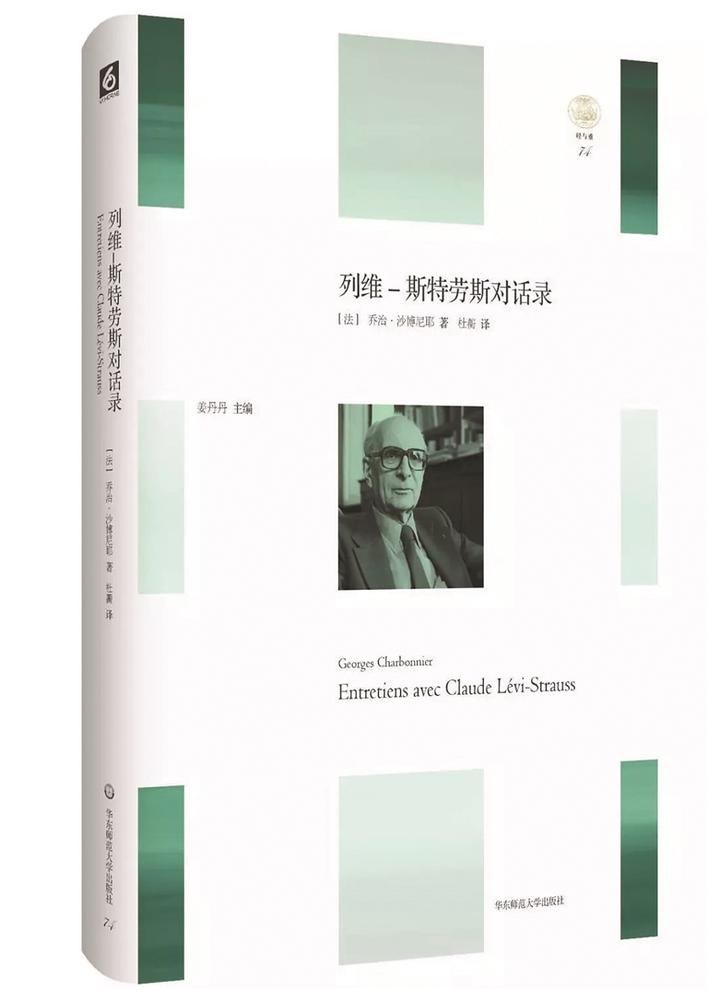
一位著名人类学家围绕艺术主题进行谈话,看似跨界,但见解实在深刻,让人钦慕。《列维-斯特劳斯对话录》源于他1959年在法国电视三台录制的系列访谈。它为我们重现了一个博学、机警、从容的思想家是如何精彩论辩的。书中他关注艺术与语言间的难解关系,难以调和的矛盾。那就是语言系统的稳定性和共性,与艺术作品的多变性和个性追求,形成了巨大反差。
从客观上看,原始社会的艺术家们没有了解不同世代,不同地域作品的条件。但从另一面看,他们也没有意愿去模仿、接纳其他艺术形式。相反,他们采取了一种拒斥态度。这种原因可以归结为,原始艺术把作品视为语言功能的延伸,保卫语言的纯一性,也是维系社会内部功能的需要。有趣的是,当代艺术家们虽然“手法多得泛滥”,但也并非是去吸收外部语言,只不过是“用语言符号玩着无谓的游戏。”“艺术创造的条件仍然是个性化的,而立体派无法通过自身找寻艺术作品的集体功能。”
原始社会隐含的“群体的内部生活”造就了某种“群体性艺术”。这使艺术作品的符号功能更突出,它更多是用来沟通,交换价值,更加偏向于社会学意义(如作为艺术家的巫师,通过作品沟通部落众人和神)。“在我们所称的原始社会中没有或者只是特例的东西。”但这是否说明原始艺术就等同语言系统呢?斯特劳斯指出“艺术家永远不可能完全掌握素材和他所使用的技巧。”如果能完全掌握,那就意味艺术家能够对自然进行“绝对的模仿”。这样,艺术品和实物就没有差别,只有同一,艺术就不会存在。这个前提决定艺术将永远处于语言和客体之间的地带。
我们必须考虑,艺术在何种程度上是闭合的,它的“开放”又是在何种层面。这一问题涉及到艺术的“表意”功能。从本质上看,艺术其实模仿了语言系统,但又在语言之外,再造了另一套表意系统。艺术品和语言的区别在于它们和实物之间的关系。语言本身是一个和它所要表达的意思没有物质关联的符号体系。而艺术品却总是从“感知上”复制实物,再造与物品结构相似的对应关系。比如安格尔“就是懂得如何在给人逼真印象的同时,让这个逼真的作品散发出一种穿透感知的表意,直达所感知物品的结构”。
正是在表意的观念和程度上,我们看到艺术的两极:要么更接近于符号系统(抽象),要么更逼近于实物(写实)。斯特劳斯警惕艺术沦为随机的符号体系,他强调了美学和情感的形式。抽象绘画是否设计了一种“伪代码”,它企图强加给我们的语言,“是否还是一个黏着于美学情感的语言,难道它不是一个和其他任意体系相同的体系吗,比如铁路信号系统,各色的方块或圆弧”。这种质疑是对当代艺术的有力反思,它的危险有两种层面:一是形成了“伪语言”,它是“关于语言题材的幼稚游戏”,无法表意。另一种则彻底成了语言,除了使用的材料不同,毫无美学意义。
斯特劳斯回溯艺术史的过程,也是对艺术家认知能力、素材主题、观念模式和艺术结构的检视。他一面以“外行身份”来阐释,另一面也用“局外人”的态度深入到艺术的人类学视野。比如文艺复兴时代的画家把绘画视作“认知方式”,是占有、复现世界的手段。印象派绘画不只改变了绘画技巧和观察方式,同时也更新了客体:古典和浪漫主义里宏伟高贵风景,被不起眼的卑微郊野取代。印象派教育并培养了新观众,跳出学院的视觉传统,返回单纯的物体,但却只是“表面上的肤浅革新”。因为重组物体是不可能的,同时,它也并未“赋予含义。”
立体派又试图在工业文化里找到灵感和主题。它比印象派走得更远,“超越了物体,乃至表意。”然而,斯特劳斯对绘画的展望,看上去又那么传统,更像一种折返,一种美学理想的寄托。“未来的绘画不是试图从这个我们人类唯一感兴趣的客观世界中隐遁和逃逸,也不是满足于我们现代人生活的庸常世界,这个世界无论对于我们的感官或精神都不尽人意,而是完美运用最传统的绘画技巧,在我身边构筑一个更宜居的宇宙。”
(文章首发于《中华读书报》)
作者:俞耕耘,文艺评论人,专栏作者,现居西安。微信公众号:书语云中君。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