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北大西班牙语专业创建60周年|从读书迷成长起来的西语大师
【编者按】
北京大学西班牙语专业创建于1960年,1978年起设立硕士点,1999年设立博士点,是目前国内仅有的“西班牙语语言文学”博士点。老一辈教师蒙复地、刘君强、周素莲、沈石岩、徐曾惠、赵振江、赵德明、段若川、段玉然,学术中坚陈文、丁文林、王平媛、韩水军、王军等,培养出大批西班牙语人才,在教育、文化、外交、翻译、军事、贸易、新闻等诸多领域发挥专业优势,各有建树。
北京大学西班牙语专业的创建、完善和发展是中国西班牙语语言文学教育、研究和翻译发展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记录着中国与西班牙语国家越来越紧密的交流和交往。
今年是北京大学西班牙语专业成立60周年,北大西葡语系(2007年成立)特邀系友撰写回忆文章,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万戴和楼宇曾对著名翻译家,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拉丁美洲研究中心顾问赵明德先生进行访谈,以下为口述内容整理成文。
赵德明于1939年在北京市出生,祖籍河北昌黎,高中毕业保送至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1960年调入西班牙语专业,196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被送到智利公费留学,1966年回国,之后一直任教于北京大学西语系。赵德明教授致力于西班牙语教学和西葡拉美文学翻译与研究,译著数量十分惊人,是巴尔加斯·略萨、罗贝托·波拉尼奥等多位重要西葡拉美作家在中国的主要译介者,并著有《拉丁美洲文学史》(合著,1989)、《20世纪拉丁美洲小说》(2003)、《巴尔加斯·略萨传》(2005)等专著。
我跟西语结缘,和西语语言文学结缘,有着“误打误撞”的因素在里面。就是说,我是随着时代走、随着国家的需要走、随着党组织的安排走。我上中学是在北京市二十六中,现在叫汇文中学,是一所重点中学,高中毕业时我被学校保考(就是学校带有保送性质地送学生进入大学,但是需要有一个单独加考)到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法语专业学习。
当时的我并不清楚法语是一门怎样的语言,因为我中学6年学的是俄语,读过大量苏俄小说。二十六中的图书馆特别丰富。在借书高峰时,我帮忙站柜台,帮管理员干活,于是得到了一个优惠:别人每次借一本,我可以借两本;别人阅读时间是10天,我可以是三周。当时我读书真是痴迷了。痴迷到什么程度?我从学校,也就是现在北京火车站附近的地方回家,一路上我仗着路熟,就捧着书一边看一边往前走,穿胡同、过小巷,一直走到东便门外的家。那时候,我正是十几岁这个年纪,就像海绵吸水似的,幸福感特别强。后来我读到一篇巴尔加斯·略萨的散文,说马德里的一个老公务员养成了一个习惯:早晨离开家去上班,这一路上也是捧着书。他喜欢读各国文学,一路上,他的心远离了马德里那喧嚣的车水马龙,飞向了俄罗斯大草原。这让我很有共鸣。

赵德明
进北大读法语时,我从高中开始对文学的喜好还是延续下来了。北大法语课最早就是教语音语调,内容不多,但有很多练习。我觉得那点发音道理也就那么回事。所以课后,别的同学都很认真地做练习,拼命地练法语,而我就钻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文艺部里埋头阅读。
1959年1月,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胜利了。1960年,古巴和中国建交。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当时急需一批西语人才。这个时期西语人才的培养主要是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当时北大按照国家的要求,准备开设西语专业。生源一方面从社会上招,另一方面也从法语专业里调了三个人:赵振江、段若川,还有我。调我们三个人是有目的的,不是为了将来走向社会,而是为北大建立西语专业教研室服务。说老实话,当时我实际上是不情愿的。其实我学法语也不是很情愿。然而,当自己的兴趣与国家需要出现分歧时,我是一直服从国家需要的,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信念。
1963年大四夏秋一开学,学校党组织就找我谈话,说准备送我出国,派我先行集训。集训地点在北外的出国部,我就到那里报到。北大第一批就派出了我一个人,第二批又派了徐世澄等几位。这第一批里的12个人,组成了一个出国临时支部。我是支部委员,领着大家伙儿置装、学习、培训,忙了两三个月。培训快结束时,接到通知说这批12个人里,走11个,留下赵德明另有任务。等他们都走了,组织再次找我谈话,说准备派我去智利。之后,又从外交部来了一个干部叫丁永龙,我们两个人一起接受培训。培训结束后,我们就开始办去智利的手续。办完手续后,我就和丁永龙出发了:先坐火车到莫斯科,之后是捷克,再到瑞士,然后从瑞士飞巴西,从巴西到阿根廷,从阿根廷飞越安第斯山,最后才到智利首都圣地亚哥。
我们的飞机降落以后,很快就有人来接。我们住到了新华社驻圣地亚哥的办事处,第二天就开始联络。将我们推荐到智利大学的那位重要人士,是当时的智利副总统。他曾访问过中国,并和中国达成了协议:中国可以派两个人到智利留学,并由智方提供奖学金。我们留学的单位是智利大学教育学院,我选的课程是语言、文学、历史、地理。
当时党组织要求我们要学好专业知识,而且一定要学到最好。就这样,我们入学了。说老实话,开始时,我听课非常费劲,因为北大学的那点东西在国外远远不够用。这个课不是专门给我们开的,是正规的高校课程;智利大学教育学院是培养教师的,要求还很高。同班学生主要是智利人,也有部分其他拉美国家的学生。给我印象最深、让我受益最大的一门课叫“恢复性语法”,授课教授叫安布罗西奥·拉瓦纳莱斯。多年后,我买了一本《美洲西语大辞典》,编委会里还有他的名字,这让我十分激动。

1964、1965级北大西班牙语专业学生返校留影
我们听课比较吃力,理解也十分困难,心里都很着急。于是我们就想办法录音,然后把录音听写出来,让助教给我们辅导。最后,我们打印出来西语版本,再请助教给改一遍。这位助教态度认真,对我们也特别重视,又让教授看一遍,教授在字里行间作了修改。如此一来,就变成一本像模像样的语法教材了。而到考试之前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是拼命背书,因为是字面阅读,就好懂一点了。考试时大家按照名字顺序排好队,抽签考试。我抽到的题目正是我认真背诵过的内容,我答完了以后,考试委员会的四个老师都点头笑了。于是,他们打分,当时是10分制,他们给了我9分,是班里的最高分。出去后,班长问我:“赵,你得了多少分?”听完我的回答和我对问题的解答之后,所有同学都为我欢呼了起来。
这件事很轰动,对我们后来站住脚、避免警察的监视起了很大作用。不过也有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就是当时智利方面提供奖学金,也给点生活费,我省下钱买了很多书,总共有好几百本。但快回国时接到通知,说没这笔钱海运,最后我只能拿皮箱装了十几本最重要的书,剩下的只好送人,留在那儿了。都是好书,太可惜了!
1966年3月,我回国后正式在北大留校任教。但是很快,一两个月之后北大就开始乱了,后来课也停了。我想搞点文学研究、文学翻译的计划全都泡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的同行听说我回来之后,希望我能翻译一些拉美文学作品,我就翻译了一批短篇小说;他们也希望我搞一点拉美文学动态,约了好些篇。当时真是有一番新的计划,可什么都做不成了。等到70年代“文革”转向,要求老师们都得去五七干校劳动。我还年轻,干点活也不算什么,就依照学校安排去了江西劳动。我去了半年,这段日子里,除了下地种点水稻没别的事情。我悄悄地带上了《马丁·里瓦斯》原书,用《毛主席语录》盖着,下面垫一本练习用的笔记本,开始着手翻译。最后那个本子让我翻得老厚了。回到北京之后,北大慢慢开始复课、招生,那时候就有点事干了,时间也多了,就开始继续翻译。差不多到1978年吧,这本小说就翻译完了。翻完之后,书稿就放在了那里,直到1981年6月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大约在1977年,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西班牙语专业有一位秘鲁专家,名叫米格尔·安赫尔·乌加德,他是巴尔加斯·略萨的远亲,也是文学语言专业的教授。当时刚好“文革”十年结束,我作为青年教师,对于拉美文学的情况已不甚清楚,正好向他请教最近几年拉美文学的新动向。他第一个就谈到了巴尔加斯·略萨。我读完了《城市与狗》后,产生了要把这位作家介绍到中国的想法。

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活动现场
1979年10月,在南京大学召开了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大会重点讨论的作家有两位,一位是巴尔加斯·略萨,还有一位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两位作家对于1979年中国西语文学翻译界都是很新鲜的。适值改革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完不久,也提到需要了解国外的情况。具体到文学研究、翻译、出版领域,则是如饥似渴地想了解世界文坛近况。最终,我们决定通过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杂志《外国文艺》,把马尔克斯和略萨介绍到中国来。于是,当时的中国文坛对拉美文学有了一定的认识。中国作家发现,拉美文学区别于欧美文学,更区别于东方文学,有着自己的独特性。拉美文学真的是一朵奇葩。《我们看拉美文学》(论文集,赵德明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可以为证。
1996年,我在西班牙做学术交流,刚好赶上西班牙穆尔西亚大学举办巴尔加斯·略萨作品国际研讨会。我在大会上作了一个报告,主题是关于巴尔加斯·略萨在中国。大会参与者众多,坐满了大礼堂,略萨本人就坐在台下。按照西班牙学术会议的惯例,我单独在台上进行演讲,用西语梳理了巴尔加斯·略萨在中国国内的翻译、介绍、影响,以及国内学界的看法。我当时对略萨1990年参加总统选举的经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他不适合搞政治,他的失败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就有一个杰出的作家可以继续写作,而他即使当上了秘鲁总统,也未必能够做成惊天动地的大事。这时会场又是掌声又是笑声。他坐在台下面对着我,也笑了。
因为住在同一个大饭店里,我俩相约一起共进早餐并且进行了一些叙谈。其中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文学的译介。当时中国已经加入了伯尔尼版权公约,我们的译介工作也逐渐规范化。他慷慨地表示要送我一个礼物,就是请他的版权代理将《水中鱼》的版权免费赠送给我。
除了略萨之外,我重点翻译的作品还有罗贝托·波拉尼奥的《2666》。原著是出版社提供的,希望我来操刀翻译。这部书很厚,有800多页,应该是我一生中翻译篇幅最长的一部书。尽管体量大、阅读时间长,这部作品依然好看,故事性强、情节抓人。且作品背后对欧洲文化、拉美文化均有所涉及,对社会的黑暗面具有很强烈的批判性:黑社会横行、普通百姓遭欺压、战争的杀戮和平日的杀戮,如连环强奸杀人案,作家对此都有着细致的描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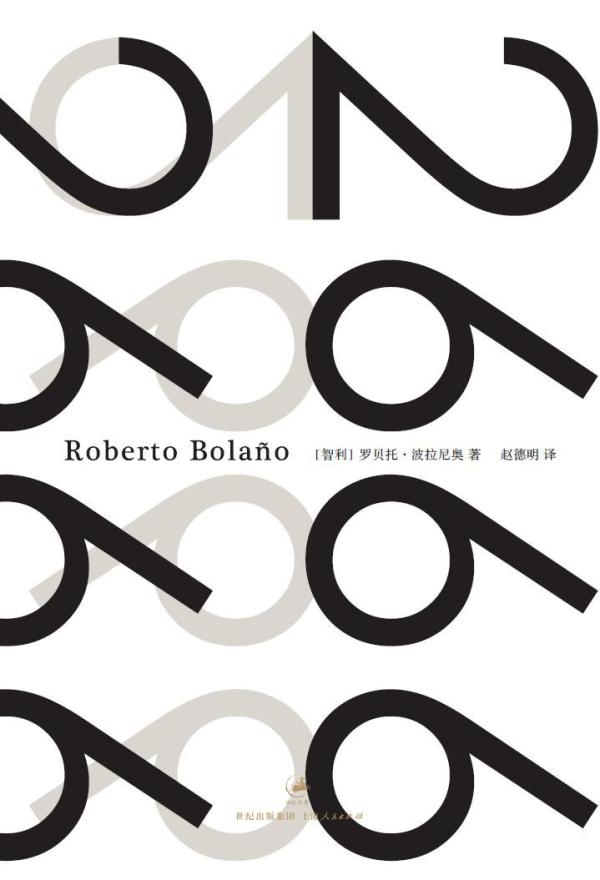
《2666》
我的任务是教学,翻译则更多的是兴趣。这40年的翻译生涯,我翻译的文学作品有八九十部,再加上其他类型的书籍超过百部。如果总结我的体会,大概有以下几点。
第一就是眼界要开阔。要明白这个地球上还有另外的世界,有另外若干个不同于我们的世界。这个观念不是一句空话,是实实在在的。说这话的时候就想起当年见到的老师、同学和朋友。不管你是智利的、阿根廷的、古巴的、西班牙的、巴西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人。他们的说话、办事、风俗、习惯,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另外好几种生活方式。他们的所思所想反映在文学方面,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迪,我们要老老实实先弄懂这些,而不是不懂就批评。还有交流,交流是带着问题的,你对人家能提出什么问题,人家对你提出什么问题,你怎么解答这些问题,你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是真话假话,是敷衍的话、官话,还是骨子里的话?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反复思考的问题。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互惠的、平等的,但也是各取所需的。
第二是通过翻译方法而来的,就是需要注意细节。文学翻译中的符号、短句、主句、从句等,都告诉我这样一个思考方法:要注意语言背后的东西,专注文字表面和其背后东西的关系。进入文学译介的专业领域,就需要察觉文学表达中的暧昧:有些可说可写,有些可说不可写,只能通过特殊的描述方式体现一下,这样译出来的文字就会比较复杂、文雅。文学告诉我们很多复杂性,要避免片面、避免偏激、避免简单化。复杂的东西味道浓郁,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第三就是一定要读书。读文学的书,读翻译文学的书,包括写文学的书,要把历史、哲学和文学这三者贯穿起来。比如像《红楼梦》中“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这是一种悲观的观念。这种观念统领了全书,就是说贵族世家辉煌繁荣的背后,埋伏了危机,而这个危机和刚才说的白茫茫一片是有关系的。如果能够考虑这种悲观哲学观念的话,对深入理解《红楼梦》就有好处。而历史和文学关系就更密切了,有的历史事实经过了演化之后,就可以变成很好的文学作品。就像《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关系,《三国志》是写历史事实的、记录性的,但是《三国演义》就是大家的拓展了,是虚拟的、带有主观构思的,这就是文学了。这种作品,就是结合文学中的拓展和夸张,对于历史事实进行重新建构,形成全新的文学作品。所以历史和文学创作是有密切关系的。
第四就是要认识到虚构作品与作家想象的密切关系。这也是我翻译了这么多书之后的重要感悟。文学中当然有写实,但是如果没有丰富的想象力,就会显得苍白。毛主席曾言道:“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要是没有想象力,这些意象就不能够串起来,也就失掉了诗词的意境。理解到作家、诗人们丰富的想象力,并且将这种汪洋恣肆的想象用母语表达出来,是对一位文学翻译者一生的挑战。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