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43
2020︱动荡一年中的三个历史片段
人类史远比自然史短暂,但若也具有古生物学的“间断平衡”特征,那么2020年即是长期渐变后的一段短期剧变。疾疫蔓延全球以来,国际学术活动的形态,尤其是学术介入公共界域的方法和视界随之改变。如疾病史家虽然不奋战在公共卫生前线上,但力图从古今鼠疫、霍乱和流行病治理中汲取经验;隔离中的政治理论家在霍布斯《利维坦》卷首图中的空城空巷中找到了瘟疫医生的形象,促发了一场疫情政治理论的探讨;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家则辩论封锁隔离和经济效益的权衡取舍、医疗物资分配的伦理问题。但在本文中,我甄选了今年看似无关疫情,却在其语境中应运而生的三件案例:美国社会冲突中的修史浪潮、梵蒂冈政策影响下社会保守派的中国视野、印度政治经济危机中的历史回忆,借此管窥2020这动荡一年中,学术界、思想界和舆论场促人省思的张力。
美国史的政治意识危机
2019-2020年的新冠疫情无疑加剧了美国既有的社会经济张力。美国人民面临的不仅是结构性的制度难题,更是蓄势已久、有触及发的政治意识危机。譬如,内战后南联邦子女后代为“先烈”们办的纪念馆一直遭受口诛笔伐,甚至游行示威。但在今年乔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事件之后,示威者一把火点燃了里士满“联邦之女”总部,消防员调动了九辆灭火卡车才平息“怒火”。再如,美国中学的美国史课本虽不尽相同,但都存在大量叙述性纰漏,极有必要修缮原住民史、贩奴史、南方重建和民权运动等篇幅。但今年,《纽约时报》迫不及待地自赋使命,推出了“1619年项目”(the 1619 Project),意图将美国诞生的“时间意识”推移至非洲奴隶首次抵达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时间,并以非裔视角重新书写美国史。一时间华府沸腾,右翼学、政二界震动,参议会推出了“保卫美国史法案”,白宫也针对“1619年项目”成立了“1776委员会”,推行“爱国主义教育”。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访谈时慷慨陈词,批判美国史的修正主义:“我看,我读,我看这玩意……它来自哪里?代表什么?我都不知道”,可谓大辩若讷。

“1619年项目”文本和印刷物
尽管“1619年项目”的倡议者琼斯(Nikole Hannah-Jones)获得了普利策奖,但因其史料史论俱待推敲,引来了学者们两点同情的批评。一是具有法理意义的“美国建国”是否真要从1776年前移至1619年?炮火之下,“1619年项目”悄然删去了这一立论,又再度引发争议。二是美国独立前夕,尽管英帝国舆论界普遍批评蓄奴、一些殖民地领袖也无意废奴,但这是否足以说明维持奴隶制是美国殖民者谋求独立的主因?在这一点上,左右翼学者均持异议。传言《纽约时报》主编一度拒听谏言,直到视种族正义为己任、以介入政治为己好的非裔学者艾伦(Danielle Allen)警告他,再不将炮火对准的“殖民者”限定为“部分殖民者”,她便要公开批评“1619年项目”时,《纽约时报》方面这才妥协。
其实,“1619年项目”最令人疑惑的,正是1619这一年份。在以英属移民为主的十三个殖民州引进黑奴之前,奴隶制已存在于北美大陆。黑奴抵达美洲最早的时间不在17世纪,而是16世纪,即西班牙人最初设立在南卡州威雅湾和佐治亚州沿岸的圣米格·瓜达卢佩殖民地。盘踞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一带的西班牙探险家艾利翁(Lucas Vázquez de Ayllón,1480-1526)经查尔斯五世恩准,曾于1526年载了一船人,包括妇孺、黑奴、牛马猪羊,还有两位不太情愿的道明会教士,来到北美海岸。据同时代的作家奥维耶多(Gonzalo Fernández de Oviedo y Valdés)记载,一行人到了当地后,疾疫肆虐,艾利翁饮恨撒手人寰。同行的董瑟(Gines Doncel)及其党羽叛变,为非作歹。值此危急存亡之秋,黑奴愤然起义,火烧董瑟楼,之后遁入茂林之中。倾家荡产之后,殖民地告吹,众人铩羽而归。
如果美国建国的时间真正按照黑奴抵美来算,“1619”应让位于“1526”,否则如何能说尊重非裔人民的历史?但不论是“1619年项目”还是“1526年项目”,我们仍在期待“15000年项目”,承认一万五千年前美洲原住民抵达北美那可歌可泣的美国史诗。

葡萄牙裔西班牙绘图家、探险家迪奥戈‧利贝洛(Diogo Ribeiro, 1478-1526)绘制的艾利翁属地地图
“中国礼仪之争”:保守派学者对华态度的一次悄然分流
2020年无疑是中美关系在贸易战、疫情战、舆论战,以及美国鹰派急于在俄国之后再觅一“他者”的背景下,美国左、中、右翼疑华态度大汇流的一年。然而大潮之下,总有暗流。譬如,在经济保守主义遇挫、社会保守主义抬头之际,右翼学界也充斥着内部张力。这一定程度上源于右派思想阵营本身的智识多元性,还有一个原因是教廷的微妙态度。今年,教皇以“不牵涉美国内政”为由拒见蓬佩奥,挑起了美国新保守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两派之间的争吵。新保守主义受到怀疑宗教的政治理论熏陶,又基于当前逢中必反之原则,故而不忌讳批评教廷。天主教学者则自动为梵蒂冈辩护,申饬“新保”人士不明教皇“超然的神学视界”,也不具有长时段的历史思维,因此不能揣度圣座经略东土之奥意。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施特劳斯的门徒和天主教信徒既唇齿相依,又互挖墙脚。七十年代,众多天主教徒皈依施特劳斯。但近期,天主教不断吸引施派青年回流。数年来大力向施派传福音,并在哈佛法学院开辟出一片天主教殖民地的维米尔(Adrian Vermeule),近期在右翼媒体《纽约邮报》上撰文与蓬佩奥“商榷”,提出梵蒂冈与北京改善关系不但合理,而且有益——这显然符合梵蒂冈的思想趋势。笔者在圣座国务院、主业会(Opus Dei)等处得到的总体印象是,尽管梵蒂冈内部声音不尽相同,但主流的观点认为:目前是教廷吸取17、18世纪“礼仪之争”的教训,是真正谋求文明对话的契机。天主教历史学家尤其注意到,如果对比近代早期以来教廷和所有世俗权威的关系,中国对教廷的态度不但正常,甚至恐怕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温和、理性得多。另一方面,亲近教廷的学者强烈感到美国外交界自冷战以来,惯于利用教廷,但不屑于协商,每涉及国际冲突问题,从来都把教皇的意见抛诸脑后。这种背叛感也导致一些保守派天主教学者反感西方鹰派,维护教廷与北京对话。这些怀念耶稣会的声音通过层层渗透,逐渐蔓延到天主教知识分子群体之中。虽然尚无实证研究,但笔者认为在西方普遍对华提高警惕的情况下,的确存在一股对华态度较为开放的社会保守派思想。
这种态度有两个思想理论基础。其一,人文主义政治思想强调美德、才能、审慎,淡化政体之别。在这一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文艺复兴史家詹姆斯·汉金斯(James Hankins)从“德政”角度出发的亲华言论。他近日在右翼知识分子大本营《克莱蒙特书评》撰文斥“中国缺乏罗马法传统中的权利观、义务观”为谬论,颂扬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提出中华文明未来的政治愿景必是复合、融通的产物,不应贴上简单化的政体标签。诚然,文艺复兴政治思想轻“政体区分”、重“讲德修学”。如帕特里齐(Francesco Patrizi: 1529-1597)质疑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循环论:之前,多数中世纪晚期政治思想家坚持认为,政体相互转换,按照周期规律兴亡交替。帕特里齐却反问,不论是何政体,若行德政,为何要亡?与之类似,布兰多里尼(Aurelio Lippo Brandolini)在《共和制与君主制比较》中也淡化政体,强调美德。对话末尾,马蒂阿斯(Matthias)虽然已经成功劝服多米尼科(Domenico)偏向君主制,但话锋一转道:归根结底,共和法制不一定不佳,君主制也不一定贤明,所以不论政体,还是要看哪里有德行高尚之人。如此一来,“贤能政治”这一论域便成了文明对话窗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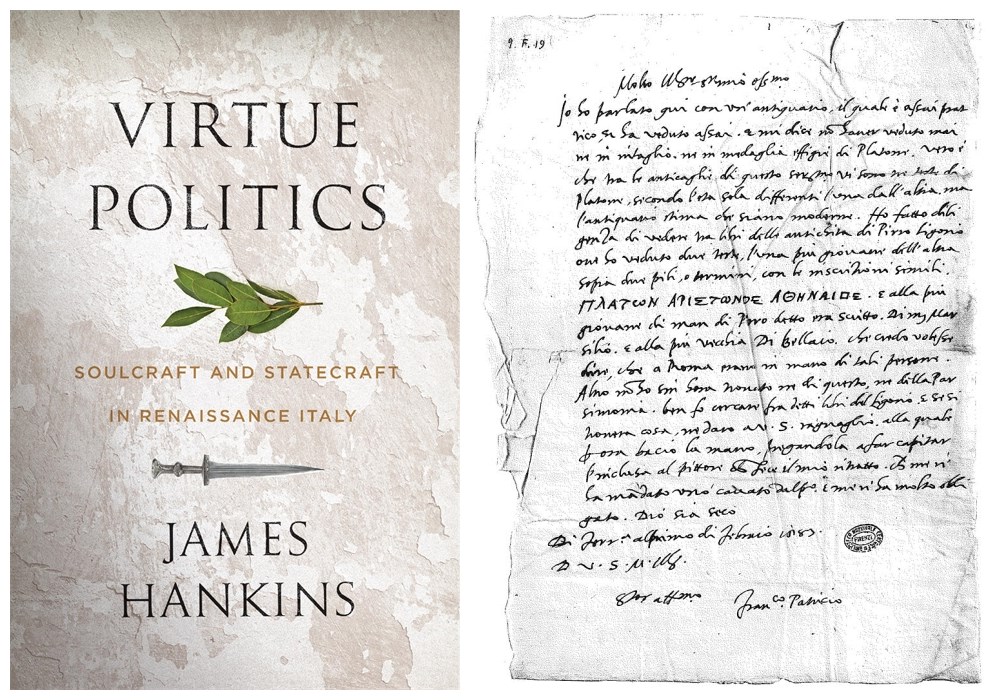
左:汉金斯的新书《美德政治: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灵魂术与治国术》
右:帕特里齐致佛罗伦萨政治家巴乔·瓦罗里(Baccio Valori)书信手稿
第二个思想基础是耶稣会的自然法遗产。耶稣会思想家每至一地,将所见风俗笼统地归入“万民法”(ius gentium)之中。尤自萨拉曼卡学派始,“万民法”的界定逐渐在最初罗马法的定义之外,获得了更多的规范性意义。同时,在各级法理之中,神圣法(ius divinum)与自然法(ius naturale)的界限慢慢含糊;自然法与万民法又逐渐打通,因为长时段的万民法可以被视为体现自然法的实际效力。而当教士们来到地方,发现当地不但有社会中的习俗,其实也存在着政治组织时,他们又必须面对如何界定“城邦法”(ius civile)这一难题。尤其是在印度和中国的广大地区,有时“城邦法”典即是习俗法、立法和判例集结而成的。因此,随着时间推移,教士们开始不断扩充“万民法”,使之成为极为强健的一股法理来源。如此合理化了当地法律,即与宗教不相抵冲。这一传统的中国代表是利玛窦,而在南亚,亦有一位印度版利玛窦:耶稣会传教士诺璧立(Roberto de Nobili)。他来到印度南部后,采用“适应法”(accommodatio),从婆罗门贵族入手传教。他习梵文、泰卢固文、塔米尔文,将印度习俗归入自然法下的“万民法”,以为与天主教毫无冲突。这是近代早期自然法学在时空流动之际显现出的灵活性。许多当代的宗教保守主义学者用耶稣会的自然法传统来合理化教廷在处理国际关系、外交事务时,考虑各国国情的变通之道。

利玛窦与徐光启(1670年《几何原本》)

法兰西耶稣会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
不论是人文主义还是自然法,这种使用过去的观念重思国际关系的做法再次说明,历史转变的动力之一即是对更久远历史的再想象。有选择、有目的地使用过去来介入时政辩论,这本身也是值得被我们历史化、规范化的一个智识传统。
印度社会危机的潜台词
今年印度坎坷不断,四年来“印太战略”的承诺,今成梦幻泡影。克什米尔问题悬疑未决,中印边境摩擦余震不绝,防疫仍然未果,经济衰退超乎预料,最近又在施行农业改革后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抗议。在归纳印度深陷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时,当代“印太”鼓吹者们似乎忽略了1924年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在最初提出“印太”理论时阐论的一大问题:殖民主义对亚洲的政治意识意味着什么?时至今日,亚洲许多地区的问题的根源仍可以追溯到殖民和反殖民时代。譬如,南亚的语言文化极为多元,然而政治思考范式停留在简单粗暴的“二民族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即便在“二民族论”内部,双方也并不明了彼此的历史关系与精神遗产。
政治争议往往以争夺历史遗产的形式呈现,例如最近印度各界对如何纪念印度独立运动领袖钱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诞辰125周年的舆论战。其实,反殖民历史除了激发异议,又何尝不能促成对话?不论是印度国内的宗教群体还是中印关系,都可以在反殖民历史记忆中找到互信基础。今年十月,印度史学者鲍斯(Sugata Bose,前述鲍斯之侄孙)在纪念史家哈桑(Mushirul Hasan)的讲座上,做了一场“民族主义时代的亚洲普世主义”演讲,惋惜二十年代初的亚洲团结刚一萌芽,便被日本军国主义化的“泛亚洲主义”扼杀在摇篮之中。他和塔帕尔(Romila Thapar)、政治理论家梅塔(Pratap Mehta)等众多既“民族主义”又“国际主义”的印度学者一样,认为亚洲合作的基石是南亚、东亚、东南亚,甚至中亚和西亚共享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记忆,因为只有争取自由解放的经历才能超越傲慢与偏见,在时间和空间流动之际打通道统的束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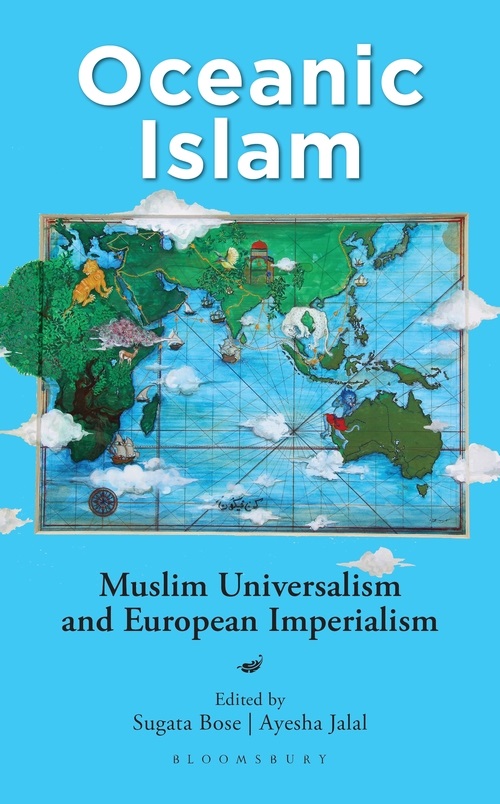
鲍斯与妻子——塔弗茨大学阿伊沙·贾拉尔(Ayesha Jalal)教授合著的新书《大洋伊斯兰:穆斯林普世主义与欧洲帝国主义》
再以中印关系为例。今年3月,印裔中国史学者郭旭光(Arunabh Ghosh)的专著《算数: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统计学与国家治理》(Making It Count: Statistics and Statecraft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千呼万唤始出版。作为中印比较史、交流史、统计史家,郭旭光呼吁在新冠疫情危机时刻,各国政府更应保证数据诚信。他也涉入了跌宕起伏的中印关系辩论,含辛茹苦地帮助印度社会释读中国信号,致力于在“亲华”“仇华”外开辟“知华”一派。正值印度负责“社会正义与赋权”的国务大臣阿塔瓦莱(Ramdas Athawale)呼吁“关闭所有售卖中餐的酒店”,触怒了不少印度商家之时,郭旭光警示印度对华研究严重不足,因此匮乏外交政策制定的知识基础,导致公共论域关于中国问题的辩论充斥着无知、俗见和妒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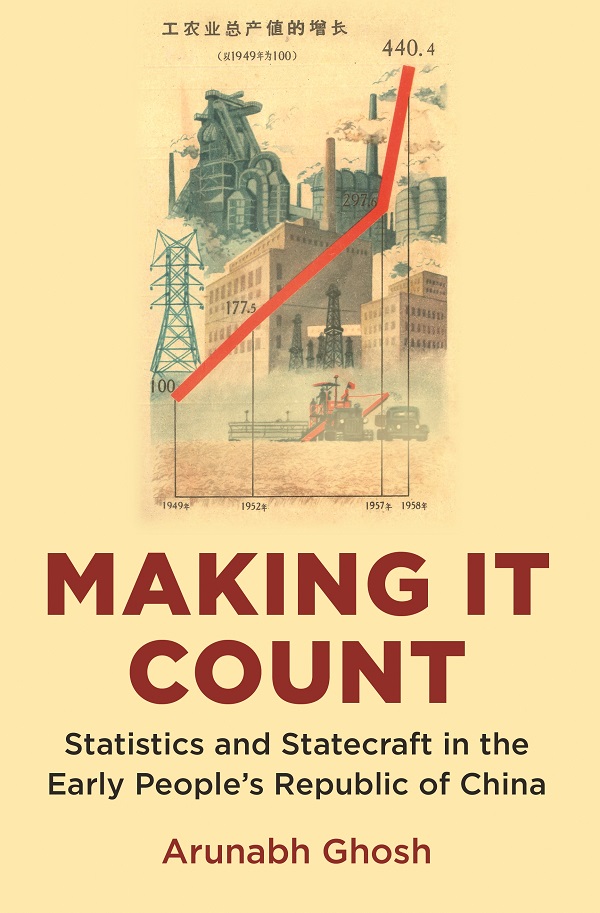
郭旭光《算数: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统计学与国家治理》
对等视之,我以为中国学界的挑战是将批判性反思印度化为自我教育的动源,而非自鸣得意的本钱。中国史学、政治学和语言学界应普及印度研究成果,介入公共论域,形成“观印度而内自省也”的舆论风气。我们能否在2020年印度政治、经济、社会多重危机之际仍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谦逊的姿态,自勉作出更好的印度学研究来,这是中国学人的一大智识和学养考验。
另一部中印关系领域值得一读的新书是塔帕尔1957年赴华考察的笔录《东望:中国的僧人和革命者,1957》(Gazing Eastward: Of Buddhist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China, 1957)。塔帕尔不仅考察了敦煌和麦积山石窟,还留意观察新中国的社会百态。在印度左翼对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普遍失望的气氛中,塔帕尔尤其思索中苏模式之异同,探索中国的农村问题。

1957年塔帕尔在中国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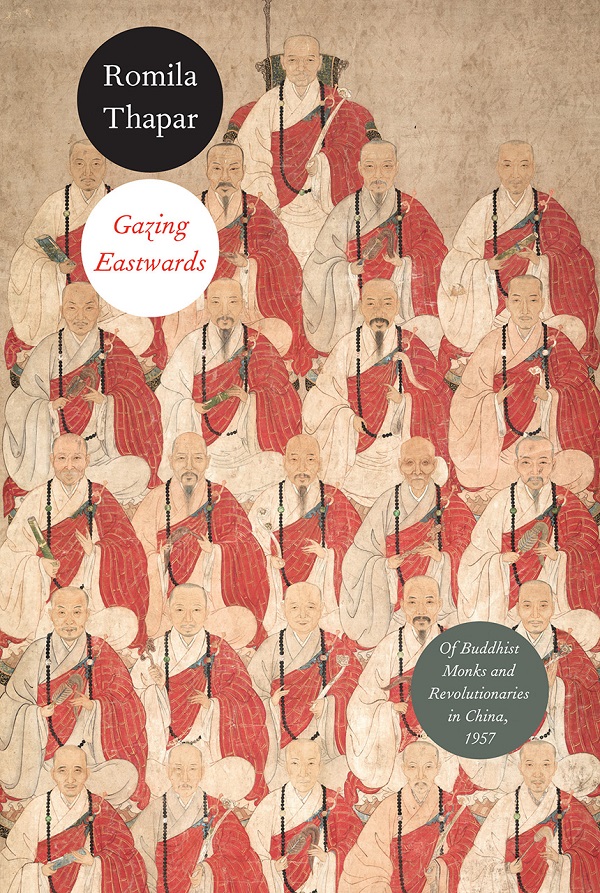
塔帕尔的旅华笔记《东望》
说到这里,不能不谈印度的农村问题,尤其是通过最近席卷印度的农民抗议运动,透视印度社会和思想的现状。印度农村问题由来已久:定价机制混乱、基础设施不足、产量提速慢。尽管农业经济在印度经济增长中占比持续下跌,但印度农民仍占劳动力近一半。然而,因为债务、气候、政策、公共心理健康等原因,印度农民自杀率居高不下。此次争议在于农产品定价。从前,印度政府依照“最低支持价格”(Minimum Support Price, MSP)介入市场,定价采购。此次改革旨在通过自由化,拓展农民的供销选择。农民上街后,前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巴苏(Kaushik Basu)与和莫迪经济顾问、前亚行首席经济学家帕纳加里亚(Arvind Panagariya)各执一词,辩论激烈。巴苏赞扬印度农民的道德勇气,与19世纪末美国进步主义农民运动相提并论,还将市场垄断造成的隐性压迫比作“自愿奴隶制”,譬如亨利·休斯(Henry Hughes)为美国南方量身定做的“担保主义”(warrantism或warranteeism, 奴隶主摇身一变为“担保人”,奴隶则被法律授权成为“被担保人”)。将不不公正的市场比作“奴隶制”,看似有些言过其实,但它反映出左翼经济学家特有的敏感神经。自从亚当·斯密被程式化为“看不见的手”,经济思想家便常常以历史上的“担保主义”为反例,证明市场机制不能盲目地合理化一切看似合法的“契约”。正如休谟(David Hume)警示的那样,实证性命题不一定是规范性命题。
事实上,印度农民与改革开放以来经历农业商品化的中国农户一样,需要市场化改革。但是与中、美、甚至部分拉美、加勒比国家相比,印度尚且缺乏配套的风险缓释政策。骤然撤除历时十年多的管制政策,补给和保障措施又不到位,难免农民不信任政府。在数据企业时代,买方垄断(monopsony)盛行,贫农与大企业之间的议价力很难平衡。不论是政治经济权力的集中,还是政府与市场利益的循环,亚当·斯密都曾警示过后人。广泛而言,契约伦理、信贷资源、技术普及,都依靠长期文化、教育、科研的积淀。只有建立在社会道德的基础上,市场才能持久、灵活、有效运转。印度社会危机的背后是社会凝聚力和公信力的匮乏。
在塔帕尔等印度史家看来,这种不足具体体现在对异议的不容忍。从古印度的佛教徒、景教徒、正命派沙门挑战吠陀婆罗门主义,到中古巴克蒂思潮的平等主义,再到莫卧儿时代伊斯兰神秘主义与印度教哲学的融合,印度传统从来是在逻辑思辨、哲学争鸣、融会贯通中不断发展的。这种文明形态体现在制度之中而超乎制度之外,浸润在更广泛的社会土壤之中。从孟德斯鸠、休谟到密尔,政治哲学家告诉我们:政治制度只是自由的一部分,而独断,甚至残暴的支配也可以变形,甚至无形地存在于社会界域之中。印度的民主共和传统目前面临的更大挑战,恐怕不在于制度框架的搭设,而在于社会文化缺少崇尚知识和宽容异己的氧气。
如今,印度舆论场的核心辩题之一是印度教多数主义的合理性。多数主义作为民主制度的现实,是否与宪政主义之间存在着张力?多数者行使民主主权,代表全体公民的意志立法,本无可非议。但是当多数者制造出一系列潜移默化的社会伦理规范,并借此暗箱垄断市场和政治权力,那么便侵蚀了宪政。因此倘若我们真在经历一场“民族国家的回归”,那么即便不是民族主义本身,它的“虚妄诸相”也应引起我们的警觉。
2020年是危机迭起,日无暇晷、前瞻未卜一年,也是争讼过往的一年。没有不受争议的历史,因为重新阐释、想象、使用历史记忆是社会自我理解、自我调节、自我向导的主要形式。辩清过去,才能滋润语言和思想的贫瘠。而我们共同反思过去的经历,也必将成为亲切的回忆。

- 中方出手连环反制
- 中方连环反制,美指期货应声下跌
- 10位在韩志愿军烈士寻亲线索公布

- 美股继续暴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入熊市
- 美媒:美国国税局将裁员2万人

- 被誉为“活化石”的中国特有树种是
- 被誉为地球之肺,位于南美洲亚马逊盆地的雨林是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