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工作坊︱全球网络、多维叙事:广州口岸史研究应转向大格局
2020年11月28-29日,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中山大学广州口岸史重点研究基地主办的“全球语境—广州视角”历史专题工作坊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召开。来自全国多个高校和科研单位的10多位学者齐聚一堂,以文会友。藉此机会,本次工作坊还举办了祝贺范岱克(Paul A. Van Dyke)教授荣休的仪式。
中山大学江滢河主持了工作坊开幕式,吴义雄致开幕词。吴义雄在致辞中首先向与会学者表达了谢意,他指出当今的口岸史研究早已不再满足于对一个时段、一个城市、一种商品的发掘和叙述,而是转向“时代变迁、全球网络、多维叙事”大格局,将口岸的历史置于更为广阔和深邃的背景与脉络中进行考察和认识,本次工作坊的宗旨也正在于此。接着,吴义雄回顾了范岱克教授在中山大学工作期间的教学与科研成果,并祝愿范岱克荣休之后能有更多的著述面世,为广州口岸史研究开拓更广阔的前景。

吴义雄教授向范岱克教授赠送《广州记忆—中大岁月》纪念册
范岱克进行了主旨演讲,主题是《连官(Leanqua)和晏官(Anqua)与1685-1720年广州体系的建立》。他指出,尽管在广州贸易初期,连官和晏官已经拥有了广阔的全球贸易关系网,但中文史籍中并没有相关的记载。通过爬梳英文、法文和荷兰文的史料,范岱克勾勒了连官与晏官二人的贸易行迹。
对连官与晏官的记载最早可见于18世纪早期,他们常常往来于广州、澳门、福建,并参与了东南亚贸易。他进而指出,连官和晏官的事迹反映出当时广州的高级官员参与了对外贸易并从中获利,此种活动直到1720年才被禁止。由于清政府政策的差异性,商人没有得到一视同仁的待遇,不同群体的商人面临着不平等的境况,这导致了中国商人在广州贸易中逐渐居于劣势。范岱克关于两位行商的研究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清代早期广州贸易运行体制的了解。

手捧鲜花的范岱克
一个千年与两个广州
第一场发言主题是“一个千年与两个广州”,旨在从长时段探讨广州在全球发展中的位置。
广东省社科院李庆新的讲题是《南海贸易的第一个“广州时代”——基于8-10世纪考古资料的思考》。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海底沉船考古项目的开展,暹罗湾叻丕沉船、黑石号沉船、印坦沉船、井里汶沉船等均出土了与广州相关的船载遗物,为研究南海贸易的两个“广州时代”提供了大量水下考古资料。李庆新指出,8-10世纪南海贸易进入繁荣阶段,广州港在此贸易网络中具有首位性、中心性和代表性。经过数个世纪的起伏,广州在15世纪再度重返主港地位。两个“广州时代”的差异在于,第一个“广州时代”是单一中心的“一元结构”,第二个“广州时代”是广州—澳门组成的“复合结构”。两次“广州时代”的更迭与差异显示了中国政治经济的历史变迁和全球海洋贸易市场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展现了全球化不断深入的历史趋势。
中山大学郭丽娜提问,发言中展示的广州出土木屐是否外销订制品?李庆新回应到,出土木屐数量共十八只,外观一致,至于它们是出口的订制品或是广州人的日用品,尚无定论。
第二位发言人是吴义雄,他以《1814年中英“贸易新章”的解析》为题,利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中文档案,通过对1814年两广总督蒋攸铦批准的“中英交往新规”以及附加限制性条款的解读,揭示了鸦片战争前中英关系转折的关键一幕。他指出“新规”的出现,是英国人在通商关系中权势日益增长的结果,他们利用渐增的话语权向清朝的“夷夏”观念展开了攻势,以“国家名誉”为焦点争取在广州的贸易权益,而广东当局的妥协实质上意味着全球化的浪潮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将清政府卷入其中。
中山大学李爱丽提问,发言中提到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喇佛等人,是否也要留意他们在澳门的活动,从而更加全面地展现出来英国商人的集体行动机制。吴义雄肯定了这一思路,表示相关的情况需要更深入地挖掘史料进行探讨。
第三位发言人是广州美术学院蔡涛,他报告的主题是《<现代版画>:新启蒙与战时现代美术之路》。通过解读广州的现代版画家李桦的人生路径,蔡涛以广州刊印的《现代版画》杂志为例,认为其艺术风格的转变反映了现代艺术的战时转向,并且展现了中国的美术运动与国际画坛间的互动。他认为,《现代版画》可以被看做是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并为重建以广州为中心的全球美术史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报告结束后,蔡涛教授向全场老师展示了珍贵的《现代版画》杂志原件。
李庆新就报告中提到的广州版画家到佛山购买材料一事,指出在晚清到民国前期,佛山的印刷业、图书出版及绘画艺术等十分兴盛,许多图书销往东南亚,那么在广州成为现代艺术中心的过程中,佛山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蔡涛回忆在上海鲁迅纪念馆查阅十八卷《现代版画》时,发现郑可将他在巴黎学习到的艺术理念用于重新看待本土的、传统的材料,将民间祭祀纸品的图案作为创作中的灵感,可以说是现代版画对本土艺术要素的再利用。随着这些版画流传到上海、东京等地并得到了重新的诠释,佛山在现代美术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也得到了证明。
金属、口岸与全球科技史
第二场报告的3位发言人在全球科技史的视野下,借助科技考古的成果及实物史料的发掘,讨论广州作为口岸城市在全球物质文明交流和技术传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中国科学院大学的韩琦做了题为《科技史视野下的广州》的报告,他认为从全球史和物质文明交流史的视野出发,利用多语种的史料,可揭示从清朝康熙年间至鸦片战争之前,以广州为核心的历史空间所发生的科学知识交流。并且,对科技史的研究要既见物也见人,通过地方士人、各国商人和传教士之间的互动,说明不同的人群在科学仪器和科学知识的传播方面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作为贸易口岸的广州在中西科学与技术交流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江滢河提问道,发掘的史料中有无提及广州本地的读书人?韩琦表示目前所能看到的多为零碎信息,虽然在1820年左右的英国期刊里能看到一些阮元诗作的英译,说明英国人对广州的信息有一定了解,但要将这些零碎文献整合为完整图景还需要付出巨大努力。董少新问,如何看待传教士宋君荣在信中言及中国宫廷里葡萄牙的天文仪器要优于法国仪器一事?韩琦认为这可能取决于当时来华传教士的身份与背景,一些葡萄牙传教士可能有进行天文观测的需求,这导致了他们所携带的天文仪器比一般传教士所用的更为精良。
第二位发言人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孙琳,她的讲题是《明清中国和美洲之间全球的白银流动:历史文献和科技分析的结合》。她在演讲中提供了对16-19世纪多国的白银货币进行科学成分测定的数据,指出明清时期中国本土的银锭(银币)含银量均高于美洲及其他地区,这种纯度差异可能会导致几十年来学者们所注意到的巨大套利现象。由于目前所获样品数据相当粗略,量化白银纯度差异所造成的经济影响和政治影响仍需进一步探索,但将科学成分分析纳入历史研究有助于重新思考现代早期的全球循环。
对于韩琦关于样品采集年代的提问,孙琳回应道不同年代的样品采集的确是一个难点,而且白银样本也存在数量少、易变黑等问题,因此在数据测量上有所误差,难以解释人们通过颜色判断白银含银量的准确性问题,以上种种都是这项研究需要克服的难题。范岱克提到,在近代以货易货的贸易多不使用白银,例如很多广州帆船到东南亚进行贸易时都不携带白银,而当时此类贸易的规模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量相当,那么应该如何评估白银在近代贸易中的重要性?孙琳以自己研究的满洲贸易史为例,说明明末清初中国的北部边疆贸易聚集了大量从国外流入的白银,而白银流入是清朝前史研究的重要命题,因而引发了她对白银研究的关注。可见白银全球流通对彼时区域变迁的深远影响。
随后,暨南大学黄超以《广州贸易时期的跨国金属交易研究》为题,介绍了“tutenague”等金属的跨国知识史流变以及中国白铜在欧洲的传播和流通的简况,进而探讨了广州贸易时期白铜在广州的加工、传播和交易的概况。“Tutenague”命名的复杂性及其流通区域的文化差异等,都给相关的研究提出了挑战。黄超认为金属产品在中西方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相关的研究方兴未艾,有着广阔的前景。
梁立佳提问,应如何看待在东南亚贸易时代,欧洲国家利用中国、日本、东南亚、印度之间的金银价格差价进行中转贸易以牟利的历史现象?黄超表示他也在关注这一问题,而且前辈学者已经整理了丰富的历史文献,以新方法推进前人研究将是下一阶段的工作。暨南大学张廷茂注意到铜在澳门贸易中的重要性,询问在商业文献中的“copper”与白铜是否有所不同?黄超表示史料中的“copper”是一个大类,红铜、紫铜、黄铜、白铜等等金属都可以包括在内,像在《粤海关志》和《户部则例》里并无有关“白铜”的分项记载,应是被归入大类当中了。范岱克补充道,贸易文献中经常不会准确详细地记载商品的名称,因此在相关研究中需要借助现存的实物加以考察。郭丽娜谈到了“在文学作品中往往会发现历史的第一现场”,像银制烛台便在《悲惨世界》里被提及。她认为可以从欧洲各国的档案馆和博物馆中发掘新史料,将此作为研究跨国金属制品贸易的一个重要途径。

工作坊现场
政府、商人与市场
第三场报告“政府、商人与市场”的核心问题是近代全球贸易中政府的权力、商人的角色以及市场的互动关系。
河北大学梁立佳的发言题为《关于近代太平洋毛皮贸易研究的几点思考》,基于近代太平洋贸易的复杂性,他回顾了学术界关于太平洋毛皮贸易研究的主要理论和视角,包括现代世界体系论、中国中心论、民族国家建构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等不同的诠释框架。梁立佳认为,近代太平洋毛皮贸易的兴衰是理解现代早期世界体系的形成与发展的生动案例,俄美公司与美国商人在对广州口岸毛皮贸易的合作是诸多国际因素中最为引人关注的。展望未来,他强调在近代太平洋毛皮贸易的研究中,要注重对中国本土文献、东北亚区域文献、美洲西北海岸文献的挖掘与融汇。
沈宇斌提议,可从环境史尤其是动物史的视角来进行毛皮贸易的研究,另外,考虑到俄国的犹太商人关系网,近代太平洋毛皮贸易中是否也存在犹太商人得因素呢?梁立佳回应,犹太商人的网络确实存在,且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值得关注。范岱克关注的重点在于史料,提议除航海志外,可参考其他类型的材料,以研究毛皮在进入广州后如何流向国内市场,这是目前有关海运毛皮贸易研究缺失的重要环节。
中山大学侯彦伯报告的主题是《条约贸易初期广州的商业形势与中英商人(1843-1847)》,他利用英国外交部档案,剖析了英国租地兴建领事馆而引发的交涉事件,即耆英坚守《虎门条约》第7款“华民不许勒索,英商不许强租”的原则,拒绝李太郭改造十三行区的提案之事。他指出国际条约不仅是外国领事赖以争取权利的“矛”,而且是清朝官员用以遏制外国领事不当要求的“盾”。不同于既有研究多从消极的方面评价条约时代旧行商的没落,侯彦伯的研究表明,旧行商在条约贸易时代之初不断地采取积极性行动,以应对新的挑战。
江滢河关注当时在广州贸易的行商是哪些人?侯彦伯回应说主要还是伍、潘两家为代表的旧行商。董少新问,另外几个条约贸易口岸与广州有何不同?侯彦伯认为,在英国政府眼中福州和宁波的通商是不成功的,由于广州旧行商的干预,英国人无法从福州、宁波等通商口岸就近购买茶叶。上海以物易物的贸易习惯给英国商人带来了新的不便。而厦门的贸易则更为奇特,厦门商人仅从英国商人手中购买商品,却很少售出货物。商人群体产生的变化和香港在条约口岸贸易中的角色是黄素娟关注的重心。侯彦伯认为在19世纪40年代末期到50年代初期,旧行商仍保有一定的势力,而香港的商业化并未达到英国政府和商人的预期,仅仅承担着“广州的货栈”的任务。
现代世纪新篇章
第四场报告名为“现代世纪新篇章”,两位讲者将研究时段置于20世纪初期,从新的视角探讨了广州的历史变迁。
广州大学夏巨富的报告题为《“新中存旧”:清末广州商务总会筹建及其活动》,他的研究以商会档案、广州本地的报纸和东南亚的刊物为基础,着重考察清末民初广州商务总会的筹备过程、组织运行及该组织对地方活动的参与,研究清末商会在商界的角色定位及其作用。他指出清末商会势力与旧式行会组织相较,表现出“新不如旧”和“新中存旧”的双重现象。他还提出要横向比较近代商会的历史,以探究其地方特色。
广州图书馆黎俊忻认为,对商人团体的研究不仅要注重引用报纸、档案等史料,也要着重考察当时商人的具体活动和心理变化,应挖掘不同类型的史料如私人的文献。夏巨富回应,商会史、制度史研究中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局限,他在自己的研究中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尝试克服“只见制度不见人”的研究难题。对于黄素娟“如何判断新旧商人”的提问,夏巨富表示“新旧”概念是相对的,应将这一概念置于清末的历史背景中理解,商会相对传统的会馆、公所、行会势力而言具有新的一面。周湘认为研究广州本地的商会时应注意到英国商人和广东华侨商人的示范作用,也就是地方特定历史场景。
广东财经大学的黄素娟的讲题是《从军事重地到筹建公园:民国时期广州越秀山的意义构建》。黄素娟尝试通过对民国不同时期广州各界人士参与规划、改建越秀山的情况,及其中蕴含的土地控制权和建设经费筹集等问题的探讨,分析了现代城市空间重组所反映的话语转向。她认为,回顾越秀山公园的历史,从“粤秀连峰”到“越秀公园”,从文人雅聚的游赏之地转变为表达革命话语的实在场景,实际上重塑了城市空间的社会记忆。而多次游艺会的举办,也体现了不同的群体在塑造广州现代城市空间中的作用。
董少新提问,公园作为一种西方城市化的产物何时在中国出现?黄素娟回应,公园被视为从西方引进的公共空间的一种形式,一直是城市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李德英等人的研究,公园在中国的引入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租界里的公园,第二个阶段为清末新政时期的“公家花园”,第三阶段则是1920-1930年间在各大城市市政府组织下兴建的“公园”。董少新补充道,越秀山在以往朝代作为军事重地的问题,在广州城市史中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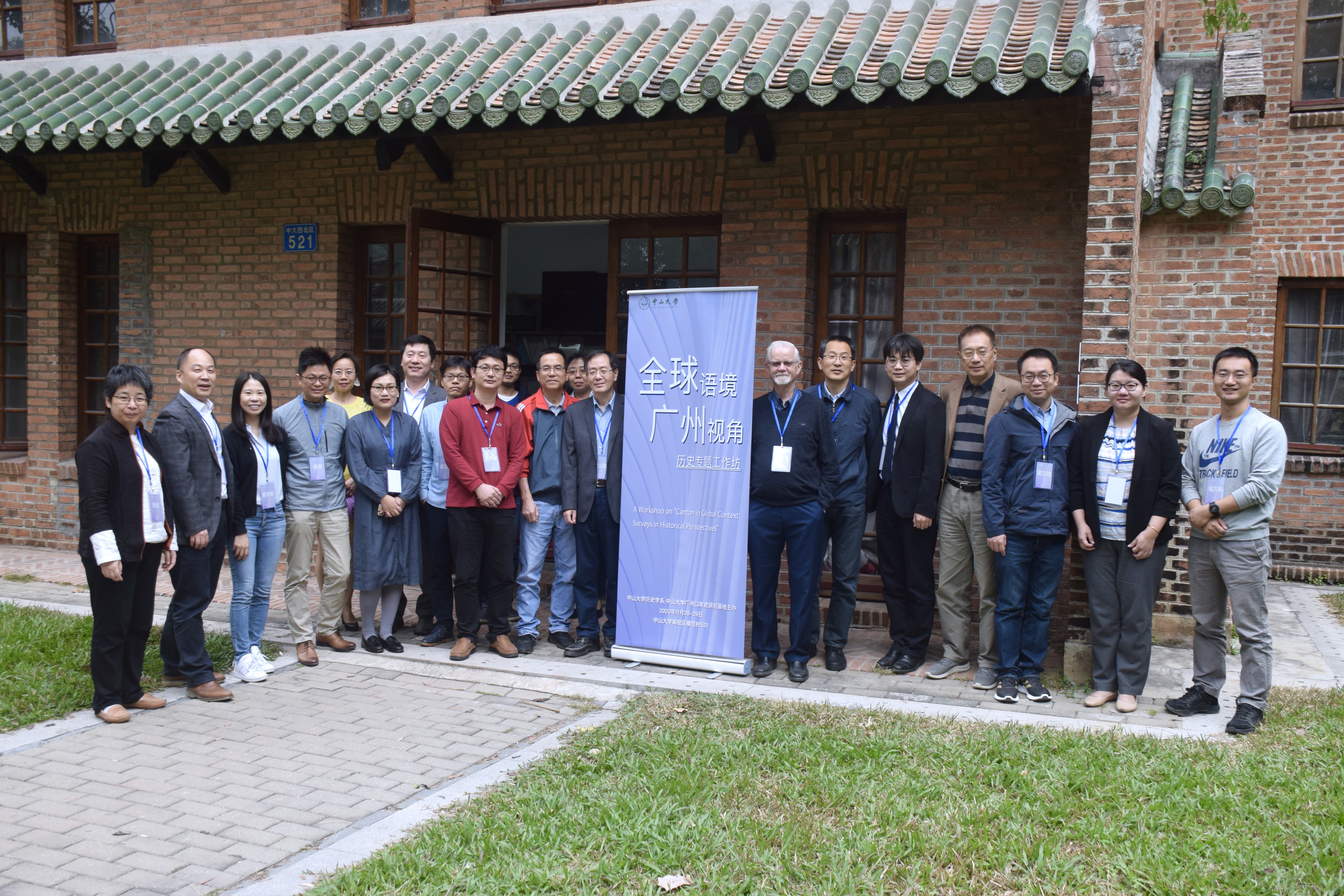
与会学者合影
文献、文物与新知识
第五场报告的报告集中探讨如何从文献学、博物学、图像学的角度看待中西交流中的异与同。
第一位报告人是来自复旦大学的董少新,他报告的主题是《文献立场与历史记忆:以广州“庚寅之劫”为例》。他首先提出文献是有立场的,即便是最原始的文献亦是如此。其次,文献的立场影响了文献留传,从而影响了人们的历史记忆。他以清初广州城被攻陷的事件为例,分析了征服者、被征服者、广州人民、耶稣会士和荷兰使节等不同身份的人著述中呈现的不同立场。他进而提出了构建“西文中国史料学”这一学科构想,这将有助于突破固有的史学研究框架,在全球史的视野下考察中国史的进程。
程方毅认为,广东地区的族谱、墓志和碑刻也可以作为一种有着自我立场的文献。董少新认同家族记忆类型的文献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并强调多语种文献互证的必要性。孙琳提问扬州屠城和广州屠城在叙事类型上是否存在共性,董少新回应记载扬州屠城事件的西文文献尚有待深入研究。
中山大学程方毅的报告《地生羊与鞑靼羊(Tartar Lamb)——两种博物知识体系的交流与遭遇》别有趣味。通过对比中国和欧洲早期博物传统处理“地生羊”进入本国博物系统的差异,他考察了随着17-20世纪欧洲博物馆学的发展,博物学者们对“地生羊”这一超自然文化遗产的态度的变化。同时结合英国博物学者对于中国的认识与研究兴趣的变化,他还探讨不同模式的知识传统之间的交流进程。他总结道,近代博物学在全球扩张中对各地的物产进行了科学帝国主义的描述,它既是非帝国主义的,也是非科学的。
郭丽娜表示程方毅的报告非常有趣,在研究思路、资料运用和题材选取等方面给予了她很大启发。她询问鞑靼羊是否有拉丁文学名,唯有拥有拉丁文学名后才能被纳入了欧洲的博物学体系之内。程方毅回答,虽然鞑靼羊的学名并不来源于拉丁语,但它确实有拉丁文学名。
随后,听众们的注意力从精美的文物转向了一本别具风情的画册。中山大学江滢河的讲题是《德格里画册与早期广州外销画》,他以现藏于美国迪美博物馆的德格里画册为例,指出该画册是研究早期外销画的重要资料。18世纪全球艺术史变迁中存在着的“从贸易画到外销画”的变化过程,他概况了中国外销画市场从区域性(东亚,东南亚)贸易向全球(欧洲)拓展的历史过程。他强调对外销画绘画特性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中西绘画技法的融合方面,应该包含更多对中西交流视觉表达的探讨,以更广阔的视野去对中国外销艺术品进行质性研究。
董少新对早期中国山水画在欧洲的流传情况以及西方人在中国购买画册的情况很感兴趣。江滢河回应,耶稣会士带回欧洲的画册不一定是购自各个口岸,也有可能购自诸如北京、南京等地。他指出18世纪欧洲人购买中国山水画作为纪念品的情况并不多,这一收藏趋势到了晚清才逐渐上升,山水画成为一种兼具装饰性和知识性的藏品。韩琦指出,画册中有一些画采用了透视的技法,带有中西融合的色彩。江滢河肯定了这个说法,并说明目前尚无法厘清相关技法的来源。
国家与生态的边疆
第六场报告的主题为“国家与生态的边疆”,两位学者探讨了国家因素在资源、生态边疆的扩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中山大学费晟作了题为《论南太平洋地区的中国资源边疆与生态变化(1790-1920)》的报告。他从生态—文化网络构建的角度,考察了近代中国的市场需求、海上贸易、跨国移民及产业投资等因素,如何合力将南太平洋地区的自然产物转化为商品,世界市场的发展推动了当地生态与文化的重塑。费晟认为,这种历史过程彰显了中国因素在近代全球生态交流与重塑中的不容小窥影响,未来的研究有必要深入发掘中国在全球史发展进程的主导地位。
在讨论环节,董少新提到任何历史叙述背后都必然存在价值判断,那么如何判断全球生态变迁中的国家因素呢?费晟赞同要有正确的价值判断,认为他运用“资源边疆”这一概念旨在说明自然中的特定物种、商品的流动必然导致相应的生态转变,各种人群的客观作用是有待考察的问题。程方毅提问,报告中提及的进口动物毛皮,到达广州后的分销情况如何?费晟回应,据他了解,有相当数量的皮货被销往北方,广州本地的毛皮消费规模有限,且本地毛皮加工业并不发达。
中山大学沈宇斌发言的题目为《发展型国家、全球植物学网络与抗疟药物:20世纪30-50年代云南的金鸡纳树栽培》,他反对沿用西方金鸡纳树研究史中占主流地位的帝国—殖民研究范式,主张应立足本国历史来探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成功的金鸡纳树栽培项目。他认为云南河口的金鸡纳树栽培项目不仅仅是科学史研究的对象,而且应将之置于全球脉络的视野下国家与地方互动的进程中予以观察,战争和国内、国际政治合力形塑了当时的生态环境。
梁立佳提问,疟疾作为传染病在20世纪5、60年代的中国较之以往是否更为严重,以及大量人口因边疆开发的需要而向边疆地区的迁移是否扩大了疟疾的传播?沈宇斌认为确实如此,但反过来看,人类活动对环境的长期改造也会抑制疟疾的影响。程方毅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金鸡纳树与其医疗用途的联系何时为人们所知,二是关于发展型政府、发展型国家的理论背景。沈宇斌指出奎宁的提炼在19世纪30年代便已实现,但要到19世纪末人们才知道奎宁通过杀死疟原虫来治疗疟疾的原理。至于发展型国家的概念,来源于美国学者对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研究,强调的是技术官僚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最后,上海社科院的施恬逸和董少新共同主持了圆桌讨论环节。董少新终结了两点收获,一是要弘扬范岱克教授的治学精神:作风低调、学风扎实、潜心于文献的研读;二是要广泛涉猎各个领域,从而促进自己的研究。范岱克谈到他在中大工作了九年,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善意的关怀,非常感谢所有人对他的帮助。韩琦说非常高兴看到众多海外求学归来的青年学者加入到中西交流领域,期待立足于广州的海洋史、全球史的研究能有更大的发展。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