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默音:作为小说家,我对文字的未来是悲观的
原创 万千 三明治 收录于话题#三明治 · 写作者访谈45个
文|万千
从出版社辞去编辑的工作之后,默音在2020年新出了一本长篇小说《星在深渊中》,30万字,509页。
在这本小说里可以看到许多现代生活的符号,比如书中主角陈晓燕会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写文章,里面提到的年轻女孩喜欢听“米津玄师”的歌曲,年轻人会玩《阴阳师》,看日剧《约会~恋爱究竟是什么呢?》……这是一本离我们现在生活很近的书,同时,作者又用文字制造了一座迷宫,隐藏的路径是书里悬疑情节的核心——主角死亡的真相,而书中错综庞杂的生活碎片为读者揭开案件之外更多值得思考的命题。在大部分场合,这本书会被介绍为有关“失语症”群体的故事,其实里面所体现出来的沟通困境是多维度的,不只局限在某一个群体身上,也不免让人想到,如今的读者还有没有耐心去消化这么长篇幅的故事,接住小说家在书里抛出的问题。
在默音看来,她的小说是写给和她同时代的人阅读的。

默音是谁?从2009年开始在张悦然主编的文学杂志《鲤》上发表短篇小说以来,默音陆续出版了《月光花》《人字旁》《姨婆的春夏秋冬》《甲马》四部小说,除了《人字旁》,另外三本都是长篇。
她一直写得不紧不慢,甚至在大部分时间里非常低调。
去年,在即将迈入40岁的门槛前,她辞去了出版社的工作,为了更专注地写小说。在出版社工作的那几年里,默音每天六点半会起床动笔写一个小时,大概能写1000字左右的内容,然后八点出门去上班。这是她一天里唯一的写作时间。这个习惯一直保持着直到辞职。
每天六点半会起床动笔写一个小时,大概能写1000字左右的内容,然后八点出门上班。这是她一天里唯一的写作时间。
三明治·创作者访谈
生于1980年,作为一个在云南长大的上海知青家庭的孩子,她把自己童年生活的地方也写进了长篇小说《甲马》里,那个叫做弥渡的小镇。镇子很小,四面被山包围,那里的人们从来不看天气预报,想要判断是否下雨就抬头看看远处山尖上云的状态。
14岁那年,回到上海生活,她讲着一口“云普”。由于教材不同,中考进了一所职校,“中层管理”专业,后来才知道这个专业的对口工作是分配到商场当营业员。1995年夏天起,默音在八佰伴商场实习,一年后成了正式员工。那时候她热衷于日本漫画,买了画具,想要成为一名漫画家,也爱看《科幻世界》,构思了一周,写了一篇六千字的小说投稿,得了1996年的“少年凡尔纳”奖项,有300马克的奖金。这在当时几乎是一笔巨款。
第一次在《科幻世界》上发表了作品之后,因为刊登了学校名字和真名,默音还收到了几百封读者来信。她没想过要通过写作养活自己,于是做了很多不同种类的工作:日企翻译、日企IT、日文免费杂志编辑。也在那些年里,陆陆续续地学习日语,通过了成人自学考试。
在2006年,她决心成为一名编辑,开始备考上海外国语大学日语系研究生。因为在豆瓣写书评,认识了出版人,获得了在出版社实习的机会,慢慢正式走上编辑和文学创作的道路。

《星在深渊中》的图书编辑李蕊说默音给她的感觉像是有文字洁癖,她的文字内容特别干净整洁,很少有病句、错字。而最新这本长篇小说在正式出版前,按照默音的记录,前前后后修改了八遍,每一遍几乎都是重写了整个故事,之后还做了两遍审校。
现在,默音继续保持着翻译日本文学作品和写作的节奏,她对一切显得不那么着急,也对咖啡、器皿、旅行都保持着兴趣。
她正在构思一个故事,设定在未来,人类已经不需要阅读了,戴上一个设备便可以感受由其他人扮演出来的经历。她说:“我对文字的未来是比较悲观的。”
以下是三明治与默音的对谈。

#
小说永远是写给与你同时代的人看的
三明治:这次新书是一本字数超过30万字的长篇,村上春树用“跑马拉松”这个比喻来形容长篇小说的创作,你会有这样的感受吗?
默音:写《星在深渊中》这本书最早的计划不是写长篇小说,而是一系列中短篇小说的集合。在日本有一个词叫“连作小说”,就是一本书里每一则中短篇小说的故事是独立的,而其中的人物是有关联的。我起初就是想写一系列跟甜点有关的故事,开始写了4-5篇,包括这本书现在有一个番外,叫做《最后一只巧克力麦芬》,也来自最初的雏形。现在在豆瓣阅读可以读到那则番外。
最早这本书也不叫这个名字,后来重新开始写,它慢慢变成了一个长篇。反正也是经过了很多波折。最后总共写了八稿,我直到写到第五稿的时候,才知道故事里的凶手是谁。
三明治:中间设想过这个故事的凶手可能是其他人吗?
默音:故事里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凶手,最早也写过其他人是凶手的版本。我自己觉得这是我在写作上不够成熟导致的。有些成熟的作家在一开始就把故事的整个构架搭得很好,然后他/她就能按照自己的计划书写。我虽然做了一个大纲,结果这个大纲在创作过程中不断被推翻和改建。一直到第五稿的时候,故事的大纲才大致成了最终的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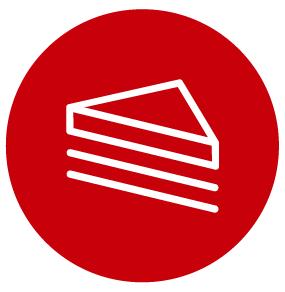
我自己觉得这是我在写作上不够成熟导致的。有些成熟的作家在一开始就把故事的整个构架搭得很好,然后他/她就能按照自己的计划书写。
三明治·创作者访谈
三明治: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很吸引我的一个特质,就是它非常现代。书里很多元素非常贴近现在人们的生活,比如我读到书里有个人物在玩《阴阳师》游戏,或者听米津玄师的歌曲等等。这些元素是你有意设计的吗?你又是如何选择这些元素的?
默音:本书歌单来自某朋友的贡献。其实《甲马》里也有歌单,不过《甲马》里出现的歌单是90年代的歌单,《星在深渊中》出现的是一个更现代的歌单。里面有一两首歌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会和故事的整个氛围有关,所以是仔细挑选的。其他歌曲就是生活在那个时间段、符合书中人物年龄的人会听的歌,没有什么深意。写到的游戏和剧都是在那个时间线正好流行的。
但是书里所有提到的小说都是有深意的,我里面写到的黄依然在看的书都是和她的遭遇有关的。
三明治:在小说创作中处理这么贴近生活的素材时,会有什么困难吗?
默音:其实也没有特别“近”,这本书主要的创作阶段是在2018、2019年,而故事的背景是在2016年,对我而言,隔着两年的时间,它还是一个发生在过去的故事。第二点是,肯定会受到影响。我原来没有想过这本书里会出现这么多跟性侵有关的内容,也是受到2018年的“Me Too”运动影响。外部的声音会投射在创作的过程中。这不是我有意安排的。
三明治:所以其实你的小说更多是想去呈现在这几年里面你所关注到的,或者说对你有影响的一些事件,然后通过小说这个载体去进行一种表达。
默音:对的,在创作这本小说的一开始,我其实只是确定了几个主人公的年龄和身份,要写他们从千禧年一路走来的故事。我自己现在回望,会觉得我们的生活跟2000年前后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一个人的心态、生活方式以及对事物的感知。尤其是进入到“微信时代”之后,互动方式变了,一个人接受事物的方式也变了。
当然你不可能说一本书能体现所有这些东西。最核心的,我原来是想写失语症,但是我想把这些对时代的观察也收纳进来。所以小说出版之后,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觉得它还蛮吸引人,因为故事是有悬念的,有人会一口气读下去;有的人认为里面碎片太多了,拖泥带水。我觉得这两种意见都是可行的,每个人看书有他自己的感受,书的最后完成是靠读者的阅读和再构建。
三明治:有些创作者在面对特别当代的素材时,可能会遇到的一种困难是无法下判断,或者要经历更长时间的反刍才能够动笔。譬如说书里提到主人公陈晓燕的职业是写“公众号”的,但可能“公众号”这个事物本身是只有经历过这十年中国生活的人才会懂的一个词。是否会担心所记录的一些事物是速朽的?
默音:小说永远是写给与你同时代的人看的。也许未来五年或者十年的人再读这个小说,会觉得它依然重要,也可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但最关键的还是跟你一起有过相同时代经验的人来读这篇小说。
几乎整个2020年,我都在翻译樋口一叶的作品,我们跟她隔了120年,而且她在创作中使用的并不是现代日语,所以现在去捕捉她笔下的一些细节感受是非常艰难的。现代日本读者阅读一叶的作品也是通过现代文译本。那么到了我翻译的中文译本,读者能捕捉的只有一些经过过滤的气息了。比如一叶在文中引用了一句歌谣,在她的时代,所有人都知道歌词的前后文和语境,我当然会加注解,但现在的中文读者也只能通过这样间接的方式来了解这首歌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
小说就是一个当下的事物,当然它可以被隔代阅读。不过我觉得当下的阅读是最重要的。
小说永远是写给与你同时代的人看的。也许未来五年或者十年的人再读这个小说,会觉得它依然重要,也可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但最关键的还是跟你一起有过相同时代经验的人来读这篇小说。
三明治·创作者访谈
三明治:所以你书里留下的很多当代生活的符号,也像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种互动,如果有相同体验和经历的读者,可以接收到这个讯号。
默音:就好像村上春树的作品里也会引用很多歌曲,作为读者肯定不是全都知道那些歌曲的内容。当然也有特别迷他的读者会去把整个歌单列出来,全部听一遍,为了更了解他的作品。作者写的时候肯定是有用意的。就像《星在深渊中》里面引用的每一本书都是有用意的,即便读者没有看过这本书也没关系。每一个人在读小说的当下,他的接受程度都是不一样的。
作家张天翼也注意到了,这本书里引用了《地海传奇》。因为《地海传奇》和读到它的黄依然是有内在关联的。小说的很多细节都有用意,就像一个不起眼的碎片一样,有的读者会注意到,我觉得当然是很好的,注意不到也没关系。
三明治:在创作的时候,你会有一个自己想象中的读者吗?
默音:我没有想象中的读者,有几次看到别人说废寝忘食地读这本书,我就很开心。
现在其实愿意写很长的长篇的人真的不多,我自己也没有想会把它写得这么长。写完当然还是很开心的,觉得完成了这样巨大的工程。而且,如果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写长篇的回报率是非常低的。因为中短篇可以先在杂志上刊发,先得到稿费,然后最后再集个集子。很长的长篇基本难以刊登在杂志上。另外一点,就是大家有没有耐心来读这样长篇幅的作品。像今年,我觉得路内的《雾行者》非常好,但是网上看到的讨论也不够多,可能跟它巨大的体量也有关系。
三明治:既然这样,创作长篇小说会是一件特别寂寞的事情吗?
默音:不会。我笔下的这些人物已经跟我的生活太密切相关。我有一天做了一件特别傻的事情,就是直接在我的微信联系人里面搜“杨树海”,搜完才想起来他只是我小说里的人物,并不是真的存在。
我有一天做了一件特别傻的事情,就是直接在我的微信联系人里面搜“杨树海”,搜完才想起来他只是我小说里的人物,并不是真的存在。
三明治·创作者访谈
三明治:这些虚构的人物是怎么样一点点在你生活里变得那么具体的?
默音:之前都还是很模糊的,在我写的前面几稿里,对这些人物都没有任何的外貌描写。可能写到第四稿的时候才加了进去,渐渐清晰起来。
在创作的时候,我每天都会试图去多了解这些人物一点。而且因为大家现在看到的文章顺序跟我的写作顺序不一样,比如说那些人物儿时的回忆,我可能很早就写好了,所以对我来说,我很早就知道他小时候是个什么样的人。但对读者来说,是先看到小说里这个人物成人时的样子,然后才慢慢发现他的过去。
三明治:你去年写了一篇名为《尾随者》的小说,我觉得那篇小说的设计也很巧妙,里面主人公的职业恰好也是公众号编辑。你对这个群体是更有兴趣去书写和关注吗?
默音:《尾随者》这个故事的本质是一个人太羡慕另一个人的人生,想要把另一个人的人生据为己有。如果里面人物的工作不是公众号写手,故事的核心依然是成立的,只是因为事情正好发生在这个时代,所以我把公众号的设定加进去了。这种对生活的“剽窃”可能是任何一种形式。
三明治:是,但是这种设定现在读来会觉得特别契合。
默音: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公众号剽窃现象很严重,而我在《尾随者》里写的这种剽窃方法,可能大家还没有看到过,因为剽窃的是别人的生活本身。

#
为了全心创作,辞去出版社工作
三明治:创作《星在深渊中》时,你的写作状态是怎么样的?
默音:写这本书的时候比较苦,因为一开始我还在上班,九点要到出版社。所以我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写作,写一千字,然后就去上班了。吃早饭的时候,我会看自己昨天写的内容,然后做一些修改。上班的时候,我晚上是不写作的。后来我就辞职了,因为写不动,长篇还是要花很多精力。
三明治:写 1000 字大概会花多久?
默音:一个小时。基本上,我的写作速度就是这样,不管写什么内容,都是一个小时一千字左右。但是这一千字有可能是废的,可能最后完全不成立,我就是先写出来,之后再改。
三明治:从出版社辞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完成这本长篇小说?
默音:辞职的原因是有一种感觉,如果不辞职肯定写不完这个故事。主要是精力有限。我周末一天可以写三千字左右,就这样拖拖拉拉地写,怎么都差口气。后来我觉得不行,就辞职了。辞职时还有书没做完,所以虽然回到家,还一直在做编辑的工作,把手头的书慢慢出掉。那段时间是上午写小说,下午改出版社的稿子。
我记得这本书是从2017年年底开始写,然后正式辞职是2019年的年初,然后到2019年底写完了第八稿。
辞职的原因是有一种感觉,如果不辞职肯定写不完这个故事。
三明治·创作者访谈
三明治:辞职的时候有考虑过经济方面的压力吗?
默音:没有想太多,是因为还有一点点积蓄,觉得一两年内暂时没问题,就没有多想。
三明治:辞职之后的创作状态有什么改变吗?
默音:和预想的写作生活不太一样,主要是在《星在深渊中》交稿后不久,我就开始做樋口一叶的翻译。我起初没有想到这个翻译做了10个月。一开始我在上午写中短篇,下午翻译。后来发现这样的进度好像来不及,就变成全天都在翻译。所以2020年一直到九月我每天都在工作,而且是周六、周日都在工作。
三明治:你是一个很自律的作者?
默音:我觉得写小说和翻译有点相像,需要每天投入一点时间,否则的话,就很容易变成拉松的橡皮筋,没有办法保持状态。保持状态很重要。可能跑步的人会比较理解这一点。
三明治:改稿习惯是怎么样的?
默音:迄今为止的改稿比较漫长,每一稿都是重写。所以《星在深渊中》改了八稿,是指我写了八遍,有一些主干的部分是沿用的,大部分是重新写的。
三明治:我从这本书的编辑那里得知,你交上来的稿子很少有错字、病句,非常干净整洁,这算是一种语言洁癖吗?
默音:不,这只是编辑的职业素养。后来看到校样的时候,还是发现了几个小的硬伤,让我有点后怕,然后又继续改。因为这部小说它涉及一个比较严密的逻辑,虽然表面上是一个城市故事,但因为描写了一个案件,会涉及到里面每个人物在他的时间线做的事,这些时间线最后咬合到一起不能有破绽。
三明治:在长篇小说的完成过程中,编辑能够给到作者怎样的支撑?
默音:一本图书的最终呈现靠的是编辑有关,不管是封面、宣传文字以及对故事核心的提炼等。毕竟书不是写完就结束了,所以编辑有点像长跑者在最后冲刺时的助跑者。现在网店呈现一本书,往往会用一句话来归纳。我自己是无法归纳这个故事的。如果一个作者能够用一句话或者一段话归纳自己写的故事,那可能他都不会去写这本书了。肯定是有很多你觉得无法归纳和无法归置的东西在那里,所以才会让你用这么长篇的体量来表达。

#
原来的理想是当漫画家,不是小说家
三明治:你小时候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是怎么样的,在云南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上海人吗?
默音:不会,但是会有种略微像“蝙蝠”的感觉,既不是上海人也不是云南人。因为我在云南的时候我们家是讲普通话的,在学校所有人都讲云南话,我后来就变成一口“云普”。我刚回上海的时候,我普通话是很不标准的,前后鼻音不分。云南人是没有“昂”这个音的,就是念“安”。
三明治:14岁回到上海,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如何?
默音:那时候刚回上海,可能就觉得物价很贵。之前在云南是感觉不到的,可能县城里大家都没什么钱,你也觉得挺自然的,然后你突然就被抛到一个你可以很清晰地知道你跟你的同学的消费是不一样的状况里。但也没有特别清晰的自卑感,因为那个阶段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念的是中专嘛,很快自己就有收入了。
从县城到上海,最大的文化震撼来自于突然接触到大量的漫画。那个时候我的日常生活,除了上课都在看漫画,是典型的“漫画少女”,然后还跟同学一起画漫画。我原来的理想是当漫画家,不是小说家。
三明治:童年时,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吗?
默音:因为小时候作文写得好,可能有人会鼓励我说,希望你将来成为作家。我自己没有很具体地想过。我十五六岁的时候是一心想画漫画的,还投入了“巨资”买了很多东西,像网点纸什么的。我写了漫画大纲,然后画了封面,拿去展示给一个漫画杂志的编辑部看。那家杂志社正好在我家附近。他们说你起码要画一个16页的故事。那时候我和同样在商场工作的好朋友,两人的休息时间都是用来研究漫画分镜,一开始并没有想要写小说。
另外一本长期看的杂志是《科幻世界》。以前在我们那个县城买不到什么杂志,好像只有《科幻世界》《故事会》。其他纯文学杂志也看过几期,觉得离自己特别远。那时候是1995、1996年,“新概念”也还没举办。
在八佰伴实习的时候,商场办了一个西安碑林拓片展,我被分到展厅待了一个星期。站在四面都是拓片的空旷大厅里实在太无聊了,我就想了一个科幻小说,很快地把它写出来了,6000字,那时候当然是手写。写完我就投给了《科幻世界》。之后就收到了他们的回信。我还记得编辑莫树清老师的字特别好。莫老师写道,我们杂志有一个“校园科幻”栏目,该栏目没有登载过这么长的作品,一般都是两千多字,但是因为你这篇很特别,所以会录用。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又来信说,这篇作品得了1996年的“少年凡尔纳”奖,一年只有一个名额,有300马克的奖金。
三明治:当时什么感受?
默音:当然是很开心的,相当于3000多元人民币,在90年代后半是一笔巨款。
三明治:这笔奖金怎么花掉的?
默音:给我妈了。
三明治:当时觉得成为一个小说家或者一个专业作者是一条明朗的道路吗?
默音:那时候还没有想过自己会一直写小说。这个奖项带给我的,首先是发现“哇,写小说能赚钱”,但很快又发现这是错觉。因为那会儿在《科幻世界》发表稿件的稿费其实是很少的,可能写一篇小说就一百来块钱,你不可能靠这个生活。我后来也继续写了几篇科幻。写得很慢,可能一年才能写一篇的样子。因为还不成熟,绞尽脑汁也写不出什么东西。
另一点是,第一篇小说发表以后,我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可比现在的读者反馈热烈多了。“校园科幻”栏目会出现作者的学校和真名,读者就可以根据这个信息写信到学校。其中有几封特别打动我的,我就给他回信,成为笔友什么的,还有实际见面的读者。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段时间。以至于很久以后我新认识的一个朋友还和我说,他之前看过我在《科幻世界》写的文章。
再后来,2002年左右,论坛起来了,我就在论坛上写恋爱小说,比方说天涯论坛。论坛的写作也没有一直持续下去。和小说世界的重新接触,起源于我想做编辑,开始备考上外的研究生。
三明治:当时是怎么看待编辑这份工作?
默音:觉得是一份理想的职业,可以看很多书——这也是一个错觉。在我表示说想要做编辑的时候,也听前辈说过,编辑的工作可能会和理想有差距。
那时候豆瓣也才刚刚起来,我在上面认识了出版人彭伦。那时他在豆瓣上送书、要书评,他是最早发起这种活动的。我就要了一本书,写了一个书评给他,他觉得我写得蛮好的,我也跟他表达了我想做编辑的心愿,他说那你来实习吧,我就去了“九久读书人”实习。
实习期间,我负责编辑了一本年轻作家的作品合集,整本书读下来,我觉得这样的作品我也能写。我很快就写了一个短篇,写完了不知道应该给谁,就去问彭伦。他说张悦然她们在做一个杂志《鲤》,可以给她们投稿。我重新开始写小说之后的几个短篇都是给《鲤》的。
在我表示说想要做编辑的时候,也听前辈说过,编辑的工作可能会和理想有差距。
三明治·创作者访谈
三明治:那个时候你的创作节奏是怎么样的,还在念书?
默音:我是2009年研究生毕业的,毕业后没有立即当编辑,被很低的月薪吓跑了(笑)。我也没上班,自由职业,做小说翻译。时间是有的,但没有像现在这么自律,那个时候也没有规定自己每天写多少字。 《甲马》的第一稿收到了《收获》杂志的编辑鼓励,我就开始改稿,虽然最后没能在杂志上发表出来。后来我放下写了两稿的《甲马》,写了《月光花》,是个有科幻色彩的故事。
三明治:所以最先出版的是长篇《月光花》,然后是短篇集《人字旁》,最后隔了若干年完成的《甲马》又是一个长篇。你是怎么安排自己写短篇还是写长篇的节奏?
默音:短篇比较随机,有想法了就写一篇。长篇需要准备工作,材料上的,精神上的。《甲马》之所以一开始没能成功,还是因为准备不足。第三稿记得是2015年开始写的。中间隔了很长的时间我没有去动它。
我觉得我真正学会写小说,或者说对小说有些感觉,是当我写了一个关于女同志“形婚”的小说,叫《逗号,句号》。我对《鲤》之外的纯文学杂志没什么概念,在网上看到《上海文学》一位编辑崔欣的邮箱,就给她投过去了。没有想到她隔了三天就给我回信了,说这个小说不错,要留用。我完全不知道她是怎样的一个编辑,后来接触慢慢多了,发现她很严格,她经常会给一些非常具体的意见,和我讨论小说里的人物、细节如何处理。遇到好的编辑对作者来说就像邂逅好老师一样,真的能让你成长。
三明治:《月光花》出版后,作为一个刚出了一本新书的作者,心情如何?
默音:那会儿觉得能出书就很不容易了。其实即便现在,出书也还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不过其实在《甲马》之前,我的每本书的销量都非常惨淡,我也接受了这个惨淡的事实。
三明治:新人小说家的第一本书的首印能有多少册?
默音:好像是6000册。不过没有卖完。
三明治:刚开始出第一、二本的书的时候,是抱着怎样的心态继续写的呢?
默音:《月光花》《人字旁》刚出版的时候,我是满意的,现在回头来看是不满意的。
写作总有个成长的过程。到了《姨婆的春夏秋冬》,这个作品我现在重看依然觉得满意。这本书明年会在中信重新出版,我也从头到尾改了一遍。《姨婆的春夏秋冬》写了蛮长时间。自由职业三年后,我去了文景,真的像最初想的那样成了编辑。上班后没有很多的时间写作。那时候处于一种,我现在看来,其实是很黑暗的一个写作过程,就是自己闷在那里写。后来《小说界》的谢锦看了,说挺好的,他们可以刊发一部分。因为全文比较长,有12万字,他们没有体量来刊登一个长篇,但是因为这个长篇是四个中篇组成,可以从中间选两篇刊一下,她还说,我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书。
上班后没有很多的时间写作。那时候处于一种,我现在看来,其实是很黑暗的一个写作过程,就是自己闷在那里写。
三明治·创作者访谈
三明治:写《姨婆的春夏秋冬》这本书的过程是你经历过的比较黑暗的一段时期,没有什么信心?
默音:对,没有什么信心,然后那个书出了也没有什么反响。现在回望,我自己觉得《姨婆的春夏秋冬》是我写作的一个节点。那个故事是我第一次试图处理对自己来说是陌生的时空,而且不是科幻小说里的架空时空,因为它写到了1940年代的上海。那个是真的看了很多资料来写的。也是因为如此,后来写《甲马》,写到西南联大相关的内容,我觉得还比较容易。
三明治:所以对你来说,你的“作家身份”觉醒或认同自己是作家的身份也是从完成《姨婆的春夏秋冬》开始?
默音:没有作家的身份,只有写作者身份。
从写《月光花》开始,我就觉得自己是很喜欢写小说的,因为写小说带来的不是物质上的回报,而是精神上的一种完成感。而且我本质上是很喜欢写长篇的。因为中短篇伴随作者的时间是有限的,可能一个月到几个月就完成了。而长篇创作必须耗费非常长的时间,你必须整个人投入在其中。写长篇对我个人而言能获得一种非常巨大的喜悦,所以我还是会愿意继续下去。而且我也是一个长篇读者,喜欢看很长的小说的,例如约翰·欧文的书。
长篇创作必须耗费非常长的时间,你必须整个人投入在其中。写长篇对我个人而言能获得一种非常巨大的喜悦。
三明治·创作者访谈
三明治:现在你会怎么去安排你自己未来的写作计划?
默音:这一次写完,我觉得蛮内耗的,可能短时间内不会写长篇了。从《甲马》交稿到出书中间,我一直在玩,什么也没写,然后《甲马》出来了,我有一种“不行,我得写点什么”的感觉,于是开始写之前悬置的《星在深渊中》。现在这本书完成了,我确实觉得需要再多读点书,多看一些地方,然后再来想之后如果再写长篇,方向是什么。现阶段可能写中短篇比较多一些。
而且我最近也在做一些翻译的工作。因为自由职业者不可能就指望着稿费。翻译相对是一个有保障的事业,你能知道这个事情做完了是有钱进来的。
三明治: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写作习惯?
默音:只要有电脑就能写,对环境没什么要求。说到工具,我在最近半年意识到了 iPad Pro 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我现在改稿都是用 iPad Pro 手改,这跟你对着电脑打字修改还是不一样的。用手改非常人性化。做编辑的时候会把稿子打印出来看,但是自己在家没有这个条件,不可能每次打印个几百页出来。
三明治:你会保留你的修改痕迹吗?
默音:iPad Pro 是在PDF的格式里修改,很直观,当作品以印刷体呈现出来,还是会发现好多以前没发现的东西。只要有可能,刊物发表之前,我都会请编辑再给我改一遍校样。
三明治:你在这方面是会有点强迫症吗?
默音:可能是做编辑的强迫症。总归觉得最后改一遍,还是更放心。
三明治:今年受到疫情影响,你的生活里还有什么其他改变或不同吗?
默音:疫情刚刚起来的时候,当然是很难过的。那个时候我在家里面,也写不了什么小说,每天一直在看新闻,但也不能长时间盯着新闻看。为了排遣注意力,那段时间我还看了很多网文,比如《诡秘之主》。
其实按照原定的计划,我今年应该是一半在东京,一半在上海。本来想学金缮,后来发现那个班太热门了,我报不上。还有一些地方想去看,现在也都无法成行,只能自己在家工作。
三明治:为什么想学金缮?
默音:我们家的器皿特别多,然后也有坏掉的,就要去找师傅帮忙修补。但现在做一个金缮还是蛮贵的,所以我想自己学一下,并不是想要做手艺人,只是想着家里有什么坏了,可以自己补一补。
三明治:当创作有压力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来缓解压力?
默音:你说的压力是指什么,写不出来吗?我的方法特别简单,写不出来就硬写,然后这一稿不行,就写下一稿。反正总能改出来的。
三明治:你怎么看待现在华语文学市场里出现的一些实验性强烈的文学作品?
默音:目前还是在用比较传统的叙事来写,我也没有想过用新的文体创作。我觉得可以有各种写法。张天翼有一篇小说,全是票据,也很有意思。它的小说是没有正文的,就是用票据勾勒出一段人生。
三明治:坚持你认为的比较传统的叙事的话,其中有没有什么你在坚守的标准?
默音:没有所谓的标准。其实对我来说,一篇小说写出来了,是独立于作者自己存在的,接下来读者跟它的关系是读者自己生成的。你不能代替读者去读,每个人读到这个小说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对我来说,我对文字的未来是比较悲观的。前段时间我写了一篇科幻小说,假设未来大家都以一种“视梦”的方式来体会别人的人生。这种方式不是电视,也不是小说,它是通过直接刺激脑神经达到的虚构。我们现在还依赖文字,到了未来,人类很可能不依赖文字了。
图片提供 | 默音、译林出版社
三明治创作者访谈系列
点击标题阅读对应访谈
的
……
关注三明治(china30s),可以阅读更多创作者访谈。你也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你还想看到哪位创作者接受采访。

12月短故事学院12.17开课
正在报名中把生活变成写作,把写作变成生活
三明治是一个鼓励你把生活写下来的平台
原标题:《默音:作为小说家,我对文字的未来是悲观的 | 三明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