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姜宇辉:假若媒介永生—— “生态电影”与“以物观物”
原创 idf2020 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


IDF学术(IDForum)是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的学术版块,旨在以宽阔的视野、深度的思考,整合与更新纪录片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以此来伴随和支持纪录片创作中的艺术探索与社会实践。本届论坛学术主题为“后真相时代的影像真实”( Reality of Image in the Post-Truth Era),由学术讲座、学者论坛和作者论坛三部分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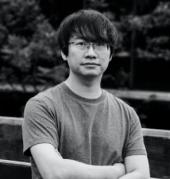
姜宇辉讲座及对谈互动视频
主持人(周佳鹂):在座的各位嘉宾,美院的同学老师,以及校外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此次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学术论坛。我们IDForum学术论坛试图用比较宽阔的视野,深度的思考去整合于更新影像理论,甚至更广义上人文学科领域里的研究成果,用新的成果来伴随于支持纪录片创作中的艺术探索和社会实践。我们期待此次论坛能够建立一种平等、自在、深远而敏锐、细微而辽阔的学术氛围。在此次讲座活动开始之前,请允许我邀请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前三届的执行长,也是中国美术学院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的副院长刘智海教授,让他跟我们聊聊对这次论坛的一些想法。


中国美术学院影视与动画学院副院长刘智海
主持人(周佳鹂):接下来进入今天讲座的部分,今天讲座的嘉宾是姜宇辉老师。姜宇辉老师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博导。姜老师主要研究方向是法国哲学和艺术哲学,他翻译了法学哲学家德勒兹最著名的学术著作《千高原》,他自己有非常多的学术专著出版。这几年姜老师学术的关注点更多转向后人类主义与影像研究。我当年在华师大读书常去蹭姜老师的课,经常占不到座位,因为他可以把特别复杂的哲学问题举重若轻地阐释清楚,同时姜老师一直关注声音、影像、当代艺术等新的艺术媒介,他对艺术持续的关注与研究,跟我们美院整个气质是非常相通,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姜老师。

学术主持人周佳鹂副教授
假若媒介永生—— “生态电影(Ecocinema)”与“以物观物”
姜宇辉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
这篇文章虽然是我去年发表在《艺术理论研究》,但我自己很喜欢这篇文章,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标志我研究的一个转向。之前有一段时间我是比较偏向思辨实在论,今年我特别想转向另外一个方向,开始研究体验、创伤、苦痛等。这可能也跟疫情有很大关系,因为疫情在家里待了半年的时间,也受到了很多苦痛,所以也让我自己好好想想哲学面对这样的时代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回应,是不是像思辨实在论那样用抽象冷冰冰的思考就能够代表我们在这个时代活过,我觉得这是不够的。所以这篇文章我觉得能够作为这两种研究范式的交界点,从思辨实在论对物的反思回到对主体性——对人自身的体验、苦痛、伤痛的反省。大家看这个标题,我实际上是借鉴我之前看过一部美国电影《假若明天来临》,但我想放在这里很好,这涉及到媒介跟生命之间的关系,我觉得特别有值得反思的意味在里面。

实际上我这篇文章的副标题是研究生态电影。我在这里对实验电影、生态电影、纪录片进行稍微一点题外话的反思,而且我尤其想从哲学的角度去探索在什么样的意义上有一种Ecocinema生态,或者生态跟电影之间有什么样的连接。今天大家不管是去看屏幕上的大片,还是实验的小的短片,其实生态是很重要很关键的问题。我们已经不仅仅陷入到环境危机而甚至到环境崩溃的边缘,因此特别能够从影像角度对这些东西进行一些反思。
首先我们从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开始,我想追问一下,从人生这个角度出发,我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可能大家都想过,人生生命的最终意义,最终的归宿是什么?在座所有同学,在人生某个阶段、某个时刻可能都想过,但如果把这个问题正式提出来,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区分两个不同的视角,第一个从每个人,从个体的角度出发。大家有不同的人格,不同的追求,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从每个人的个体角度看生命的意义非常不一样。从个体角度来说,每个人有自己选择自己生命权利的方式,可以追求快乐、幸福,甚至追求孤独,离群索居,追求各种各样不同的意义,不同的目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视角放得更大,从个体扩展到整个人类作为一个种群,作为生命的整体,当完美去考虑这样一个宏观尺度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想过整个人类生存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单纯说快乐、幸福、满足、成就这些就不够了。把人类放在更大的生命整体来说,完美可以回答这样两个要点。第一,作为一个种群,作为一个存在的整体,它在地球上最终的方式就是要活下去,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包括环境的危机,各种其他生命的挑战)在地球上延续下去,这是人类作为种群的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我想更高一点就并不仅仅单纯活下去,而且想让自己的生命不断延续下去,甚至突破生命的极限。以前可能只活几十年,医疗发达的时候活80岁、100岁甚至更长,但我们看在人类历史上,各种各样的历史的阶段,发现人类都有更终极的东西——就追求永生、不朽。所以从这个角度发现,“永生”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整个人类生命种群非常终极的追求,所以把永生这个问题提出来是有所用意的。

我们说人体冷冻不仅仅是科幻小说的情节,今天在美国有很多实验室做这方面的工作,要花很多钱把人体冻得非常好,因为里面不能出各种各样的故障,稍微有点参数的变化可能冷冻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大家都看过一部电影《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冻着冻着突然醒过来了,这就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大家看到了对永恒或者不朽的追求,是人类自古以来一直到今天甚至一直到未来,伴随人类生命历史所有的阶段,永生都是终极的追求。我们想在这里问一个很根本的哲学问题,或者说技术的问题,在今天人类是否真的能够实现永生,不是通过木乃伊,不是通过冷冻人体,而是通过一种更为科技、更为技术化的方式实现永生,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有没有可能做到?我想很多学者,包括很多的艺术家,已经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比如说这篇小说《奇点遗民》大家都很熟悉,这是非常有名的华裔科幻小说家刘宇昆的作品。他有一篇小说我很喜欢,直接探讨了在数码时代,在后人类时代,如何实现不朽的问题,而且他最终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们之所以要发展数码技术,就是为了更好地、更彻底地、更完善地实现人类生命的不朽。我们发现在以前,人类以前追求不朽的方式都是跟身体去较劲,比如把身体掏空,用各种各样的香料填满,或者把身体冷冻起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让生命能够延续下去。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永生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极端的方式,不是在身体的层次,而是转换到意识、精神层次,把它转变为信息和数据,而数据和信息可以更完美地实现不朽。但是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转化到服务器,转化为数据和信息的时候,是否可以更完美实现我们人类一直以来终极的追求——不朽、永生、不死。这就是刘宇昆在他的小说《奇点元年》里面所设想的一个场景。“奇点”大家都知道,最早是库兹韦尔提出来的,(他是)一个美国IT技术大师、未来学家。奇点就标志着这样一个时刻,大家看这个引文:“第一个人被上载到机器的那年。”就是人类把自己数字化。抛弃你的身体,抛弃你生命的、物理的、生物的身体,把你所有存在的状态和信息,都转变成数码上传到一个庞大的服务器或计算机。如果是这样,我们发现不朽的问题就非常完美地可以去解决了。当我们的生命转化为数码和信息时,就没有生命这个短暂的时间间隔了,我们可以无穷无尽存在下去,在数码的天国里,在服务器的天堂里,我们就是一串101010……。刘宇昆这样设想,他公司也很有名,这个数码公司就叫做永生公司。奇点元年的到来,它要实现的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实现人类历史上最根本的追求,就是我们所有的人从历史一开始的地方就渴望的——长生不老。所以当我们有了数码技术之后,就可以实现永生这样一个终极的理想,我们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但刘宇昆在这部作品里面,最后给出的结果是很悲观的。
不知道在座的同学有什么想法,这篇小说写作(年代)很久,大概在20多年前,当时大家根本没有想到还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想数码技术。刘宇昆作为科幻小说预言家,他在非常早的时候就已经看到数码技术给我们带来的灾难性的影响。这篇小说最后两个主人公,一男一女,必须面临生和死的选择,你是选择把自己上传到服务器,抛弃肉体,还是选在留在地球上负隅顽抗。你留在地球上就变成遗民,所以这篇小说叫做《奇点遗民》,就是遗留在地球上的最后一批生命,你注定要被之后所有的信息技术淘汰,所以你只是托着自己残破的身体等待着有一天那个信息技术来收编你,剿灭你可怜的躯壳。所以主人公的孩子甚至包括他的老婆都已经上传了服务器,他们通过这些服务器、通过这些屏幕,通过数据交流,但这两人还是觉得他们留恋地球的生命,留恋人类历史,他们甚至走遍地球各个地方去看古书文,翻那些尘封的古迹,想找回人类生命里的痕迹。这是很悲哀和无奈的事情,当你想用人类历史对抗未来时,就说明其实你对未来已经无力抵抗了,你仅仅是进行缅想,根本没有办法抵抗历史的潮流,所以最后这两人紧贴在一起开枪自杀。最后一句话是非常具有隐喻意义的:“我们一起欣赏这个纯净的世界,这个没有被数码技术沾污的世界,这座从活死人那里继承的花园。”什么叫做活死人?就是未来再过30年、50年的孩子就是活死人,为什么?他生下来就是在数码技术里,他从大脑到机体都被数据化和技术化,所以最后一批奇点遗民还想用这样的方式拥有世界上所有的时间,但是又能拥有多久呢?是一分钟是一秒钟还是一小时?但注定你的未来是不属于你的,你只是死命去抓住脱离你而去的这样一个未来而已。所以最后一句话非常有讽刺性:“世界上一切时间都属于我们了。”但这个时间到底有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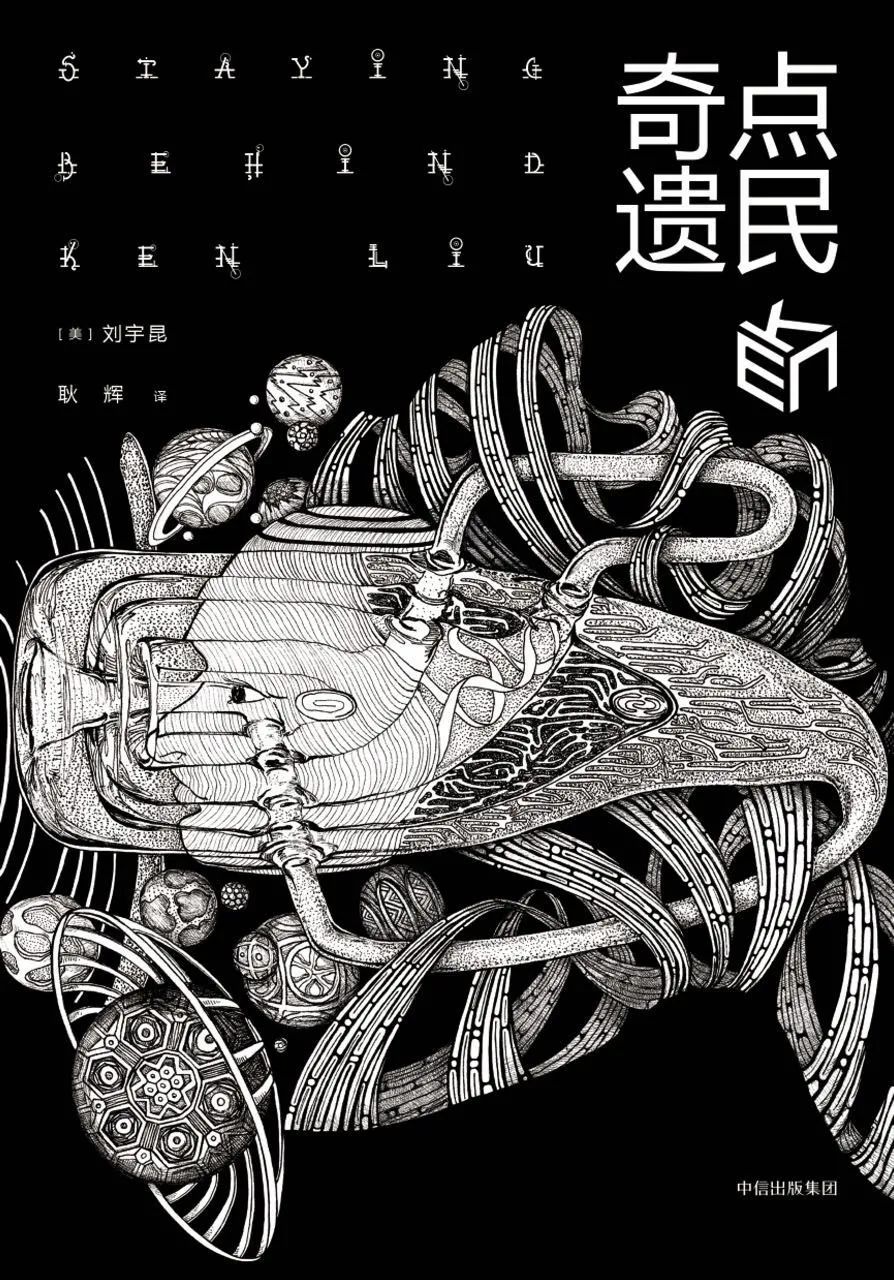
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些反过来的思索,刘宇昆他作为一个小说家,他非常有理由去表达自己对科学技术的悲哀,因为文学家、艺术家可以表达自己不同的立场。但像研究技术的专家会觉得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可怕,这样一个数字化的未来,这样一个奇点来临的未来,其实我们应该去拥抱它,因为这是人类进化的下一阶段,为什么不呢?大家都知道人类是从单细胞生物,从海洋里面一点点进化过来的,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经历了多少次形态、智力的变化。所以像库兹韦尔写《奇点临近》,他就觉得奇点来了就来了,挺好的一件事为什么要怕它?我们只是变为另外一种形态去活下去,以前我们通过肉体去活,接下来我们通过数据去活,我们作为数据而活下去又有什么不好呢?等我们进入下一个进化阶段,就像我们之前从哺乳动物进化到直立行走,进化到使用工具,进化到智人这样的阶段,就是这样一点点过来的。那也许下一阶段就是人类开始变成数据,有什么可怕呢。所以大家仔细看看库兹韦尔的这本书《奇点临近》,他在这里面充满着非常乐观的情绪,他说我们应该拥抱这样一种技术的未来,这个未来仍然还是属于我们人类的。不管它看起来发展的速度有多快,因为Singularity在科技史上标志这样一个阶段,就是人类的技术发展到达这样一个奇点之后,不再是平稳的按照线性方式发展,而是有一个指数性地突破。大家看库兹韦尔这本书里有几个图,到了奇点的时候它的线是直线往上走的,它有非常陡的向上的飞跃。所以当他用这个方式预示整个人类技术发展的时候,他是告诉我们未来没有什么可怕的。
但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出三个问题:奇点到底是延续还是断裂?到底是新生还是覆灭?到底是肯定还是否定?奇点之后的人类,是人类生命进一步的进化,还是它跟我们人类已经没有关系了,它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存在形态?我们说人类从单细胞进化到现在的智人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但从恐龙到人类呢?有没有想过,它是不同的,恐龙灭绝了才出现人类。那我们到了奇点,可能那个生命形态就像人类回过去看恐龙一样,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是一个断裂。为什么像库兹韦尔这些人这么乐观的一定相信,这个未来还是我们人类生命的进一步的留存?为什么你会觉得奇点的未来跟我们今天是延续的,我们可以拉一条连续的进化线,而不是当中有一个深渊横亘在那里?当人类踩到奇点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跳向一个山峰而相反是跌入一个无底的深渊,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大家对库兹韦尔都有一个非常深刻地质疑,就是他对这个未来太过有一种乐观的立场了。我在这里更愿意用浮士德作品的方式来比拟这样一个未来,其实我们跟机器之间有一种“浮士德”式的赌注,确实机器可以赐予我们永生,这没有问题,因为贯穿整个人类历史找不到更好的永生方式,无论是木乃伊还是冷冻人体都不能像数据这样去实现无穷无尽生命的延续形态。但是当我们在机器的天国里,在数码的王国里实现了永生之后,我们丧失的是什么?我们丧失的是人之为人,我们把所有人类的本质,人的生命、人的情感、人的意志、人的历史,人的文化……所有人的东西都放弃和否定掉了,然后变成数据,这难道不是“浮士德”式的赌注吗?这个赌注人类承担得起吗?有多少人投票觉得这个未来是我们可以去接受的,还是这个未来就是掌控在那些IT专家手里,他们有没有听取过“遗民”的意见?这是很关键的问题。
很多技术专家都抱着这样一个立场,像英国IT专家Nick Bostrom写过一本书《超级智能》(《Superintelligence》),例如强AI这些东西都在这个脉络里。他说其实未来一点都不可怕,虽然技术的发展是超线性的,是指数性的,但我们还可以采取各种各样防御的方式。他设想我们人类在今天,可以对这个不可抗拒的未来采取各种各样的防御方式,比如说沙盒等限制AI进一步地发展。他进一步提醒我们,这样一个奇点未来可以用人工的方式、技术的方式去进行挽回和弥补。但我们接下来去想的是,可能这个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当Bostrom设想各种各样防御方式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我们身边已经有一种力量——就是数码媒介的力量,它已经可以一步步的把人类生命带向不可逆的永生阶段,而且这个趋势我们看起来已经是不可逆转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自己做声音艺术的,我也用黑胶做过很多实验,包括搓盘(Scratch)等,后来我们觉得这个实在太伤盘了,还不如用CD,甚至现在CD都不用了,我们可以在电脑上做各种各样的效果,例如划痕、跳针等。当我们今天去看数码知识或者媒介知识进化的时候,会发现媒介本身就是向着“永生“这样的趋势不断去发展的。
比如我们就说这三个在音乐里非常典型的媒介格式、第一是黑胶、第二是CD、第三是MP3,你看一下。当我们从黑胶到CD再到MP3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实体、肉体那些物质的东西越来越淡化,越来越消除,越来越趋向于无形、无象、无色、无嗅、无触、无感的那些,甚至无实体的数码格式。比如说大家在听黑胶的时候,我以前做声音收了很多黑胶的盘,我们当时为什么那么迷恋黑胶?是因为黑胶它是有磨损的,你每放一次它上面会留下痕迹,它的生命在消耗,它在死去。黑胶放几十次之后它的声音就变质了,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杂音,甚至再放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受潮变弯,你会觉得它是有“肉体“的,是活生生的,你摸上去它是存在的一个东西。但到CD就已经不一样了,CD你把它推到光驱里面,你不知道在里面发生了什么,你只听到它在转,然后你拿出来之后发现它是一个透明的东西,介质在哪里?所有的那些数据都是装在透明的盒子里,它已经开始慢慢隐形了。但是到了MP3时代,这个制式完全彻底变成无形了,你说MP3单独的一首曲子的实体在哪里?它的“肉体”在哪里?它可以在各个机器上播放,在电脑、手机、车上去放,但作为一个数据,到底它的形体、实体是什么?除了无限在一个弥漫、虚拟的网络空间里去传播去复制之外,它还是什么?它跟黑胶、跟CD到底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所以人们发现到MP3时代之后就已经非常相似《黑客帝国》开篇的场景了,我们所有“肉体”与实体的东西都在消亡,被取代、被瓦解、被转换,所有的一切存在方式已经以数码流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是《黑客帝国》开篇非常有名的一个场景。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各种各样的数据、各种各样的文字,各种各样的代码,在没有方向的空间里去流动下来,弥漫地流动、穿透地流动,渗透地流动。在我们今天,其实还是可以做一些比如复古的手法,我们今天可以用电脑在数码方式拍出的照片上做出比如说LOMO相机这样的效果,甚至我们可以在程序所写出来的电子音乐里面加上各种各样黑胶的效果,跳针的效果、划痕的效果,各种各样背景的噪音。但这些东西都是假的,都是在数码的平台上做出来的效果,这不是真实的“肉体”,这是用数据化所虚构出来的“肉体”,但这不是真的,就像我们也可以在游戏里面,在数码的天国里面,为你虚构出来数码的“肉体”,让你觉得你在呼吸,让你觉得你有欲望。但这些东西跟前数码时代“肉体”存在的方式,是否有相似的地方,还是它们之间就是一种彻底的断裂?就像这里两张照片的对比,左边是一个数码相机所拍的,后边你只要加一个滤镜,就能够形成一种时间流逝复古的感觉,但也仅仅是一种感觉,仅仅是一种特效,时间并没有真正地流逝,只是加了一层数据处理的效果而已,就像你的生命在数据天国里没有真正的流逝,仅仅是所制造出来的一种幻觉而已。

我搜集了大量英美学者以及法国学者的资料,发现其实媒介在今天这样不朽的地位是不是有些被夸大。因为很多学者,像美国的SENA CUBITT,他写了一本书的标题叫做《FINITE MEDIA》,认为媒介是有限的,是可朽的,是有生命的,是有生有死的。但我们今天去谈数据谈数码时,是不是太过了,太过于强调无形、永生的趋势,是不是我们今天都忘记了,媒介还有一个可朽的、有生命的、实体的、物质的一个方面。我提醒大家如果研究媒介问题的话,像CUBITT这些老师,这些学者,其实是起到一个纠偏的作用,他给我们一个提醒,媒介自身仍然还是可以从有形、有生命的角度去考虑。
CUBITT在(这本书)封面上给出的照片很明显,我们今天认为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数据,都是屏幕上呈现出来的,好像是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仅仅是一串数字,但其实在电脑后面有CPU、芯片等各种各样的东西,它也是有耗损的,也是有生命的。甚至在今天各种各样的电脑垃圾(像手机的更新换代),你真的看到过的话,其实电子媒体所遗留下来的尸体可能比以往如恐龙所留下的化石更为让人触目惊心。我从这个角度提醒大家思索媒介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方式,数据的背后有机器的实体,像今天苹果电脑的设计,无论怎么光滑,怎么隐形,怎么极简,但它仍然有一个物质的实体,你还是需要去触键的,你还是要摸到这个机器的质感的。所以你看到的所有数据都呈现在无形的屏幕上,但你操作所有的机器其实都是有触感的、有存在的。特斯拉的车可能跟传统车不一样,它所有的操控变成一个界面,好像取代以前摇杆等实体的东西,但它操控仍然是一个实实在在在跑的一个实物的车,还是有电线,有发动机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今天对数码电影或数码知识的反思是充满误解的,我们太过从永生的角度、无形的角度去考虑了,我们忘记了其实我们还可以从媒介或者物质实体的角度重新想想数码电影发展运动的趋势。
这是美国另外一个学者Nadia Bozak,他写过一本书《电影的足迹》(《THE CINEMATIC FOOTPRINT》),我觉得这个标题很棒,告诉你电影不是无形的,电影并不是单纯的数据,相反当你拍一部电影的时候你就是实实在在在这个大地上留下各种各样的痕迹,无论留下的是好的痕迹积极的痕迹,还是各种各样工业的垃圾或者人为的废料。他书的副标题——Lights,Camera,Natural Resources,就是要把自然的光跟电影本身的媒介这个制式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非常具有讽刺意味,像《THE DAY AFTER TOMORROW》(《后天》),这是一部反思人类的环保所带来毁灭性结果的电影,本身它是一部关于环保的电影,导演拍这部电影就是为了警示大家,再不保护环境人类的环境就延续不了多久了。但你知道拍这部电影花了多少钱吗?你知道他拍这部电影排出了多少废料吗?你知道他拍这样一部“环保”的电影给环境造成了多大的破坏和影响吗?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Bozak给出了这样一个数据(229000美金来抵消《后天》所排放出的10000吨二氧化碳)。
还有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黑客帝国》,他拍的是虚拟的电脑场景,拍的是网络空间。网络空间是什么?是无形的,无实体的,我们在网络空间里甚至可以不需要肉体。但大家知道拍一个虚拟的网络空间,需要消耗多少实体的材料和资源吗?搭一个虚拟网络空间的场景需要花费90吨的物损资料,这不是最大的讽刺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悖论到底在哪里。后来一大批研究Ecocinema的学者、导演都提出了疑点,你别说今天媒介是永生的,今天我们拍数码电影,以及拍一些数码制式的影像作品时,其实对环境的破坏和影响,比胶片时代的电影大得多。所以像CUBITT用三个词:过剩的存储,冗余的系统,过量的供电,这三个词里面都加了“过度”(over-)。我们今天拍电影不是说电影进入数码时代之后,我们就不消耗自然资源,我们变成环保了,我们可以用无形的格式去取代以前对环境的消耗和破坏,恰恰相反我们越是拍数码电影我们对环境的破坏越是过度,甚至超过以往所有电影的时代,超过梅里爱的时代,超过卢米埃尔的时代,超过戈达尔的时代,超过安东尼奥尼的时代。大家可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你看一些成本的制作,看一下它背后的预算报告你就知道,所以CUBITT就写“过剩的存储、冗余的系统、过量的供电”,这都是今天的电影,对环境破坏是非常大的,“环境罪”“生态罪”。从这个角度来说,媒介不仅仅是不朽的,相反在电影数据的背后对环境有种巨大的依赖、破坏和影响,这是值得进一步反思的。

我们先看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媒介作为框架,什么意思?我们一般人对媒介的理解是这样的,媒介像一个窗户或窗口,它是隔在我们跟世界之间的,我们通过这个框架看到世界,比如我们通过镜头看到世界,通过收音机听到世界,我们通过各种各样触觉的东西摸到这个世界等等,所以媒介一开始隔在我们和世界之间起到中介的作用。但沿着这个思路想下去,媒介并不仅仅是窗口,当我们把这个窗口无限延伸时,发现所有东西都被吸到窗口里面,被它左右,被它同化,被它操控。其实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媒介这个窗口之外的世界,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媒介本身它给我们描述出来的形态。这是玛格丽特的两幅画,左边这个画很有意思好像一个窗口在拉开,上面是外面的风景,打破之后发现所有东西都是媒介本身提供给你的。你以为媒介是一个框架可以打开外面更广阔的世界,其实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被限在媒介这个陷阱里面,就像海德格尔他写的《世界图像时代》,我们是在媒介这个框架里面的。

当我们可以用“连接”的方式拓展媒介时,会发现原来单一的媒介能量形态可以转化,如当我们石油这个能量形态用得差不多时可以用电力,电力不行可以用光能、水能、风能等所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转化、弥补我们现在在能量这个角度上造成的缺失。我觉得当我们思索媒介的聚合形态时,这个问题会变得更为微妙更为复杂,好像聚合起来的媒介真的又能够实现不朽的形态了。它可以用连接的方式、用转化的方式、用拓展的方式,它可以自我修复,因为它是一个网络,单一能量形态被消耗后可以用其他能量形态来弥补,所以它怎么可能死亡呢?之前我德领馆做过一个讲座,和一位艺术家对谈,当时德国领事问过我:“你是否对人工智能有太过乐观的想法,我们今天不可能造出那么庞大的计算机,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怎么可能造出计算整个宇宙的计算机呢?不可能的。”我当时想到一个回答,非常明确,如果它真是人工智能,它就可以开动自己的技术去运用所有宇宙中可以用的资源,不一定是地球上的,甚至哪怕是地球上的资源它也可以用自己转化的方式去运用,因为它是人工智能,他可以发明重新再生的网络或者重新再生资源的方式,是人类根本想象不到的。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可能媒介不朽的问题又要放在台面上,跟CUBITT这些学者唱唱“反戏”,那些学者强调数码媒介背后是有实体的,消耗的是自然资源,破坏的是整个环境。但当我们进入媒介第三个形态——“聚合”的时候,发现其实未必如此,它是在消耗资源,但是它可以用更为强大的力量去弥补自己的破坏,因为它是连接的,它有无穷的力量可以把整个宇宙变成它网络中各种各样的部分。所以这是我接下来去想生态电影,包括看了一些片子结合一些研究后,所进一步思索的问题。
我们从生态“意识”和生态电影的角度最后谈一谈这个问题。第一点,大家可以看这个表格。我们看这个表格,左边是媒介,右边是人类。我们前面都在讲媒介的问题,你会觉得这跟人类有什么关系,媒介的生和死跟人类有什么关系,哪怕是黑胶变成CD变成MP3,它只是格式不停在演变而已,我们人类的生活还在延续,该怎样还是怎样。但我觉得大家可以重新想想,把媒介的演化和人类的演化结合在一起,你会看到这两条脉络之间是非常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媒介每一次作用的变化都面对着人类面对世界根本态度的变化,旁边三个是媒介:框架、流动、聚合。框架是什么?框架实际上就是人类中心主义。这个框架,这个媒介是我们人类看到世界的窗户,我们人类造出来的框架。概念、语言都是框架,甚至声音、影像都是框架,我们人类造出来的,为了更好看到外面的世界,是为人类服务的,表达的是人类的诉求、欲望、意志。当我们把媒介变成框架时,肯定是指向人类中心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当我们把媒介理解为流动的时候,能量流动的时候是非常不一样的,如果是能量流动就没有人类跟外界,内和外,人和物,主体和客体,没有这些区别,因为能量是自由流动的,它可以突破和跨越各种各样的边界,是cross的。第二个媒介形态对应的是人类纪(Anthroprcene),简单而言,就是把人类的生命放在更大的生命网络里。人类的生命并不是生命的顶端,也不是生命的典型形式,只是生命的一种。人类生命的延续必须跟其他各种各样的生命形式重新连接在一起。这就是美国著名的学者唐娜·哈拉维说的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她用了一个词叫“克苏鲁纪”(Chthulucene)。什么叫做“克苏鲁”?就是那个庞然大物,有很多触角的章鱼,未来的生命形态就是这样,各种各样的生命形式拼在一起,构造像怪物一样的形态。所以当我们从流动角度去考察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抱着人类纪的立场,我们突破人类视角的中心,人类生命的中心,放在更大能量生命的网络里,把人类作为一个结点,作为一个部分存在的方式。
但是当我们进入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进一步突破前面的两种,前面两种其他老师和学者谈了很多,第三种是我自己稍微有一些体会。大家可以仔细想想,当媒介聚合起来之后,我们非常需要有一种力量能够从聚合网络里跳出去,重新找到一个外部,当所有一切都连在一起后,我们要找到一个不能够被媒介化,媒介之外的一种存在方式。那是不是就是“物”(object)呢?就是物本身,它不能够媒介化。因为媒介化是跟人发生关系,进入到人类生命形态里,进入到人类社会形态里,但如果有纯粹的物,冰冷的物,它抗拒着人类,抵制着人类呢?是不是就可以找到一种方式,从聚合的、不可逆的、不朽的命运里跳出来,有另外一种可能性。这是我一两年前写这篇文章时候的解决方式,但我今天已经不抱这样一个立场了,所以我只是在这里列一下这个可能。
怎么样从物这个角度,从媒介的聚合里跳出来?首先区分两个很关键的词,一个叫做Environmentalist Films,我把它译成“环保电影”,我觉得这是有贬义的,这并不是真正面对环境的一种电影的形式,这是非常商业化的,非常主流的,非常景观的,非常很炒作的,跟环境和环保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应该区分“环保电影”跟“生态电影”(Ecocinema),这两者是非常不一样的,无论从制作的手法,还是创作的理念,还是背后对待媒介的基本态度,对待世界的态度(都是不一样的)。环保电影不用多说,因为市面上研究的很多,大家能看到的资料也很多,但大家看多了之后也会觉得这些电影的优点和缺陷很明显,优点就是很好看和卖座,在院线IMAX屏幕上看到冰川崩裂、火海或水灾……那些大的场景,视觉特效上很震撼。但如果从电影,尤其是从环保(Eco)这个角度来说这些电影一点都不环保的。首先成本很高,其次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因为这些电影拍出来就是为了去迎合人类的口味,迎合人类的需要,迎合人类的想象,对未来的担忧,对末日的恐惧。它的主流市场是大众口味,环保电影是一个框架,即我们说的媒介的第一个形态,就是这样一个有色的窗户和眼镜,它让你看到的不是外部真实的情况,不是物本身到底是什么。你是看不清的,你只能看到屏幕上呈现出来的各种各样惊心动魄的景观,那些工业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影像的景观、灾难的景观、世界末日的景观。大家想想近十年或近二十年看过的大屏幕上的灾难片,远远不只这些,以火灾、水灾、冰灾,小行星撞击,机器人暴动等无数种方式,地球已经毁灭过了。但你还是一次次走进大屏幕看,每次都很爽,因为有特效。每次特效都在升级,声音在升级,影像在升级,屏幕在变大,原来是2D现在是3D甚至8D。这些真的把我们拉近外面的环境、拉近世界了吗?好像并没有。它仅仅是让我们更为麻醉地沉浸在框架里,这个媒介给我们虚构出来的形态里,磨灭了我们反思和行动的可能性。
由此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开始兴起了一个比较实验比较独立的流派,这些电影不可能进入院线,不可能进入大屏幕,成本很低,也可能取得票房的收获,是完全跟这些东西背道而驰的。在这些电影里,我们看到了它有一种新的“意识”——就是生态(Ecocinema),真正把生态作为电影的追求,作为电影真正关注的要点,我们看到在生态电影里有下面几个特点:
第一,它从“框架”里跳出来,强调电影应该回归媒介作为能量流。哪怕特效做得再逼真,但并没有真正把你的生命、你的存在,放到更大的世界里,它只是让你隔开了这个世界。真正的生态电影应该想尽各种方式,用艺术的手法、实验的手法,让你能够真正回到世界里,让你反省于意识到你自己有肉身的存在,它是更大的生态里的一个部分,而并不仅仅是你坐在电影院里看了一场惊心动魄影像的表演,特效炫目的展示而已,所以生态电影第一个是回归媒介能量流。
第二,它想让我们所有人真正唤醒一种意识、行动的可能性,我们把它叫做生态中心主义,把人类放在一个更大的生态圈里面。我们可以重点谈一部电影,一部很好的片子,也是研究生态电影非常有名的美国学者波拉·维勒盖特-马里孔蒂重点分析过的一部电影,叫做《Riverglass》,拍的就是一条河流。他在这个电影里提出来有两个很重要的手法,能够让我们从媒介的不朽的网络回到物本身、自然本身。他用这样两个词,第一个叫做“间距”(distance),第二个叫做“疏离”(alienation),他想让我们看到我们跟自然之间是有距离的,首先我们要拉开这个距离。让我们意识到在各种各样大屏幕、媒介、信息、网络之外还有一个东西叫做自然,它可以脱离我们的存在而独立存在下去,它有一个力量可以挣脱我们而去,它是独立的。这是之前环保电影犯的最大的错误,它太把世界和环境拉近我们人类,变成了人类消费的产品,变成迎合我们欲望的东西和对象。相反在生态电影里面,我们发现首先我们需要一种离心的力量,把自然分离出去,拉着我们的注意力和我们欣赏的眼光去看到媒介网络之外更大的独立所在的自然的世界。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才可以进一步思索自己跟自然之间的关系,只有把这两个东西先分开,不是缠在一起连在一起变成一个“聚合”,而是先把她们分开然后在这个间距前提之下,你才能更好地看清自然,不是带着媒介这个有色的眼镜,也不是陷在这个媒介的网络之中和能量流里。而是有一种方法让你可以按照自然本身的方式看到自然本身(nature as nature)。有没有这样一种手法,这是生态电影所追求的非常极端的方式。
大家如果做电影或拍电影或研究电影,你会发现这是痴人说梦。因为所有的电影都是人拿着摄像机去拍的,去拍给人看的。真的在人拍的电影里,在人看的电影里,人评论的电影里,能够出现一种“物”的视角,一种自然本身的视角吗?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在你的摄像机和你的屏幕上呈现出自然本身?我看过《Riverglass》后,觉得其实这部电影真的很好,但我并没有觉得真的像马里孔蒂所说是一个“物”的视角。我看到这条河流,好像它就几百年在那里流,跟人类没有关系,可以跳脱人类的媒介网络之外,我并没有看出这点。可能每个人看的感觉体验不一样,在我看来跟早期的诗意纪录片没有什么区别,我根本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客观的物,这是一条河流在人之外流动,这是自然本身,我没有这种感觉,。相反我有非常强烈的感觉,有一个人在河流的对面,所有的镜头都在表达他对河流的那种诗意,那种哀伤,那种忧郁,那种伤感,那种回不去的对家园的眷恋,所有这些东西都打在这个屏幕上面。我根本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河流本身,至少这个作品马里孔蒂分析完之后,我觉得是不足以服人的。虽然这个作品(没能展示),但马里孔蒂提出来这样一个方式,就回到物本身这样一个观看的视角、拍摄的视角,仍然还是很有启示的。所以他在自己文章里用了一个非常哲学化的词,叫做“物导向”(object-oriented)。这个词在近二十年西方哲学里是很有名的,大家知道有一个词叫做“OOO”——物导向的本体论(object-oriented-Ontology)。听完之后你可能觉得这只是种哲学,但你会发现生态电影里贯彻的就是物导向的哲学,就是想通过影像跳出人类的中心,跳出人跟物的关系,达到物本身,这样一个独立存在的物的实在这样一个本体,这是马里孔蒂在他的文章里非常清晰表达出来的。所以他要求我们不带主观视角去观看河流自身(in its terms)、去体验河流自身,而不去考虑它能够给我们提供何种资源,这可能才是一种真正的我觉得生态的视角,这才是真正的生态意识。相反像那些绿色环保组织,环保电影是不是走歪了,他们还是从保护自然资源的角度入手,但当你把自然下降成资源时,还不是把自然当成人的工具和手段吗?有没有想过其实应该把自然当成目的,当成归宿,当成终极呢?什么叫做保护自然资源?难道自然只是资源吗?有没有想过自然应该是家园、是母体、是我们最后要回去的地方,而并不仅仅是我们要拿的西东,好像越拿越少,那些资源如煤、气、水等越拿越少,是这个问题吗?所以真正生态的意识首先应该发生根本性的变革,OOO物导向的本体论,可以起到很好的纠偏或唤醒作用。
由此我想到一个词,虽然是我发明的,但我是从王国维那里引出来的,但非常贴切。你会发现OOO的视角,并不是新鲜的视角,在我们古诗词里就已经有这样的意境,而且非常明显,从很早的古诗词里面就已经有一种“以物观物”的视角了: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有没有想过“无我之境”到底是什么?难道“无我之境”不就是把我的主观视角悬置掉、清除掉、降到最低,让物本身呈现出来,让世界本身呈现出来。在中国古代美学里,难道不是已经表达出来了这样一种非常极端但新鲜的在今天仍然有启示意义的这样一种观物的视角吗?王国维说“有我无境,以我观物”。当你“以我观物”的时候,你把所有的物都打上了自己情感的烙印。比如“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单纯同物的角度来看这没有什么,一点都不伤感,只不过是花瓣落下来而已,只不过秋千在那里荡而已。它是物,凭什么你去看这个物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世界想象成你自己情感的投射?你痛苦这个世界就痛苦吗?你快乐好像所有的花都在对你笑吗?所以这是“以我观物”。中国诗学的终极意境是“以物观物”,回到物的视角,把主观“我”的成分降到最低,去打开“物”的这样一个向度。
我觉得在《Riverglass》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观物的手法,比较重要的,大家可以借鉴的,第一是它放慢的时间,并不仅仅是观看的时间,而且跟你心里的时间也造成错位。一般电影里看到的河流,它在流是有一个自然的节律的,好像跟你的呼吸、心跳、脉搏有一种呼应,当你看到电影里水流湍急的时候会紧张,会有一种呼吸急促感,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比如伯格曼的电影里,水流突然冲过去就发生什么事情。但马里孔蒂这个电影里不一样,是通过放慢时间,让这个时间从人类的感知和生命模式里抽离出去,让你觉得那个时间跟人是没有关系的,是物本身的时间。就像思辨实在论里经常举的例子,两块石头的对话:两块石头坐在那里说,今天你好的,我也好的,过了40年两块石头还在那里继续对话,过了几百万年,这两块石头还在那里,恐龙灭绝、人类灭绝了、地球都灭绝了,这两块石头还在那里。你会发现物的时间和人的时间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有一种深层的时间,它不能够被纳入到人类历史演化的节律里面,像OOO影像他们首先尝试的实验手法,就是放慢,非常非常慢,不是慢镜头的慢,是慢到你根本感觉不出来的,就像Michael Snow的那部《波长》(Wavelength)实验作品,30分钟从前面推到墙上的镜头,但你感受不到镜头在动,很有OOO的特性。你在观看的时候,你觉得不是你自己在观看,慢慢有一种力量把你观看的视角把它磨灭掉,把它吸到物那边去。《波长》最后就是墙上的一幅画,海浪的照片,你会觉得你看到的其实就是海浪本身。这是第一个,放慢的时间。
还有一个,就是无意义的细节,在美术里面经常用到的。每个细节,即使人根本不需要关注或看不到的细节,都描绘出来,早期荷兰静物画里经常会使用。大家看荷兰静物画的时候,英国美术史家诺曼·布列逊把这叫做“注视不可见”,讲十六十七世纪的荷兰静物画。他在《注视被忽视的事物》里面讲,当我们看到荷兰静物画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一种恐惧,会有一种陌生,就好像你在看一个外星世界,但其实画的都是人类非常熟悉的场景,比如餐桌、新鲜的水果、各种各样的高角杯。但为什么你在看荷兰静物画的时候感觉到很恐惧,好像所有东西都反过来在冷冰冰地注视着你,而且那是一个人类根本没有办法进入的空间?这是因为在这些静物画里,采用了一种巨细无疑的,近乎机械扫描的方式,把每一个细节呈现出来,在马里孔蒂的电影里面也有这种方式。
最后总结一下,我认为以马里孔蒂为代表的生态电影有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他并没有达到这个物,无论他用什么手法最终还是回到“观”的角度,包括他那么诗意,那么唯美,那么渗透着自己对这条河的爱恋——这里哪里有“物”?我看不出来“物”的视角。其次,他的影像是很平面的,他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法对影像呈现的方式进行艺术的处理,反而淡化了能量的冲击,淡化了背后物质的背景。第三点,可能我说得不太恰当,我觉得他跟所谓的诗意纪录片没什么区别,这里只有人文情怀并没有物本身,只是人在这个镜头前面,在这条河里面,投射了很多我们自己的感受而已。
大家都知道Ivens早期纪录片,我自己也很喜欢,你看Ivens拍的《雨》,你会觉得他可能想采取一种客观的视角,不掺杂自己主观的态度、情感和立场。但实际上恰恰相反,他每个镜头,包括归家的人带着孩子,三三两两的行人在道路上面,这个伞,花的形状,尤其是这个镜头,你会觉得这是客观的、物质的雨打在地上吗?完全不是!这里面(充满了)梦幻与浪漫的氛围,这是Ivens所独有的标记。所以像马里孔蒂这种生态电影大家觉得还不够极端,还不够生态,所以后来出现Bozak这一批人,把生态电影推到极端,根本不需要拍电影,镜头不需要动,只需要一帧就可以,甚至一帧都不用,你直接到外面看就可以了。
美国有个著名的音乐家叫做约翰·凯奇,他写过一本书叫《寂静》,他说还需要人去演奏音乐吗?不需要,打开窗户听自然的、人的声音就可以,那就是音乐,自然本身就是音乐。Bozak说真正有一种电影叫做生态电影的话,还拍什么,你到那个地方去看就可以,自然本身就是电影,生态本身就是电影。Bozak提出“低碳”甚至“碳平衡(carbon-neutral)”电影、“可持续电影(sustainable cinema)”,甚至无光影像(sunless image)(没有光怎么会有影像?)“静止影像”、“无电影之电影(film without film)”。不用胶卷的电影,不用光的电影,不用拍的电影,最后也可以加一句不用看的电影,这就是ECO。大家对Bozak虽然颇有微词,但他有一个东西是很值得探讨的,他把物导向的方式进行了一种推进,就是我们未来的生态电影真的应该最大程度消除人的痕迹、拍的痕迹、看的痕迹、人的主观,以及各种以我观物的视角,这才是生态电影。虽然不一定像Bozak那样把所有这些电影拍摄的东西降到最低限度,但我觉得他提出了本体问题——电影到底是什么?这是生态电影为我们提出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点。电影到底是人拍出来,人制作出来给人看,还是电影最终拍出来是为了让人看到更大的世界,让人从人的世界里跳出来,去看到在人之外还有一个世界,叫做生态。是否在这种意义上才具有一种生态意识,而不是花费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去拍环保的电影?
大家看这个图,这是Bozak的书扉页的插图,真正的电影是这样——你应该躺在冰面上去抓一条鱼,旁边其实都不需要有摄像机,(大家)不需要看了,反正你自己看到就可以。
小野洋子在1964年创作过一部作品《music》,这是一部音乐作品,她总谱上只写了一个字water,最后加了一个句号。什么意思?这就是音乐,(你)去听就可以了,我不需要演奏,不需要浪费时间去排练,去制作乐器,制作CD,占用场地……不用了,我就告诉你,听那个水就可以了,这就是“生态音乐”。如果我创作一部生态电影,我就“光”然后“。”,这就是生态电影。难道不是吗?

从这个意义上,我发现中国古代道家或者自然的观念,是有一些接近的地方。《庄子·大宗师》说,把所有人的东西都剔除掉,剩下的东西,然后这个世界就呈现出来了,最后叫做“朝彻”,就是让光照进你心灵的斗室里面,把它照亮,然后你发现其实心灵空无一物,它是空虚的,它是空空的房间,但心灵是空虚的所以可以容纳更大的世界,你能够open朝向更大的世界。所以像克利斯·马克《堤》这样的作品,你会觉得很环保,他的影像是不动的,是一帧一帧的特别环保,他就拍了一下,像幻灯片一样。但这还不够极端,后来像Scott MacDonald对生态电影有更极端的界定,是我非常同意的。真正的生态电影是什么?像Bozak的东西也不行,我觉得真正的生态电影应该让我们能够意识到,不是说外面有一个世界而且进一步意识到这个世界在死,而是应该把这个世界在死亡的痕迹呈现给我们,这才是真正的生态电影,而并不仅仅是我们跳出类人类的世界去看到一个物。所以Scott MacDonald用灭亡之物的残迹。这是我们今天重新想生态这个问题的核心要点。OOO是不够的,OOO仅仅是起点,相反死亡的残迹(vestige)这些东西才是我们进一步把握生态电影的要点。
最后列几张图,这是法国艺术家在台北双年展的末世考古,大家体会下什么叫做末世考古:这是电脑的机箱,这是硬盘,这是一个键盘。有没有想过它几十万年之后埋在土里的样子?真正的生态电影应该做到这样的程度,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今天所有的东西以及媒介都是可以死的,世界也可以死的,我们的生命也可以死的,不要再用不朽、永生的东西麻醉我们今天的生命,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是可朽的。这是西方哲学的第一个命题,苏格拉底是有死的,人是有死的,有死所以才为人,所以不要再用那些媒介的东西麻醉自己,告诉我们还有一个数码的天堂。我觉得这是今天生态电影回到的终极的意识。这是Timothy Morton最近的一本书《BEING ECOLOGICAL》(生态的存在),他在这里引用了藏传佛教的一个词“中阴”(梵文antarābhava,藏文Bardo),是生和死之间的间隙。藏传佛教人死之前会引这段话,“中阴”是介于生和死之间,将死、垂死这样的状态。我觉得今天的生态电影应该在“中阴”的一个阶段,重新去领悟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生命的本意,而不是不朽的,这是我自己理解生态电影大致的含义。但我今天可能已经不是这样的考虑,我更强调回到人本身的体验,而不仅仅谈论物的衰亡和世界的客观,这是我当时想到的要点,我觉得今天生态电影对大家的启示也在这里。
主持人(周佳鹂):感谢姜老师。姜老师讲座信息量很大,他不只是跨媒介的探讨领域,还有很多对艺术的思考,并在思想上把中国传统思想与诸多西方新的思想进行一种呼应的关联。我想就姜老师的讲座进行这样的梳理和总结:他先从人跟数字媒介、数字天国之间的博弈,“浮士德式”的交易作为一个引子,引出媒介在人类历史上的三种维度,第一种是框架形态下人类中心主义这样一个维度;第二媒介在流动这个阶段中,媒介的交织和互相渗透;第三种是聚合的媒介状态下,它是某种程度上的不朽,但也是某种程度的终极。这样三个阶段,再由此引出对于影像的思考——“生态电影”这样一个专用词,在“物与观”之间形式和内涵间的探索,从而最终思考我们怎么样在当今这个时代去重新思考生的概念、人类存在的概念。我想这个议题在今天让每个人都尤为触动,或许是因为疫情之中每个人都会思考自然万物跟人生死之间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像姜老师讲到的“间隙”的一个状态。另外这个议题在我们今天纪录片大会讲很有意思,我前段时间去横店,横店是巨大的人造景观,你在每个影棚里看到是影视产业制造的工业垃圾。我经过各个影棚看到每天搭景所带来的消耗,几千件古装的衣服,各种古代的影棚,它们被拆卸后就是一堆物质的残骸充斥在横店里。而纪录片在做什么?纪录片花着好莱坞大片用在口红上的钱,可能只是(相当于)好莱坞大片口红上这一点经费,真正在探索或者程度上接近着或者更新着人类物和观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讲座跟我们整个大会是有很密切的关联,因为好像纪录片某种程度更容易探索观和物之间的关系。

主持人(周佳鹂):谢谢姜老师。接下来我们留一些时间给在座的各位,大家可以向姜老师提一些问题,或者把自己的思考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有没有同学提问?
现场提问:我们说电影是一种单向交流媒介,单向交流是它限定性,今天我们的老师在做各种各样的融合,这种研究不断强调观众的参与感,不断突破这种限定,这种突破是否意味着电影在某种程度上的自我消亡或者不在?
姜宇辉: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最近两篇文章都在谈互动性,我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说。今天的电影跟以往的电影是不一样的,以往的电影在影院里或者在家里家庭影院看,其实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从头看到尾。当遥控器发明的时候其实电影已经开始死亡,这是格林纳威的说法,他说,电影最近一次的死亡是来自一九几几年,就是当第一个人拿着遥控器走进他的客厅的时候。因为你可以改变电影的线性运动,以前影院的电影是从头放到尾不能断的,你是跟着导演的思路一直走下去的。但今天你可以随便,你可以正放、倒放,不喜欢看可以停下来,你甚至可以剪辑下来弄一个同人的电影。其实interruption从那时候,一九八几年有录像带或遥控器的时候已经开始了。今天当电影变成网络方式传播后,这个互动性就更不得了,大家在B站看一个电影,并不仅仅是操控甚至可以和其他人一起看还可以发弹幕,还可以边看边和其他人去交流,你甚至可以打断进程去做一些别的事情。今天的电影互动性非常非常强,强到有你的这个质疑:电影还是电影吗?我写过两篇文章探讨这个问题,确实在电影研究中当代有两波学者抱正反两种意见:第一种,他认为电影的游戏化是一个必然趋势,是不可抗拒的趋势,电影必然会被游戏取代。今天游戏的电影化非常明显,很多游戏里面都是用电影的场景,电影的叙事,电影的过场,甚至人物的塑造、对话是非常电影化的。所以有一波学者认为游戏取代电影就像电影取代之前的绘画、戏剧,这不是说以前的媒介形式死掉,而是它是一种综合的形式,把以前各种各样的媒介形式都包含在一起。今天的电影它既是戏剧,又是文学,以及各种各样的绘画交织在一起。未来的游戏也是这样,可能是电影、表演、书写等各种各样结合一起,这是第一点,认为电影要进化成游戏的阶段。
第二,有一波学者,如《互动电影》的作者,认为互动电影就是电影必须去抗拒的命运,他认为真正的电影就应该是导演拍出来的,有线性的叙事。在这个线性的叙事里,观众才能够经历和绵延生命的历程,让你在里面有反思的过程。导演给你启示,导演讲了一个很好的完整的故事,你通过这个故事去想想自己,想想世界,想想人生,这里还有很多艺术的手法贯穿在一起。但如果这个电影是交在你手里像橡皮泥一样可以随意摆弄的东西,可以切开、倒放,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根本不是电影,这就是电影的死亡。
正反的两个观点,一个认为电影变成游戏是电影的新生,是电影进化到后电影的下一个阶段;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是电影必须抗拒的一个命运,电影必须守住自己的底限——线性的叙事,时间的过程。我自己的立场非常简单,我是倾向游戏这一方(的观点)。
现场提问:从这个意义上继续深入,有另外一个追问,今天的电影可以在家里看,电影院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姜宇辉:在电影院里,你看电影的形态或方式跟以往也不一样。你在看屏幕上影像的时候,大家也都在刷手机,在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你也不是认真在看。电影院也已经被周围的数码技术生活所渗透。以前看《天堂电影院》,里面那个小孩叫多多,他走进电影院是一种神圣的感觉,会觉得那是天堂。今天有几个人走进电影院会有这种感觉?用苏珊·桑塔格的话来说,即“迷影”的体验。没有。我们已经没有对电影的迷恋,觉得电影就是玩一玩,今天吃完饭旁边有个电影院就进去坐一会,反正屏幕上这个故事也不错,然后我们就发发微信说我今天看过这个电影挺有意思,大家评论一下。今天的电影已经不是在电影院里存在了,它已经是一个跟进的方式,那种“迷影”的在场感,即你坐在电影院里面对这个影像达到那种巅峰的体验,已经没有了。
现场提问:电影从欧洲诞生到现在,作为文化属性在不断消解?
姜宇辉:迷影文化这个东西已经被消解了,因为桑塔格提出对迷影的哀悼,实际上那篇文章就叫做《电影百年回眸》,就是她过了100年之后再看一下,发现今天就没有人再迷了,也不可能迷了。
现场提问:刚才讲到《Riverglass》这部影片,让我想到安迪·沃霍尔拍的《帝国大厦》,我不知道您怎么评价这部电影?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说现在纪录片作为主流媒介,那么您的思考(认为)它在跟人的关系中,在你刚才谈的三种模式中你更倾向(认为它属于)哪种?
姜宇辉:我们今天研究《帝国大厦》,其实是把它放到另外一类,叫做静止电影,因为它真的是不动的。有很多人分析它,有两种考虑,第一种认为它也是种手法,仅仅是一种手法,以前电影镜头一定要连续去运动,有高速运动、有剪辑蒙太奇,但沃霍尔从创作的手法上跟主流方式有一些叛逆和不同。但还有一派,强调静止电影实际上关注的不是物,它关注的是人的意识状态,不是说《帝国大厦》让你看清楚这个帝国大厦有多高,有多少层,他不是做这样的工作,他其实是想让你转化自己的意识状态。通过一个对象,通过像的运动达到一种顿悟,达到意识流的间断,它指回的是你的心,不是物。当然可能有人会从物的角度去分析,但我看过《帝国大厦》这部影片,我个人觉得其实物的成分并不是很突出。

现场提问:那它有OOO的导向吗?
姜宇辉:首先,那时候还没有OOO,然后我觉得它和《Riverglass》是非常像的,哪怕这个影像是不动的,是非常慢的,但你仍然感觉到人的在场、拍摄者的在场、观看者的在场,这种在场感是非常强烈的。不知道您了不了解日本有个摄影师,叫做杉本博司,他拍过很多建筑,如博物馆,包括几何,他也拍过双子大楼,就是在被炸之前,他把双子座模糊化了,他部是清楚拍出来的,你会觉得他拍的双子座就变成了一个几何的形象,然后模模糊糊在眼前开始洇开了,像墨一样。我觉得这个处理跟安迪·沃霍尔很像,他指向的其实是我们观者精神状态的变化,他并不关心要把我们人的意识带向物那边,我觉得无论是杉本博司还是马里孔蒂还是沃霍尔,我觉得沃霍尔更没有物导向这种倾向。但你说今天有哪个影像真正达到OOO也很难。
现场提问:这个创作跟他之前的创作很不一样,这是完全抹除掉人的创作方式?
姜宇辉:对,但可不可以说跟他的波普(艺术)也是有一些相似呢?比如波普处理的是什么?就是原型和复制之间的关系。在机械复制时代就没有原型,复制可以杀死原型,就是所有的复制品不断衍生,我可以复制无数个玛莉莲梦露,无数个金宝汤罐,那他拍《帝国大厦》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想法?你认为帝国大厦只有一个吗?它每一秒都在那里,那个镜头一直在那里对着它,那是不是也有一种一和多、原型和复制,影像流动之间,时间和空间、静止和运动之间的关系呢?这是很重要的。
现场提问:纪录片作为一种媒介,跟人的关系是属于哪一种模式?
姜宇辉:今天纪录片,前面三种模式都是有的,有各种各样的。我觉得像《舌尖上的中国》应该属于框架,会告诉你中国的食物是这样,就像《深夜食堂》一样,你会按照《深夜食堂》告诉你的那个地方去吃,按照主人公的方式去吃,这就是框架,他给你个框架。第二种能量模式,有点像《利维坦》那样,哈佛那个实验室,我很早就写过(关于)《利维坦》的文章,那个就属于流动。你发现GoPro不是人在拍,你把GoPro拴在鱼上面,鸟上面,船上面,那是物在拍。而物传过来的是什么,直接那个水就冲过来了,第一个镜头他在杀鱼的时候,视角和你是齐平的,你好像被鱼压在下面,而鱼的血水直接冲过来了,那就是energy。你感觉电影并不仅仅是影像,电影传递的背后其实是世界的能量,非常明显。第三种OOO,今天没有找到很好的OOO的例子,我觉得要不然就真的像Bozak说得一样,你就写光就好了。OOO是不是对电影本体的消解?你不要再拍电影,不要再按照电影的方式去拍电影,可能就是OOO。
主持人(周佳鹂):可能在纪录片领域还是有OOO这样一种可能性吧。
姜宇辉:对,但很难。能量流动这种模式可以做,框架模式(电影)到处都有,但从聚合里面跳出来,艺术家能做什么我们是不知道的。原创力是在艺术家那边,我们只是做一些评论,还是期待纪录片导演可能未来会有一些自己的创造。在和聂(欣如)老师讨论时,我作了一个很悲观的论断,因为我是搞电子音乐的,我觉得在近十年电子音乐领域没有新的手法,所有东西都被尝试过和穷尽了,聂老师反驳我说也许未来会有新的东西出来。新的东西是不可预测的,所以还是期待艺术家可能会做出不一样的创造。
现场观众:姜老师好,我不知道你还是搞音乐的。
姜宇辉:我不是(研究)音乐的,我只是声音,而且是电脑音乐领域。
现场观众:您刚才说生态电影,我想到《坂本龙一:终曲》里的三个场景。第一个场景在森林里去吸收那个声音;第二个在他的家门口拿个水桶,也是吸收声音;第三个是直接把冰雪融化的声音钓上来,希望老师讲一下他的创作方法论和思考的理解。第二个问题是老师您怎么看《列夫·朗道》这个系列,您是怎么看待纪录片的这种边界的模糊?
姜宇辉:这两部纪录片我都没有看过,您大概是专业研究纪录片的吗?
主持人(周佳鹂):《列夫·朗道》是那个DAU电影。
现场观众:就是前年在柏林(电影节)上映的那个。
姜宇辉:那我们也看不到。
现场观众:他搭建了一个乐园,然后他们进去拍,但其实也不能完全算纪录片。
姜宇辉:伪纪录片是吗?那我回去看一下。第一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一下,第二个问题我没有看过所以我不知道。我做过一些实地录音,我听(你介绍)下来有一点像soundscape,就是声景。在电子音乐史上或者声音艺术史上有两本重要著作,一是Murray Schafer 的,另一本是米歇尔·希翁写的《声音》,他提出三种聆听,第一叫做因果,第二叫做语义,第三叫做还原。“还原聆听”要把人的所有东西去掉,纯粹听这个声音,所以他录了很多火车,有一个作品叫做《火车练习曲》,就是他反反复复让你听火车是怎么过来,里面各种各样它本身的节奏等。后来发展到加拿大的R.Murray Schafer的《世界的调音》,他说你不需要人去录,直接去听自然的声音就可以,所以他总结了各种各样去聆听自然的方式,怎么听雨,怎么听水声……他那本书概括了一下(这些方式)。我听下来《坂本龙一:终曲》有点像soundscape的创作方式,淡化录音的技术,淡化人的介入,用最原始的让自然音呈现出来,记录下来,可能是这样。你感兴趣的话,日本有一个做soundscape很好的音乐家,叫角田俊也,他录得非常好,他把一个瓶子放在下水道里,有声音过去,他就录这个声音。当然你可以说他也用到录音机了,但他其实想说你就应该自己拿一个瓶子放在你家窗口去听就可以,但真的很好听。包括很多声景,有个瑞士的(音乐家)他录的船厂,风刮过来,风吹船索和缆绳的声音,声音非常棒,这是我近十年听过最好的soundscape作品。有风的声音,船的声音,让你觉得你是在里面的,你不是一个听者,你听的时候会觉得你跟生态这个东西是连在一起的,你甚至觉得整个身体会跟着那个缆绳在风里动,可能这就是ECO。我们说要用媒介,但要把媒介里面人的痕迹淡化,这叫ECO,叫还原。那个《列夫·朗道》我听起来还是有点像框架,是人造了一个框架,在里面进行叙事,是这样吗?
主持人(周佳鹂):非常刻意地创造一个框架,让演员在里面生活很多年,很受争议。
姜宇辉:那是不是很像《楚门的世界》?
主持人(周佳鹂):这种方式,就很受争议。
姜宇辉:他是不是隐喻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所有东西都是人造的。这要看过才知道,不能乱说。
现场观众:老师,您好,我不是电影专业的,我这里有一些疑惑。您讲到“物”,“物”这个概念,其实也是从人的视角出发,是区别我与整个世界的关系。既然从人的视角出发,我觉得我们是无法评价,离开人所有的感知,那“物”又是什么?我是在想,电影其实也是一种记录,它是能引发我们人种种感觉的东西。离开所有感知,物是什么?物自己本身的形态是什么?我觉得无法揭示,又怎么样用影像来去表现物自己呢?我感觉这是个悖论。

还有一种方式,我想到是在梅洛·庞蒂那里,就是我们可以进行一种逆转。梅洛·庞蒂是法国的哲学家,他晚期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做可逆性,实际上是一种修辞,两个句子倒错排列,他强调人跟世界之间是可逆的。我在触摸物的时候,物同时也在触摸我,touching和touch这两个是同时的、互逆的、交互的,在这里就会发现,这其实就是一个逆转。当然后来我看哈曼(Graham Harman)在一本书里也提到了这点,他觉得你直接谈那个物是无效的。哈曼(Graham Harman)写的那两本(关于)OOO的书都看过,(《更思辨的实在论》),上来就说物的世界什么样的。这没有用的,他用人的语言,描述了一个纯粹物的世界,这根本没有跳出去。所以我觉得梅洛·庞蒂是对的,你先在人和物的关系里面,想办法把这个关系逆转过来。一开始我确实是在touching,但确实像梅洛·庞蒂所说,它有一个交互的作用,反过来物也在touch你。touching和touch如果是一个交互的,可以转化的关系,就说明这个O(Object),即这个“物”本身有一个独立的存在。原来是人在摸物,但反过来物也可以去摸你,物本身的力量就呈现出来了,它本身的存在就呈现出来了。我觉得今天要回到的是,物的问题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的体验的问题。我今天不是从这条线上去想,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留给OOO的理论家们,如果还有(问题)他们自己去解决。但是我觉得这两种方式可能就是最好的了,从哲学上来说,真的很难有其他比这更好的方式。今天我们看OOO好久没有人谈了,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条死路。
主持人(周佳鹂):包括我们要在电影里找一个案例,也是感觉无法互相说服。
姜宇辉:去年在疫情之前,PSA做了鲍德里亚的摄影展,跟北师大刘翔老师做了一个对谈。刘老师说鲍德里亚的作品是非常OOO的,他说沙发上一个红布,蒙在上面没有人在坐。但我看了之后觉得这非常“人化”的,因为上面还有褶皱,就是人在上面坐完之后形成的褶皱,(人)离开了你拍下来,我觉得这个“人”的presence是非常强烈的,一点都没有OOO的倾向。鲍德里亚所有的摄影都是非常温情、非常人性化的,包括俯视的视角。他拍一对情侣是45°角斜着拍下来的,我觉得特别像希区柯克或安东尼奥尼的那种,那个视角感觉到很孤独投射下来,我觉得这两个人是被世界遗弃的,很孤独的抱在一起,一点都没有OOO。
主持人(周佳鹂):可能您特别丰沛,所以特别容易投射。
姜宇辉:我是“以我观物”,我从来没有“以物观物”,所以我后来只能回到更强烈的,如体验,伤痛,我是觉得我可能太投射了。
现场观众:非常感谢姜老师的讲座,很受启发,我自己是搞电影研究的,我听您讲“物物”的物质主义理论,可能一直前面都在讲怎么做到无我,根据物质主义理论,您刚才也提到物其实是有能动性的,你触摸它它会有反映,在这个意义上物是能动的,这个意义上人是否也变成物的一种,就其实人也是物?所以物物具有可能性。
姜宇辉:是的,后来Levi Bryant(布莱恩特)写过一本书《The Democracy of Objects》(《万物的民主》),其实就是庄子的“齐物”,即万物均齐,哪怕鲲鹏能飞很远而下面的虫子只能跳一米高,但作为生命的形态,我们都是万物的一种,我们是一个份子,我们是平等的。彭祖能活一万岁,我只能活一百岁,但是我们是在equality(层面)的。
现场观众:物质主义强调人和其他物是平等的,我们都是物,我觉得OOO是否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
姜宇辉:这就是OOO后来的一个发展。
现场观众:(所以OOO)不是完全无人的状态,因为人本身也是一种物。
姜宇辉:但你你怎么样达到这个平等,看出这个平等?那需要把原来人类中心主义的东西去掉,比如“以我观物”的那些东西,情感的、文化的、欲望的慢慢淡化,如庄子说的不断“外”出去,才能达到“朝彻”。所以“无我”是个阶段,最后达到物的均齐,达到equality。最后达到物的均齐境界里,“我”是不是有?“我”肯定是有,但这个“我”和之前“以我观物”里的“我”是同样与相似的吗?可能是不一样的。它意识的形态,面对世界的态度和立场,都发生了极端的转换,可能是一种“新我”,不一样的“我”。
现场观众:您刚才提到生态电影的理论,生态电影刚才提到是被批判的。
姜宇辉:不是,那是几个学者去批判的。
现场观众:它在电影研究领域里面也都是被批判的,生态电影从一个主题的角度来讲,很多电影像您提到的《后天》这样的电影是有问题的,因为主题上是这样但实际上是反生态的。但刚才讲到《Riverglass》的时候,我在想它也是一种的形式的角度,像很多这种电影都是由很多长镜头嘛。
姜宇辉:对,也是一种手法,它特别有它自己的style,它有自己一个类型化的特征。
现场观众:这种长镜头的方式,会比较浸入式的,我可能不一定非常赞同这种生态电影更多的存在于纪录片里,它在故事片、剧情片也是存在的。
姜宇辉:因为长镜头是普遍都运用的手法。
现场观众:刚才您谈到有学者去讨论《Riverglass》这部电影,他可能更多是从形式、手法的角度去讲,所以生态电影进入到最后,是不是所有电影可以从生态电影的角度来解读,也就是说,生态电影不是一种类别或类型,而是一种角度。
姜宇辉:对,是一种诉求,一种态度,或一种立场。您这个观点我很认同。如果让我说最生态的,也许塔可夫斯基就是最生态的。虽然他也消耗资源,但他那种对ECO、沉浸式的、长镜头的,他特别有一种ECO的特性。
主持人(周佳鹂):但实际上长镜头是最花钱的,工业消耗上最大的,所以这很悖论。
姜宇辉:但它给你的意识状态造成是最接近物的状态,因为这是物的结构,没有剪接,没有蒙太奇,没有叙事。
主持人(周佳鹂):您最后讲到生态电影当中沉浸式的体验,因为您是德勒兹的专家,我又做德勒兹影像的研究,会让我联想到德勒兹在他在《时间-影像》当中提到的,影像总是从某种混沌的、停滞的居间当中重新找到一种力量。
姜宇辉:哦,interval。
主持人(周佳鹂):您觉得这两者其实是有渊源或者有差异的吗?
姜宇辉: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在德勒兹那里,沉浸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他讲的电影实际上在讲影像本体论,没有讲人的主观意识状态,这(也)是他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后来帕特里夏·皮斯特斯(Patricia Pisters)写了(《神经-影像》),实际上在运动影像、时间影像后面还应该有一个Neural Image,你应该讲这个影像怎么跟我们的脑子连在一起,德勒兹后面讲到一点点,但他就没有讲完,所以沉浸我觉得(在德勒兹那里)不是很重要,但你刚才讲的间断很重要。我觉得“间断”首先是物的间断,其次这个“间断”还可以造成你的意识状态或者体验状态的一种间断,它是融合在一起,然后最终的“间断”我觉得应该像“中阴”,是生死之间的间断。interval是我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因为它是一个断裂。

姜宇辉:对,因为我开篇讲进化就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数字是连续的,是我们人类意识的下一个阶段,还有一种认为数字是深渊,是隔开我们人类的今天和明天,是断下去的。那我是更接近第二种观点。所以可能不能叫interval,不能叫做中间,我觉得应该叫做abyss深渊,人类如果跨不过去这个abyss就死亡了,我觉得它有一种临终关怀的意味。但这只是我的一种理解。
主持人(周佳鹂):很感谢姜老师。我觉得姜老师近几年的研究,我发现您更多转向人类生存、生活本身当中。
姜宇辉:对,转向列维纳斯、阿伦特,转向现在。
主持人(周佳鹂):从原来我们觉得特别当代、特别时髦的思想中慢慢有点回溯。
姜宇辉:难道你觉得列维纳斯不够时髦吗?但你今天看到的很多话,就是在列维纳斯书里面,在二三十年前他就说出来的,列维纳斯就说这个未来不属于我们的,我们的未来不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未来是失控的,这是他说出来的。
主持人(周佳鹂):姜老师有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哲学课,有一句slogan: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让我们用哲学连接彼此的灵魂,哲学的意义就是带给我们思想某种程度的激荡与抚慰,让我们在有困惑或不解时,意识到有很多人有过和我们一样的困惑,但跟我们不一样的是,他们已经给出了回应和答案,像您说的列维纳斯。这一点在后真相时代,在2020年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情境当中,对每个人都尤为珍贵。
姜宇辉:我想说哲学是有答案的,只是你没有用心去看,但哲学真的有答案,而且是明明白白有答案的,只要你能看懂,能理解,哲学的答案都是终极的答案,是没有问题的。

原标题:《IDF学术·讲座︱姜宇辉:假若媒介永生—— “生态电影”与“以物观物”》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