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励轩|再造中国:从“五族共和”到“中华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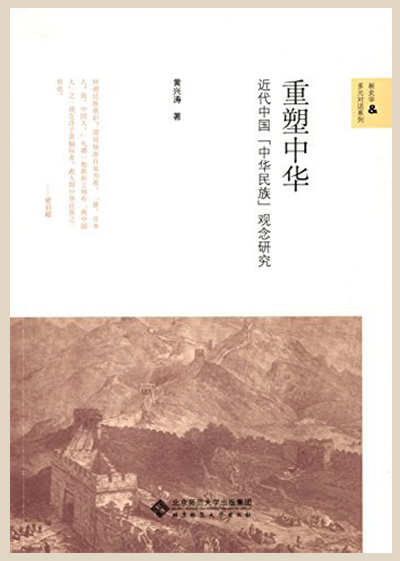
《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黄兴涛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0月,435页,59.00元
皇姑屯事件之后,张学良将原来悬挂的北洋政府五色旗换成国民政府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并于1928年12月29日通电南京,宣布接受国民政府管辖,被称为东北易帜。东北易帜长期以来被当成国民政府统一中国的标志性事件,然而对该事件影响的过分渲染,却很容易遮蔽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北洋政府及国民政府从未能够对中华民国的所有领土实施过有效管辖。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包括蒙、藏、疆在内的边缘地带纷纷寻求独立或自治:外蒙古除了1919年因徐树铮出兵而短暂取消自治外,一直自外于中央,乃至数次宣布独立;内蒙古处于当地蒙古王公统治之下;西藏由达赖喇嘛的噶厦政府统治;新疆则在大部分时间由地方军阀自治。北京的北洋政府抑或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都无法在这些地区征税、征兵、任免地方官员。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他们所接手的是支离破碎的中国,所以对于民国的政治和知识精英而言,他们需要思考国家的重新整合。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兴涛2017年出版的《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则正是有助于我们理解民国精英如何利用意识形态武器重新凝聚这个国家的概念史力作。
民国初年的政治精英用于整合新国家的理论武器是“五族共和”,即主张团结满、蒙、回、藏、汉五族共建中华民国。在黄兴涛看来,这一政治理念既被革命党人倡导,也为袁世凯等北洋政府统治精英所接受。众所周知,同盟会早期的革命口号是极具排满兴汉色彩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虽然这一口号对发动革命具有鼓动作用,但却不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同盟会领导人之一刘揆一认识到这一问题,在辛亥革命前就指出:“蒙、回、藏者与满洲同为吾国之藩屏也,满蒙失,则东北各省不易保全;回藏失,则西北各省亦难搘捂。是吾人欲保守汉人土地,尤当以保守满蒙回藏之土地为先务。”(94页)有鉴于此,刘提出,应当团结汉、满、蒙、回、藏五族先进分子推翻清政府的君主专制,建设共和国家。刘揆一的主张获得革命领袖黄兴的支持,一度也得到孙中山的认可,并写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99页)袁世凯等北洋政府精英不仅认同“五族共和”理念,而且也利用自己掌握的国家权力,在政策制定上予以贯彻。袁氏通过颁布总统令,声明汉、满、蒙、回、藏各民族,俱为中华民国国民,不再将他们视为帝制时代之藩属,强调“民国政府于理藩不设专部,原系视蒙、藏、回疆与内地各省平等,将来各该地方一切政治,俱属内务行政范围”。(113页)针对当时边疆地区的离心倾向,北洋政府通过恪守《清室优待条件》以及恢复达赖喇嘛名号等措施来团结满、蒙、藏、回的民族上层。不过孙中山在革命后期对“五族共和”理念却是持猛烈抨击态度的,他称“五族共和”为“无知妄作者”之论,批评象征“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国旗五色旗为“四分五裂之官僚旗”,认为该理念允许各族之间存在一个“界限”,便于中国遭受列强分裂与侵夺,而不利于国家统一。
诚然,北洋政府对“五族共和”理念的贯彻和实施一定程度上团结了满、蒙、回、藏各民族上层,有助于将中国建设为一个现代国家,但它并没有完全遏制边疆地区的分离倾向,外蒙古在北洋政府时期数次宣布独立,并在苏联支持下于1924年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内蒙、西藏和新疆跟北洋政府也是貌合神离。面对中国的分裂危机,孙中山在1919年的《三民主义》一文中提出了新的民族主义理念:“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138页)简而言之,孙此时提出的理念就是要将中国各民族融合为一个新的民族——中华民族。为了证明自己这套中华民族理念有强国之效,孙还以美国为例,指出美国之所以成为当时世界上“最进步、最伟大、最富强之民族”,其根本原因是国内几十、上百种之种族、民族融合为一个美利坚民族,如果中国要实现统一与富强,也必须将国内诸族融合为一个民族。至于融合的办法,孙中山提出,要以汉族为中心,使国内各族同化于汉族。显而易见,孙中山早期的中华民族理念具有很强的一元一体特征,是以同化为基础的大汉族主义民族观。尽管孙中山去世前几年也主张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各民族融合,但他早期的一元一体中华民族理念对国民党的影响更为巨大和深远。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自诩为孙中山的衣钵传人,继续强化“中华民族”一体认同符号,并积极“整合”大中华民族。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各种决议案以及政治场合,一再宣示国内各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后来定期派人去陕西黄帝陵开展祭祖活动,将黄帝当作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进行宣传。国民党以及支持国民党的知识精英还通过著书立说,在学校和社会上传播一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理念。至于蒋介石本人,则进一步在部分场合尝试用“种族”来称呼国内各民族,从而变相否认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民族”地位,以避免与一个“中华民族”产生矛盾。(182页)随着日军侵华,特别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对中华民族理念有了新的表述,这种表述突出体现在强调它的一元一体特征,代表是蒋介石提出的“中华民族宗族说”。蒋介石在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系统提出了这一理论。在他看来,中国各民族并无血统上的差异,而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汉、满、蒙、回、藏是五个宗族,他们组成的是同一个民族——中华民族。(304页)由于国内各族均属同一民族,自然再无独立建国的理由,各族同胞都应在中华民族这一大旗下共同抵抗日本侵略。黄兴涛也指出,蒋介石的这一理论并非异想天开,事实上一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也有来自知识精英的广泛支持。这些知识精英精英不仅包括支持蒋的文人,也包括一部分游离于国共两党之外的知识分子。早在1939年,顾颉刚就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提出中华民族是由许多“种族”在历史上不断融合形成的单一民族,而不是一个多民族组合而成的“大民族”共同体。(267页)无论是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抑或蒋介石的“中华民族宗族说”都是在抗战这一大背景中提出的,其本意都是为了团结国内各族同胞,以实现抗战的最后胜利。然而,这些一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理念较少顾及了少数民族的感受,在实践中还被国民党政府以及支持它的各地军阀当作在他们实际控制的边疆地区推行民族同化政策的理论依据,自然无法得到少数民族的真正拥护。在1946年年底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上,与会的少数民族代表围绕着本民族的权利与义务,据理力争,使得蒋介石不得不放弃了“中华民族宗族说”,接受国内还存在着各“民族”的事实。(326—327页)
中国共产党较早地认识到了国民党的一元一体中华民族理念无法真正获得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支持,因此在抗战爆发后就系统提出了以多元一体为特征的中华民族理念。毛泽东在193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所认同的中华民族是境内各民族结合而成的多元一体共同体。他指出,中国除了有汉族,“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彝人、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他还提出,“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的。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针对蒋介石1943年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抛出的取消境内各少数民族民族地位的“中华民族宗族说”,当时作为中国共产党理论家的陈伯达著文反驳,指出“平日我们习用的所谓‘中华民族’,事实上是指中华诸民族(或各民族)”,而蒋介石认为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其实质是“民族血统论”的法西斯主义糟粕。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眼中,中华民族是多民族构成的民族复合体,是一个复数,而不是单数。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建国后对“中华民族”的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翻译,我们就能体会得到。在维吾尔语中,中华民族被称为جۇڭخۇا مىللەتلىرى,“中华”( جۇڭخۇا)两个字是音译,至于“民族”(مىللەتلەر)则是一个复数,直译过来其实是“民族们”。
黄兴涛察觉到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中华民族理念上的不同,但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武器不光只有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还有一套系统的民族理论以及由这些理论衍生出来的民族政策。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源泉有两个。第一是列宁的民族自决论以及斯大林的民族学说。他们的学说被党内留苏的理论家带回中国来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作。第二是中国革命的实践。与长期待在内地大城市的国民党政治精英不同,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许多人经历过长征,且长期在有少数民族聚居的陕北工作与生活,与少数民族人士打过较深的交道,熟悉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能够根据民族工作的具体情况将列宁、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及苏联经验中国化。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数年,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根据列宁和斯大林的民族理论陆续推行了几个标志性政策:承认各民族的自决权;民族识别;联邦制;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布尔什维克党之所以要推行这些政策,除了本身的理想主义情怀外,还由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实际上处于崩溃状态,他们需要用这些政策来团结国内少数民族,重新统一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很快达到目的,少数民族纷纷投向革命阵营,俄国重新统一。苏联成立后,共产党遵守诺言,将民族自决权写进了苏联宪法,不过由于各加盟共和国实际上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因此只要共产党不同意,这些自决权是无法落实的。中共在学习苏联经验的时候,很注意跟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它放弃了联邦制的主张,而是采用乌兰夫自1945年在内蒙古逐渐摸索出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空喊民族平等口号却从不放弃试图同化少数民族的国民党政府完全不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就是一部尊重少数民族的历史,尽管在革命后期,联邦制改为民族区域自治,但是承认少数民族群体政治权利的初衷始终没有改变,而这是吸引各少数民族精英支持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根本原因。仔细检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我们很容易发现,是中共最终重新统一了自辛亥革命以来就处于离散状态的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尽管统一的主要工具是枪炮,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共当时的民族理论和政策是凝聚边疆民族地区人心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武器。
事实上,黄兴涛在书中对1949年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话语体系着墨不多,因此也没有指出这套话语体系其实拥有很高的自洽性。与国民党政府执着于建立一个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不同,中共早已抛弃民族国家的桎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multinational state)。在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存在着一个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复合体以及汉、满、蒙、维吾尔、藏等各个民族。虽然中华民族以及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民族都使用“民族”这一名号,但两种“民族”并非一回事,之所以产生冲突的误解,来自于汉语的构词规律。汉语名词存在着单复数同形的特点,所以光看“中华民族”这四个字并不一定能分清它是单数或复数,这一现象也存在于其他一些语言中,比如藏语,光看字面同样不能分清中华民族(ཀྲུང་ཧྭ་མི་རིགས)是单数或复数。但对于名词单复数异形的语言,比如维吾尔语,就能很清晰的看出中华民族是复数,是民族复合体。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并不像改革开放后这么频繁,他们更多的是用“中国人民”(Chinese People)来指称中国的人民共同体。毛泽东在第一届政协会上的著名演讲,用的就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不是“中华民族站起来了”,如果我们去搜索毛泽东时代的《人民日报》,有大量标题冠以“中国人民”的文章,而标题使用“中华民族”的文章则屈指可数。使用“中国人民”来指称中国的人民共同体不仅可以把国内各民族都包括进来,还可以避免汉语中两种“民族”的字面冲突,体现了第一代领导集体当时的政治智慧。巧合的是,赫鲁晓夫后来把苏联建构的人民共同体也冠以“苏联人民”(советский народ)的称号,他在1961年宣布苏联已经形成了有共同特征的各民族人民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赫鲁晓夫并没有把这个共同体叫苏联民族(cоветская нация),显然是因为苏联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民族国家,而是承认国内存在多个民族(nations,нации),用“人民”(народ)一词就把各民族都包括进来了。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