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历史是长寿者书写的吗,这些女性传记告诉你真相

愚园路1136弄31号是愚园路上地标性的著名建筑,它的原主人是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和保志宁夫妇。

那时我们在上海愚园路1136弄31号住宅,在八年抗战中为汉奸汪精卫占用,抗战胜利后由政府代为接收,到沪后我即与军政当局商洽。并承市政府协助收回出租,内中所有家具陈设所剩无几,该屋由于建筑坚固,故八年来除了花房及厨房须修理外,皆未受损坏。
-----待一切准备就绪,我即飞赴重庆将先母和孩子们接回上海,住在愚园路,数月后始搬到南京入学读书。
我则奔走于京(注:京应指南京,保氏也有房子)沪之间,因上海房屋的花房及厨房需雇工修理,暑假时候孩子们到上海居住,直至民国三十六年,上海房屋须人照应。孩子们和我也有事要离国,为保护房屋起见,遂将该屋暂租于英国大使馆新闻处应用,租期二年,我们自己亦留一部分自用。
说明房子是由市政府协助收回的,并没有论及黄慕兰丈夫陈志皋律师代其收回此屋并出租给他们夫妇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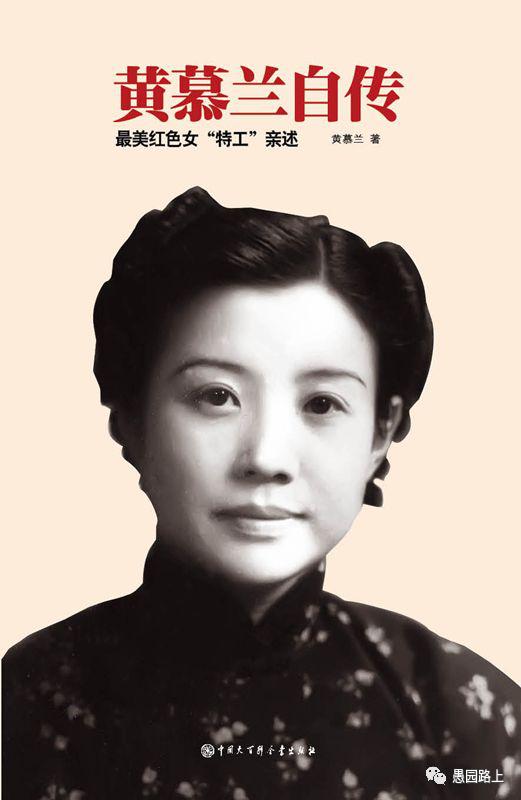
志皋(注:黄慕兰的律师丈夫)的妹妹秉璋有个很要好的同学叫保志孝,她的姐姐保志宁当年在大夏大学读书时,有校园皇后的美名。抗战期间,王伯群去世了,上海的那所大花园洋房,曾被汉奸头子汪精卫占作伪官邸,后来又被日伪特工占作秘密机构。抗战胜利后,保志宁知道陈秉璋的哥哥是一位有名的大律师,就委托志皋代他把这所房子接收回来,当时言明条件是:房子收回后由我们负责代她修理好,她只保留楼下的两个客厅以及二楼的全部;其余楼下的四间大厅、餐厅、书房以及三楼的全部,还有后面的一部分附属用房,都租赁给我们使用,租金按美金支付。但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那时,从大后方复员回上海的人数以万计,上海的住房十分紧张,我们能住进这样高级的大花园洋房,自然大喜过望。


1946年2月,我生下小儿子文中,小名愚宝,意为在愚园路家中所生。不久文中双满月,志皋已近中年,在连生两个女儿之后,今始得子,兴高采烈,特在此举行汤饼宴。承文化界的名人田汉,阳翰笙、翦伯赞、熊佛西,江南耆老冒鹤亭老师,以及戏剧界著名的南欧(欧阳予倩)北梅(梅兰芳)

和各派著名导演、演员,还有已经复业的通易公司全体职工和亲属们,共有100多人光临祝贺,真是不胜荣幸之至。餐叙时,首创当时还很少用的自助餐,个人自选所喜爱的菜肴食品,大家欢聚一堂,毫无拘束地共庆抗战胜利后重逢相叙。文娱节目有来宾即兴自动参与,有欧阳山尊、戴爱莲等表演的舞蹈,真是很难见到的嘉宾佳作,赢得满园嘉宾热烈的欢呼掌声,将盛会引入高潮----特别值得回忆的事,大家一起引亢,高唱田汉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
对于那一天的盛会,熊佛西教授曾写过一篇游记,欧阳予倩吟有七律两首,郭虞裳先生亦有五言长诗留念。----赵景深教授事后在签到簿上写了一篇短文,田汉同志为此还写了一首七绝。

田汉常常借我们愚园路住处请客,因为他在文化界交游甚广,熟悉的朋友太多,只要听说田老大请客,就会有不少不请而闻讯自到的来客,远远超过预定的人数,往往使我们措手不及,穷于应付,好在我们预定的酒席不是董竹君大姐开办的锦江饭店,就是吴湄大姐当家的梅龙镇酒家,她们两位跟我们都有友谊关系,跟上海文化界的人事关系也很密切,所以临时只要打个电话去,增加几桌酒菜,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除了文化戏剧界的进步人士之外,还有刘海粟、唐云、申石伽等名画家在我家举行过泼墨画会,郭沫若也曾在我家召开过科技界人士的座谈会。郭沫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过《洪波曲》,回忆了1937年从上海撤退的情况,以及1946年在愚园路我家召开的专家的座谈会----。
我们在愚园路住有约一年半光景,房主保志宁却背信弃义地把这所房屋以3万美金全部顶让给了别人,逼迫我们迁居。
那天,通易公司的董事长王艮仲借我们这所花园洋房举行宴会,款待上海教育的知名人士时,保志宁的仆人剪断电线,使满堂顿时一片漆黑。-----志高十分生气,拟向法庭上诉,与之论理打官司。保志宁自知理亏,自己不敢出面,赶紧请王伯群的妹妹王文湘(何应钦的老婆)到上海来打圆场,做说客,还请了好多官方权要的头面人物作陪,请志皋吃饭,她讲情说,保志宁孤儿寡母没有依靠,也是怪可怜的,她是为了培养儿子去美国留学,钱不够用,没有法子才出此下策,把房子顶出去了----志高是个服软不怕硬的人,见王文湘当众如此卑颜恭词,以礼软求,只得应允了她的恳求。
孰真孰假, 孰是孰非,过程和细节可能只有当事人最清楚,但黄慕兰在31号花园洋房住过,有照片为证,应是不假。然而,与她自称有友谊关系的董竹君大姐在《我的一个世纪》自传中,却对他的丈夫陈志皋有完全不同的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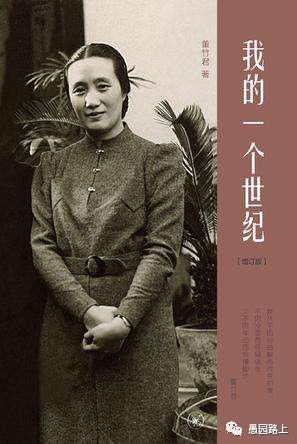
我临走时去前楼看了一下正在酣睡中的孩子,我叫醒国琼,她翻身跳起擦着眼睛,抬头恐怖的看着我和包探,我把书桌抽屉内仅有的十九元交给了她做家用,并且关照她去隔壁找张殊明一道去聘请那位在法捕房里有势力而且专为进步人士辩护的律师陈志皋做我的辩护律师。

在特别标明“律师的敲诈”一节中,董竹君又回忆入狱后的情况写道:
有一次,安南巡捕给我一张小条,并且告诉我:“你的大女儿国琼被陈志皋律师和提你的两个包探包围在陈律师的办公室,陈的家人也在旁(注:家人指谁?),说你的案情严重,要你大女国琼拿出3000元才肯把你营救出来。如果现在手头没有钱,可以打电报给父亲或者南洋华侨,或者南京政府里的要人戴季陶,又说戴季陶是你大女儿的干爸爸,不然,说你可能被枪毙。”他又接着告诉我,你的女儿年纪虽小,却很聪明能干,她回答他们说,母亲自从和父亲分开后就和这些人不来往了,对于母亲这案子,他们这些人不会同情的,她也不愿意去求他们。母亲如果被枪毙了,她就带三个妹妹去跳黄浦江!钱,说什么也没有!”
我听完安南巡捕的话,便拆开看他偷偷送来的小条子,这纸条是国琼女写给我的,信里这样说,“亲爱的妈妈。您好,我们都想念您,望您保重身体,陈志皋律师找我到他写字间去谈话,他和两个包探逼我一定要拿出3000元,我拒绝了,结果我在无可奈何中,答应付600元诉讼费,签了字,他说要我们把这笔钱完全付清才能开庭,我已经设法付了他二百元,其余的钱没有办法,怎么办?”
我看完信条,大吃一惊,原来陈志皋这个人披着进步的外衣,以所谓“左倾”的面貌出现,真不知有多少人受了他的欺骗!通过这件事,使我进一步认识到,看问题要怎样,从现象到本质,从形式到内容,什么是阶级观点,什么是资产阶级的帮凶,什么是帝国主义的奴才和走狗,这是一次深刻的政治课。

董竹君出狱到杭州暂避后,接到国琼女和友人们的信:
说我们走后,巡捕房来家里勒索钱的人有好几个,姓刘的大怒,说他上当了,陈志高律师则逼着大女交出租来的一架钢琴,抵作余欠的300元诉讼费,幸亏国琼女的一位青年朋友谢涛(他的哥哥军界有些势力)挡住了。
因为比董竹君活得更久,因而可以读到董竹君自传的黄慕兰又在自己的自传里为丈夫陈志皋辩解道:
前几年公开出版的董竹君的回忆录《我的一个世纪》内容丰富生动,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在书中有一处与事实不符。文中提到,1932年,她在上海受冤枉吃官司,孤立无援中,她的女儿慕名去找陈志皋大律师求助,不想竟遭对方“勒索巨额酬金”,见死不救。这真是天大的误会,安董在书中所叙的时间,正值志皋因其父介卿公病逝,在家守丧百日,也正是为“周少山启示”避风头之时,他闭门不出,不接任何案件,根本不可能受理董的诉讼委托,更谈不上乘人之危勒索巨金之事。我想很可能有人冒充志皋之名敲诈勒索,而董在恼怒中就把这笔账错算到了根本不知此事的志皋头上,并一直耿耿于怀,但令我不解的是,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我们奉命开展文艺界的联络工作,常在家中举行游园聚餐活动,所设 席不是由吴湄大姐的梅龙镇酒家,就是由董大姐的锦江饭店供应,彼此间有过十分愉快且颇为频密的友好合作关系, 为何从未听到董对此事流露过丝毫的不满情绪呢?当然,1932年时,董大姐尚未参加革命,其社会身份犹是夏都督刚离异的夫人,又是与人合伙办企业的老板,个别律师不知董大姐的实际困境,而仅凭他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索取巨额酬金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但绝不是志皋,不仅当时处境不符,更不符合志皋一生为人处世的准则,如今董竹君和陈志皋都已去世,我决无意在此再挑起新的争论,只是如实说明事实真相,以免继续以讹传讹。

董竹君是不是那么容易搞错,陈志皋当时的情形及为人,因为没有更多的史料和旁证,我们也无从分析,只能让当事双方各执其词。此事也可以说是死无对证了。
孔子曾谈到所见-所闻-所传闻之间的差别,历史学家熊月之先生也曾列出闻-见-历对历史研究者的采信序列。就此案例分析,证明自传只是自传,回忆录也只是回忆,可以参考,却不可作为信史,否则历史就会变成长寿者的历史,尤其是对于一些似乎无所不知、无所不对的回忆录,更应警惕,相比自传和回忆录,当时的日记和原始文档要更为可靠些。
有人说:历史本就是“人们认为往事曾应当如何发生”。只有真切感悟亲历者们“认为往事应当如何发生”这一环节,才可能使“我们以为发生过的事情”最大程度地接近“真实地发生过的往事”。不厌其烦地盘查所有最细小的情节或信息,是为了对描述对象有一种“如肌肤触碰般”的深切了解,以便从海量叙事中寻找“身临其境”的感觉,这对历史研究来说非常重要。但历史研究真正要“还原”的,并非这些细节的真实,而是活动在那个时代的人对那个时代的切身感知。细部研究通过当时人如何感受其生存环境,最终要还原的是那个特定时代的精神气质和宏观历史图景。真正出色的微观研究非但不回避对宏观图景的应有关怀,而且恰恰是宏观叙事不可或缺的血肉基础。董竹君刻意指出、黄慕兰反复辩解、保志宁力图回避的东西,可能正是最重要、最真实、最能说明问题的东西。作为大时代中的女性视角,这些长寿女性的自传和回忆录对于我们“身临其境”,体会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和世道人心,弥足珍贵。
写史者戒之,研究者却可慰。

徐锦江
城市文化研究学者。著有《愚园路上》《愚园路》《愚园路•百年纪念版》,辟上海路史研究一格,上海电视台据此改编成三集纪录片。
识码购书
《愚园路》纪录片在线观看
《愚园路》上集《洄流》
《愚园路》中集《时刻》
《愚园路》下集《呼吸》
读者反馈邮箱:bikey@paiqiwenhua.com
版权所有,欢迎转载或纸质媒体使用,请与本公号接洽授权。
原标题:《历史是长寿者书写的吗,这些女性传记告诉你真相》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