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青年马克斯·韦伯和他的时代
撰文:沃尔夫冈·蒙森
翻译:阎克文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1920年6月14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 · 韦伯(Max Weber)因感染大流感去世。在韦伯逝世100周年之际,我们选发德国学者沃尔夫冈·蒙森所撰《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一书部分内容,以为纪念。
马克斯·韦伯深为他那个时代的政治问题所吸引。他的许多同时代人都希望他能成为一个实际的政治家,他本人也曾有此期待。他的全部学术工作,尤其是他为知识诚实与学术客观性而从事的无休止斗争,在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视为一种日益强大的努力——与当代政治事件保持距离并获得内在自由。这样来看,政治,不唯眼前的实际政治,还有更大意义上的政治,在他的生活以及毕生的工作中,都是处于核心地位的。事实上,即便在他人生的最初几个阶段,也同样如此。可以说,马克斯·韦伯一出生就被抛进了政治。政治是他父亲的职业。这位为人父者是柏林地方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也是该市民族自由党的一个重要成员。城市政治是他的直接利害关系所在,但他的政治活动则远远超出了那个范围。曾有一度,老马克斯·韦伯还是德国国会的议员。19世纪80年代,他甚至进入了民族自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他作为普鲁士下议院民族自由党代表团成员的活动。老韦伯固然并不属于该党领导层的核心圈子,但他是一个极有影响的党务组织者与协调人。他与民族自由党的大佬们关系密切,本尼西森(Bennigsen)、米克尔(Miquel)、卡普(Kapp)、前普鲁士财政大臣霍布里希特(Hobrecht)、艾吉迪(Aegidi),以及冯·西贝尔(von Sybel)、冯·特赖奇克(von Treitschke)、狄尔泰(Dilthey)、蒙森(Mommsen)等著名学者,都是他那好客的大宅子里的常客。孩童时期的韦伯,就不得不在父亲那里旁听频繁的政治讨论,同时,他还通过个人观察,开始了解德国自由主义的概貌。韦伯居然会好奇地倾听父亲唠叨日常的政治工作。成年后的韦伯对德国自由主义历史那种令人惊讶的熟悉程度,与这些年的耳濡目染应该密切相关。

尽管如此,老韦伯的气质决定了他并不是个天生的政治家。和他儿子后来表现的一样,他也不是个本能的斗士。他的政治行为有一种自鸣得意的特征,而且还很容易知足。按照玛丽安妮·韦伯的描述,他属于“典型的资产阶级,自得其乐地立身处世”。马克斯·韦伯很年轻的时候就反感这种生活方式,多年以后,这种反感导致了他与父亲的激烈争吵。政治上的高明见识并不足以支撑韦伯父亲的政治活动,因为,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主要经验领域是财政和行政管理,更专注于日常的实际问题,而不是长远的重大政治问题。他在普鲁士下议院预算委员会扮演了许多年的重要角色。后来,1894年,在德国国会预算委员会民族自由党代表的职位上,老马克斯·韦伯卷入了一场与主管普鲁士大学事务的普鲁士文化部高级官员阿尔特霍夫(Althoff)的冲突,终因人事政策上的战术性政治手段而声名狼藉。阿尔特霍夫因为试图在柏林大学新设一个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而争取民族自由党的支持。老韦伯为了已在柏林大学担任讲师的儿子马克斯的学术未来,也参与了冲突,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受到了排挤,也许是在儿子的力促之下,他辞去了委员会秘书的职务。
1882年初,马克斯·韦伯刚好18岁,他第一次离家长期在外。韦伯被海德堡大学录取,学习法律、国民经济学、历史与哲学。尽管由此摆脱了弥漫在柏林家中的政治空气的直接影响,但他继续分享着父亲的政治观点。当然,政治还只是个附带的兴趣。这时的马克斯·韦伯,兴趣主要集中在各个学术领域,他喜欢听克尼斯(Knies)这位经济学历史学派主要代言人的课,听贝克尔(Bekker)的罗马法,以及其他几门法学课程,包括库诺·费舍尔(Kuno Fischer)的课。他对埃德曼施道夫的研究生班历史课程也非常着迷,曾在那里专心致志于16、 17世纪的问题。韦伯在海德堡的第一学期,与同在那里就读的大表哥奥托·鲍姆加滕(Otto Baumgarten)的讨论,唤起了他对神学问题的严肃兴趣。除此以外,韦伯还阅读了兰克(Ranke)的《日耳曼—拉丁民族史》和《现代史学家批判》(Kritik neueren Geschichtsschreiber)。另外,他还读了萨维尼(Savigny)、耶林(Jhering)和施莫勒(Schmoller),他认为施莫勒并不像以前自己相信的那样是个坚定的国家社会主义者。海德堡大学阿勒曼尼亚人兄弟互助会的酒会对他也没有产生太大影响。韦伯是在第二学期加入兄弟会的,这让他后来后悔不已。
和他父亲的政治老搭档、历史学家赫尔曼·鲍姆加滕(Hermann Baumgarten)的交往,对于韦伯的政治发展更加重要。韦伯与鲍姆加滕一家是姻亲,韦伯的父亲就是在鲍姆加滕家里初遇自己妻子的。1882年圣灵降临节的假期,奥托·鲍姆加滕第一次把他的表弟带到了斯特拉斯堡。这次逗留标志着密切的个人联系的开端,这对于韦伯来说非常重要。转过年来,他就常去斯特拉斯堡了。他在那里完成了一年期志愿兵的军事义务,其间他频繁出入那位历史学家的宅邸。韦伯成了年迈而孤独的历史学家的政治知己。老鲍姆加滕特别喜欢推心置腹地与这个外甥谈论整体的德国政治进程和具体问题。马克斯·韦伯确实是个出色的谈伴,他对日常政治事态的见识令人惊讶。他从斯特拉斯堡写给父母的信中,一再生动地谈到了和姨父的政治辩论。1884年秋天转学到柏林之后,他依然和斯特拉斯堡的这位历史学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即便后来在柏林任教的那些年,马克斯·韦伯还是经常和他联系,尽管不是那么频繁了。19世纪80年代末期,他从柏林的观察角度继续向鲍姆加滕报告他对重大政治事件的看法。
鲍姆加滕是个满腔热情的男人,48岁时,由于那场革命的失败,以及屡屡和官方的检查员发生冲突,他放弃了记者职业,成为一个历史学家,但他继续深切关注政治。尽管直到1866年他还是俾斯麦政策的坚定反对派,此后却成了俾斯麦的支持者;不过,与俾斯麦时期的多数民族自由党人不同,他从没放弃自由主义的宪政信念。在对德国自由主义的著名“自我批判”中,他力促自由派摆脱60年来的教条主义,而不是完全放弃理想主义政治。他坚信,创建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是极为重要的德国政治目标,“国家统一、国家权力、国家独立”是“至高无上的政治目标,是全部现世繁荣的基础和开端”。然而,他和那个时代的许多自由派不同,并不准备满足于1870—1871年所实现的目标,他为这个民族感到骄傲的是,它受到了一种信念的支配,即统一必须遵循道德自制和民族净化的要求。尽管他在1871年曾热情支持俾斯麦,但是,当他看到德国自由主义在一系列决定性的国内问题上遭到失败后,却敏锐地成了那位首相的反对派。像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一样,他对19世纪70年代结束后的德国政治进程越来越感到疑虑和痛苦。
鲍姆加滕批评了那个伟大首相的“恺撒式煽动行径”,批评他害苦了中间力量并迫使社会民主党和教皇党走向激进。在他看来,俾斯麦的恺撒统治导致他在1866年引进了普选权。俾斯麦本人后来承认,他把普选权“扔进坩埚”是个战术动作,以对抗奥地利“最强大的民主计谋”。鲍姆加滕担心,这个做法会带来破坏性的后果,受普选权威胁的“不仅是国家”,还有“我们的整个文化”,它将使“大众在所有问题上都陷入原始的权力本能”。鲍姆加滕还激烈批评了俾斯麦在文化斗争中使用的手段。他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即俾斯麦的行动是出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完全不顾虔诚的新教徒情感。因此,文化斗争的方式具有欺骗性,势必无果而终。根据在阿尔萨斯—洛林边界地区的直接观察,他对政府的政治路线发出了越来越尖锐的反对声音。他为国内弥漫的盲目顺从气氛、特别是它在年青一代中间的影响而忧心忡忡。伴随这种气氛的是政治判断力的危险衰败。鲍姆加滕在19世纪60年代就痛苦地指出了德国人民的政治不成熟,此时谈论得更尖锐、更频繁了。
鲍姆加滕本人虽然与普鲁士意气相投,但并没有片面看重普鲁士在德国编年史上的分量,他还尽力不去忽视南德的传统。在对特赖奇克的《德国史》(该书第二卷出版于1883年)进行的猛烈抨击中,鲍姆加滕摆明了自己对政治局势的批判态度。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的特赖奇克,把政治倾向拟人化,使得鲍姆加滕极为惊惧。他相信,特赖奇克的著作表现出一种头脑狭隘的普鲁士沙文主义性质,醉心于帝国的现状,放弃了一切更深远的宪政理想。鲍姆加滕认为,特赖奇克毫无谦恭之心,肆无忌惮地以傲慢与偏执的民族情感伤害其他民族。鲍姆加滕在与特赖奇克的争吵中,由于少见的苛刻姿态,导致他疏远了他的所有朋友,最终还包括他的老伙伴——海因里希·冯·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
鲍姆加滕强有力地影响了青年韦伯的政治观点。当然,对于他那些夸大其词的看法,韦伯并不打算引为己见。他在与鲍姆加滕阴沉而悲观的见解的不断对质中发展出了自己的观点。不过,鲍姆加滕确实帮助他摆脱了得自他父母的褊狭的民族自由党观念,让他看清了俾斯麦体制的内在弱点。尽管韦伯从未赞同过鲍姆加滕对那个伟大首相个人及其政策的尖锐批评,却接受了这位老人在许多重要问题上的判断。尤其显见的是,对于俾斯麦政策的恺撒式煽动主义性质,他与鲍姆加滕的看法是一致的。例如,韦伯当时就谴责了“俾斯麦式君主政治的危险礼物:普选权,这是所有人在这个词的最真实意义上的最纯粹的平等死亡”,尽管他并不同意老人的悲观主义看法,即实行普选权可能毁灭的不仅是国家,还有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对于韦伯后来的政治发展特别重要的是,鲍姆加滕向他指出了俾斯麦的统治对这个民族政治判断力造成的后果。鲍姆加滕预言说“此人身后将留下巨大的麻烦”,实际上,这在韦伯看来似乎过于悲观了。正如他在1888年致鲍姆加滕的一封信中所说,他并不相信从长远来看“行政机器和我们政治信仰的灵魂会土崩瓦解”,即便“君主统治不可避免将在最近的未来受到冲击”。不过,鲍姆加滕对韦伯尖刻评论年青一代那种不加思考的盲从,却使韦伯敏感地意识到,他这一代人确实谈不上政治成熟。他本人倒是能够避免柏林的同学们那种天真的俾斯麦崇拜,但他同样尊重这位天才大政治家。他曾提出疑问说,为什么俾斯麦总是忘记恰恰是“他本人激励了党派精神,从而毁掉了‘国民的好感之源’”,但他却悲哀地发现,这使他遭到了迷恋俾斯麦的同学们的一致责难。

韦伯深为他这一代人对政治问题缺乏兴趣而忧虑:“我这一代人真是令人称奇,他们所关心的事情无非就是,要么与反犹主义沆瀣一气……要么就是达到更高的水平,认为模仿‘原原本本的俾斯麦’意义重大。”他看到,那些政治不成熟的同学们在“特赖奇克讲课时只要语带反犹味道就会爆发出……一通狂欢”,其实是在释放一种紧张情绪。他确信俾斯麦崇拜、反犹主义和天真幼稚密切相关。他这一代人“最最不可思议的”特征,就是对“本世纪历史那种奇特的无知”。
特赖奇克对一部分受过教育的德国中产阶级的有害影响,导致韦伯步鲍姆加滕后尘,疏远了那位大历史学家。他并不倾向于附和鲍姆加滕那种全盘否定的裁决,而是认为,特赖奇克仅仅是没有足够充分地遵循学术客观性标准。当然,韦伯不可能忽视特赖奇克给听众留下的强大印象,那种从他火山一般的天性中喷发出来的魔力。他认识到特赖奇克的片面性背后有着名副其实的热诚,以及伟大人格的严肃性。他曾读过特赖奇克的诗作并把它们寄给了赫尔曼·鲍姆加滕,因为他发现,“里面那种诚挚的理想主义,是这个在许多方面都不幸的人哪怕犯下最不堪的错误也不会遗失的。……如果说他在讲坛上声名狼藉的影响是一种不幸的话”,他给鲍姆加滕写道,“那首先也是听众的(错)……”
俾斯麦同样是这种情况:国民知道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如何对待他,如何坚定地利用他,他们给了他信任,这是他应得的——他们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白这一点,可是现在太晚了——他那些常常具有破坏性的个人政策,影响所及已经超出了他们所能把握的范围。我的同时代人竟然如此崇尚军国主义以及类似的所谓“现实主义”文化这种怪物,竟然藐视一切不求助于人的邪恶品质——特别是粗野残忍——而达到目标的努力,然后是大量且往往非常刺耳的偏执看法,与别人的观点进行斗争的亢奋,由深入人心的成就感引起的对今日所谓“现实政治”的偏爱,凡此种种,就不是他们从特赖奇克的教程中得到的仅有的东西了。
韦伯特别抵制特赖奇克把政治与学术融为一体的做法。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开始有了激烈反对学者们进行任何煽动和预言的意识。当然,他也承认,人们可能会看出,特赖奇克“就是在这些过度的党派激情和偏见中……从事一种伟大而热情的理想架构的追求”,但这实际上意味着,“他忽视了不计后果、只求真理所需的真诚严肃的努力”。
然而,特赖奇克对韦伯政治观点的影响却不应被低估。韦伯在柏林时,可能至少听过特赖奇克的两次课程,其中一次讲授的是“国家与教会”,这是一次谈论政治的著名演说。被特赖奇克论述国家的性质时置于核心地位的大国理想,把民族国家提升到政治标准的高度,以及藐视小国寡民的生活,全都重现在韦伯自己后来的政治思想中,一定程度上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可以认为,特赖奇克积极支持雄心勃勃的帝国主义海外扩张政策,给韦伯留下的印象特别强烈。韦伯在弗莱堡就职演说中要求德国采取自己的世界政策,就很可能与特赖奇克的影响直接有关。然而,就我们目前所知,韦伯并没有全盘接受特赖奇克的帝国主义目标,也从未怀有特赖奇克式帝国主义那种典型的反英偏见。
我们无法确定马克斯·韦伯在柏林就读期间还有多少其他教师影响了他的政治发展。韦伯自己提到了格奈斯特(Gneist)、艾吉迪(Aegidi)和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但他们的影响可能并不大。韦伯对所有把学术政治化的倾向都感到不安,使他不会接受这样的影响。另外,到柏林之后,韦伯很快就开始逃课,他宁愿待在家里大量读书。当时他极为沉迷自己的专业兴趣,因而远离政治,师从戈德施密特(Goldschmidt)学习商法,他的学位论文就是围绕中世纪商业行会的历史下功夫的。他跟从迈岑(Meitzen)所做的农业史研究,同样属于完全非政治的领域。除了布鲁纳(Brunner)和贝泽勒(Beseler)的课程之外,马克斯·韦伯还修习了祁克(Gierke)的课程,不过,祁克对他后来政治观点的影响,与对胡戈·普罗伊斯(Hugo Preuss)的影响相比,可以说几乎没有产生任何重要作用。马克斯·韦伯反对一切“有机的”法律和社会理论,哪怕它们表现为最温和的形式;他也反对祁克与它们扯在一起的理论,尽管他承认祁克的理论作为法律史上的一项非凡成就意义重大。
在那段时间的韦伯书信中,只有一处着重提到了鲁道夫·冯·格奈斯特。韦伯赞美过格奈斯特的德国宪法与普鲁士行政法教程,称其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真正的杰作”,并且(不无保留地)记述说,这位法学学者偶尔也会评论当代的政治问题,偏爱“严格的自由派观点”。他作为自由主义国家法的律师,还抱有狂热的文化斗争信念,这对马克斯·韦伯可能也产生了强烈影响。格奈斯特肯定还使韦伯注意到了普鲁士东部各省那种引人注目的家长制自治体(patriarchalischen Selbstverwaltingsorgane)特性,这与德国西部各省普遍比较都市化的环境条件大不相同。另外,格奈斯特的比较法学方法论,某种程度上说,对韦伯后来的法律社会学研究可谓意义重大。但是,韦伯极不赞同格奈斯特那种自治制优于议会制的主张,而且后来明确采取了与之相反的立场。韦伯认为,单纯的地方性或全国性行政,与追求权力事业的政治,两者的高下犹如霄壤。仅靠良好的行政,绝无可能实现这个伟大民族的全球性政治目标。
因此,我们可以认定,唯一对学生时代的韦伯产生了意味深长且经久不衰的影响者,只有赫尔曼·鲍姆加滕。但是,鲍姆加滕并未深度影响到韦伯在具体政治事态上的立场。在这个领域,马克斯·韦伯往往明显地与这位满腹悲观情绪的忘年之交观点相左。鲍姆加滕以同样方式教导韦伯观察政治事件,并且同样刻板地认为这是自己的独门秘诀。尤其显而易见的是,对于政治领袖的成长和国民政治判断力的熏陶,他们两人抱有共同的看法,都认为这是一切政治现象的根本问题。他们都在研究政治制度的性质与被统治者政治成熟程度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在那个著名的“自我批判”中,鲍姆加滕把德国自由主义在1862—1866年间宪法冲突中的失败,连同自由派不切实际的教条主义政策,都归因于缺乏政治熏陶以及德国资产阶级各阶层产生不出有天赋的政治家。他强调了这种局面的历史原因。与特奥多尔·蒙森一样,他也呼吁要造就“毕生为政治工作”的人,而且要在贵族阶层中寻找这种人,如果说这些阶层实际上还空空如也,那就是因为“真正的政治生涯并不是资产阶级秩序的特性”。我们将会看到,马克斯·韦伯也一再论及德国社会结构中绝大多数群体的政治不成熟问题,并将其归因于俾斯麦统治的影响。他极为关注政治领袖的问题,反对传统自由主义的功绩原则,而是强调职业政治家作为现代大规模民主政治中的政治权力载体的重要性。
与鲍姆加滕就俾斯麦和德国自由主义的未来进行的热烈辩论,以及和柏林的同学们之间多方面的政治讨论,有助于韦伯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他父母家中的民族自由党传统,并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形成了独立的立场。当然,即便在早期阶段,他独立做出的政治判断也不同凡响,他在《反社会党人法》问题上的立场大概就是最清晰的证明。他父亲和鲍姆加滕都认为,这是一个必要的恶,但韦伯早在1884年就对这项措施产生了怀疑:“我有时喜欢相信,人人平等的权利高于其他一切,因此,把某些人投入牢房,还不如封住每个人的嘴更可取。”《反社会党人法》显然侵犯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自由主义原则,这激起了韦伯的正义感。当时他还坚称,他观察到了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和领导层都在发生彻底变化。尽管这在那时并不是准确的观察,但毕竟体现了一种对社会民主党的温和评价,摆脱了资产阶级的焦虑感,这成为后来韦伯特有的一种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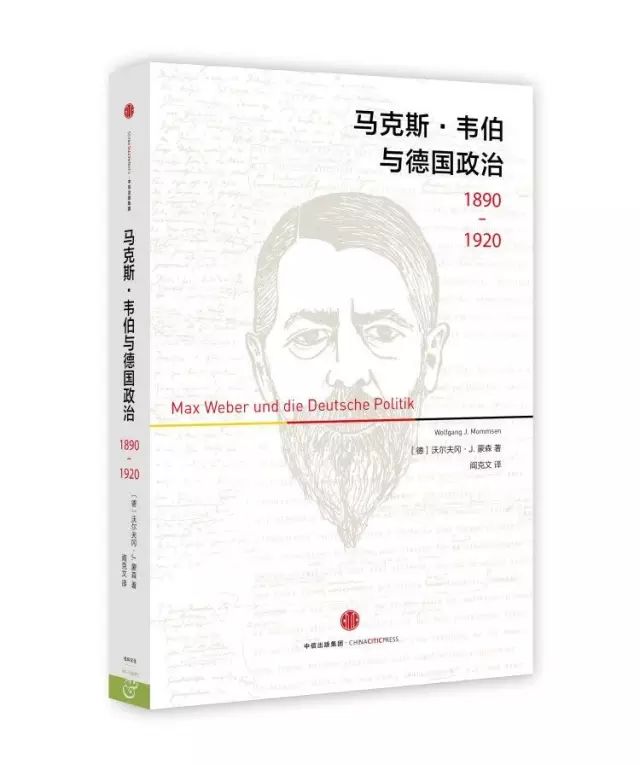
换句话说,韦伯也不赞同违背或放弃理想原则以迎合实际的现实政治。他在文化斗争期间毫不犹豫地坚持了自由主义立场,但与鲍姆加滕一样,他也支持为自身利益进行斗争,而不是把它作为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1887年俾斯麦再次给文化斗争的法律打折扣时,马克斯·韦伯断言,某些民族自由党人现在接受了这个事实——唯一的“政治”目标就是让反天主教的行动成为必须,尽管它的客观条件已经不复存在:“这种不声不响的‘和平’真是令人悲哀,无论如何,这是承认了一种不义,一种严重的不义,尽管人们如今都说,这场斗争只有出自我们一方的‘政治’原因。如果它在我们看来确实不是个良心问题而只是个权宜之计,那么我们就真的是由于表面的原因而亵渎了天主教人民的良心——正如天主教徒所断言。……因此,我们的行为并无良心,我们是道德上的输家。这是失败带来的最严重的问题,因为它阻碍着我们再也不可能继续进行这种要想获胜就必须进行的斗争。”
马克斯·韦伯通常也都会遵循父亲的左翼自由主义立场。他不满进步党对待所有财政与军事改革的消极态度。1887年他曾议论说,要是进步党能软化反对所有财政改革的绝对顽固态度,“那真是难以置信的明智”。他也不赞同进步党与80年代那种非常温和的殖民政策的对立态度。他希望,讨论一切与帝国的国际地位有关的问题,都应排除党派偏见。因此,他强烈反对把预算案和欧根·里希特领导下的进步党反复就国内政治挑起的争吵搅和在一起,并深为一再出现的斗争结果感到痛心。这些斗争给俾斯麦以国家主义的花言巧语解散德国国会提供了借口。后来,他比任何人都更严厉地谴责俾斯麦把预算案问题推到了国内政争的风口浪尖上。俾斯麦的政策“利用军事问题作为武器对付令人不快的反对党”,实际上导致这些问题变了形,“把简单易懂、直截了当的预算问题推到了一轮又一轮国内权力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严重损害了军队的利益,不过对俾斯麦倒是大有好处。”
马克斯·韦伯认为,进步党的政策纯粹是教条主义的。他断定进步党没有能力发挥建设性作用。因此,他看不出进步党未来能有什么成就。自由派普遍都抱着一个希望,即弗里德里希王储的政府会把国内政策导入自由主义轨道,鲍姆加滕和韦伯的父亲同样抱有这种希望,但韦伯相信,这是无稽之谈。德国的政党政治现状绝无可能为又一个“自由主义时代”提供框架。自由主义分崩离析的恶劣情形,事实上已经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性。韦伯鄙视进步党在这位王位继承人面前的“奴性”投机。他给赫尔曼·鲍姆加滕写信说,必须“完全否定这些人还能有任何建设性的政治行动,不然将造成自由主义的永久分裂,而且,自由主义将会同时遭到满脑子成见的狂热煽动家和盲目的俾斯麦信徒的损害。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期待着以往的团结因素及时从左翼那里产生出来并重返建设性的合作”。
我们已经知道,韦伯并不看重民族自由党人。最初他还曾在鲍姆加滕——后者在80年代越来越靠拢进步党——那里为他们进行辩护,但他逐渐认识到,民族自由党正在变得日益迟钝,特别在70年代先是本尼西森、继而又有许多其他出色的民族自由党领导人退出政坛之后。他不满他们越来越背离自由主义传统,那种自满自足的状态使他们转而成为单纯的国内政治现状辩护士。1887年,第二次法案通过、文化斗争结束时,他谴责民族自由党人“尽可能顺从地享受……‘我们拥有’的东西”,批评他们不肯思考不确定的未来问题以免自寻烦恼。早在1885年他就注意到,“这个党能不能再次赢得普遍信任是大可怀疑的。人的记性并不可靠,没有人还会记得这个党干出过什么业绩。”韦伯也不相信民族自由党如果不与进步党合作,未来还有什么生气,因此,进步党走下坡路也会损害到民族自由党。到80年代末期,韦伯对德国自由主义的未来已经极为悲观。他对德国政党政治的“总体颓废”哀叹不已,担心最后会是左右两翼的激进政党交替与中央党结盟支配德国的政治舞台,事实证明,这个预言是准确的。
原标题:《青年马克斯·韦伯和他的时代》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