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清末东北大鼠疫撕开的中西医之争
文 | 江隐龙
宣统二年(1910年)10月,一场浩大的鼠疫席卷了清朝的整个东北地区,并透过长城侵袭到直隶、山东等京畿征地。虽然这只是20世纪的第10个年头,但在后人眼中,这场最终造成6万人死亡的灾难已然是整个20世纪最严重的流行性鼠疫,没有之一。
这场鼠疫带给中国人巨大的创痛,但也造就了一位英雄:伍连德。在国势动荡、疫情危急的情况下,这位刚过而立之年的年轻人仅用4个月的时间就扑灭了这场举世震惊的瘟疫,让各国医学专家刮目相看。疫后,清朝当局召开了万国鼠疫大会——这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次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23次会议中有20次均为伍连德主持,伍连德对于中国乃至于世界鼠疫防控事业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东北大鼠疫平定后,摄政王载沣为表伍连德功绩,任命其为陆军少校、蓝翎徽衔并赐进士出身。但作为一名医者,伍连德的梦想却远不是封妻荫子。在此之后,伍连德奔走于全国各地,建立医疗卫生机构,组织医学专业组织,致力于收回中国失去已久的海港检疫主权,并在痛感西方医学界不了解中医的情况下与王吉民合著《中国医史》……而在鼠疫研究中,伍连德更是走到了世界前列。2007年,诺贝尔基金会官方网站公开了部分诺贝尔奖候选人资料,伍连德因为“在肺鼠疫防治实践与研究上的杰出成就及发现土拨鼠于其传播中的作用”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候选人提名,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走近诺贝尔奖的第一人”。
1960年,82岁高龄的伍连德溘然长逝。这位清朝的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北洋政府的北京中央医院院长、南京国民政府的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总监,除了功彪史册的抗疫大业外,还为中国留下了1所滨江医学专科学校(即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前身),20所检疫所、医院、研究所,包括中华医学会在内的数个医学组织以及三大本医学著作,其中便包括影响颇大的《中国医史》。
一位因抗击鼠疫获得世界认可的中国医生,维护中国检疫主权、筹建中华医学会、撰写《中国医史》,这样的故事似乎很难不让后人在景仰之余,高喊一场“中医崛起”。然而,历史却偏偏在此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东北大鼠疫
《大公报》上的论战
1913年“民元教育系统漏列中医事件”、1929年“废除旧医案”和1950年《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是中国近代史上公认的三次中西医大论战。但其实,中西医的第一次交锋早在东北大鼠疫爆发的同时,就在内地以《大公报》等媒体为战场轰然打响了。
《大公报》创刊于光绪廿八年(1902年),以“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为宗旨,向来以“敢言”著称。东北大鼠疫中,《大公报》多次刊发抨击中医的报道与时评,且言语中颇有挖苦,与中医界分歧已久。宣统三年(1911年)2月15日,《大公报》又在一则报道批评一位天津中医“聪明自恃中医所以误事者为此”;天津中医药研究会看到报道后立即派人调查,却发现该报道失实,立刻提出抗议。《大公报》虽然在第二天作出更正,但天津中医药研究会显然无法接受,并立即在《正宗爱国报》上发表了一篇《天津中医全体质问大公报函》:“贵报对于中医全体每多贬词,一似与中医有宿怨深仇也……今竟捏造谣言硬诬……按语竟谓(聪明自恃中医所以误事者为此),踹其心理,势非摧尽中医不止,中医何怨于贵报而忍出此残暴野蛮之手段也?”
作为“檄文”,《天津中医全体质问大公报函》从立场出发而少“就疫论疫”,而《大公报》则以质问回应质问,直接将话题引入鼠疫:“对于此次疫症中医是否确有把握医治?” 由此,双方的论战正式开始。
《大公报》力主西医,当时的西医尚未完成现代化,认为鼠疫能防而难治,这也成为《大公报》的主张。相较之下,内地各中医学派却多坚持鼠疫可治,《大公报》对此评论道:“无论那国的医生,对于此次的疫症,都是异口同音,都是说没有法子治,只有严严的防备一法。没想到我们中国的医生则不然了,一个人一个说法,这个说是寒,那个说是火,不是这个查出古方子来,就是那个得了新治法。总而言之,总出不了‘世间上没有治不好的病’这一句话,故此许多的热心君子,就乱传开了方子了,虽然这些位的热心可敬,到底这些位的知识也太可怜了。”
针对具体的药方,《大公报》则语多讽刺:“这种疫症,经多少西洋医生,用显微镜察看,实在是许多的虫子,在血管里作祟,不用说草根子树皮杀不死他,就是什么烈害的毒药,也杀不死他,岂有蓄点猫尿,用点人中黄,什么又加上点东壁土就好了?”“以相克之理言之,则鼠固畏猫,猫亦畏狗,若取演进之义,与其用猫尿,不如用狗屁。”
当时《大公报》所言的“猫尿治鼠疫”事实上也出自一则失实报道。不过早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华字汇报》上的确刊登过一个药方云:“鼠疫之毒焰……兹有普济子邮寄一方,谓用猫胆一个,暖酒冲服,立愈,盖胆能散郁去毒,猫鼠相克,而人以生方亦奇矣。”若《华字汇报》确有实据,那“鼠固畏猫,猫亦畏狗”的讽刺之语倒并非全然冤枉。

《大公报》
鼠疫期间,内地中医陆续公布了诸如神效复苏散、杀菌消毒丸、剂升麻鳌甲汤等药方,不过始终流于口头,未能送至抗疾前线并通过实效证明其疗效。《大公报》认为这些药方均为参照医书“虚揣悬拟而成”,以此指责中医“只能拿旧说敷衍,不能发生新理”,进而抨击中医们强作药方不过是因为利益相关:“此次时疫流行势极危险,五洲各国之医士无不懔懔危惧,乃我国一般刚愎自用者流,妄传方药强作解人,其自欺欺人,贻害曷堪设想。本报天职所在,岂忍默也不言,乃不意竟触本地铮铮佼佼诸医士之怒,因而布局设法以图报复,在诸君既为名誉所关,复为饭碗所系。”
或许诸多药方未能用于前线的确是“硬伤”,中医们的论点遂又转于医学角度的比较:“防疫一事,以学理上言之,西医固胜于中医。然事实上,恒有与学理相背驰者,试问东西洋医学专家对于疫症禁阻之手段,能否确有实在把握?日观东西洋防疫手段,可谓之能避而不能防,又何能言治,徒责问于中医,岂不太苛乎?”
以当时西医的发展水平,面对鼠疫的确亦难有效防治。不过东北鼠疫爆发后,除原在东北的诸多中医外,奔赴疫区的“援军”的确大多为西医,由此《大公报》进一步激将:“自东三省防疫事起,西医之前往疫地者,前者方扑后者又登,大有奋不顾身之概,而我国医生平时最会说古方,讲大话……及以重金招往疫地,迄无一应者,岂西医不爱命华医不爱钱乎?曰,此非不爱钱,爱命胜于爱钱也,此即华医之特色处。”
中医则言明:“防疫与治疫未可偏废者也,西医随云不能治,中医未尝不讲防(中国医书《素问》云,上工治未病,其次治已病,此即防病胜于治病之义也)。特是中国防疫之法不如西人之严者,其原因,由于西医不能治故不能不致力于防,一意严防亦救世不得已之苦心也……以纸上之防疫论,中医实不如西医,以事实上之消疫论,实善于西法,请征诸实验是非自明,强词夺理无用也。”
“西医不能治故不能不致力于防”一句或许有些臆断,但“请征诸实验是非自明”一句的确公允:中医们的医术及药方,终究要靠“征诸实验”证明其疗效。恰在此时,一位自长春“逃”入天津的中医张聪彝也加入了论战,并希望——或者说是挑衅——内地那些自信能扫平鼠疫的中医们能将“征诸实验”付诸实践:“试问鼠疫致死一霎那之顷,以吾国医药之迂缓,而谓能立刻奏效乎?如曰能也,二三君子何不束装赴奉一试其技,而乃于此间饶舌乎?”此言一出,内地中医亦大有愤慨者,北京名医丁子良甚至声称“三五日内商议妥恰即可见诸实行”,但最终未“束装赴奉”。

《丁公庆三事略》和《丁子良先生事略》
伍连德控疫与“西医东渐”
非常之时,东北与直隶、山东等处交通被封锁,内地医师未能“束装赴奉”未必便是《大公报》所言的“爱命胜于爱钱也”。而从实战来看,无论是内地中医还是滞留于东北的中医均积极参与到了抗疫斗争中——东北中医固然义不容辞,而内地中医不要薪水、义务救治者也不在少数。
就在《大公报》的论战白热化之时,《正宗爱国报》上也刊载了天津中医界的药方。初患鼠疫者可服“神效复苏散”,此方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瘟疫时中医所拟,曾“寄往沧州救活多人”,于此“将原方略为变通……一见头眩痛、恶寒、昏愦等症服此必效”。稍重者可服“杀菌消毒丸”,此方以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时疫中“保卫医院用之极效者”所用的药方为基础,“加减数药”所制。而“咳嗽、喘急、抬肩、咯血、神昏”等重症患者则当“速延医士诊治”,依王清任先生《医林改错》中的之解毒活血等汤,“十中可救二三”;再进一步的重症患者,用升麻鳌甲汤,“在十人之中仍可挽救一二”;而面对“转瞬即亡之危症”病患当服用生犀饮,“亦有得生者”。
从中不难看出,当时中医并未对鼠疫进行实地考量,而是针对鼠疫所传的病症,沿用古方加以应对,其研究也不可谓不细致。只是从之后既无后续治疗情况跟进,也无官方加以推广的结果来看,上述药方的疗效显然不尽如人意,反而应了《大公报》“这些位的热心可敬,到底这些位的知识也太可怜了”之语。
东北抗疫前线的中医,情况便更为惨烈。伍连德在抗疫中后期曾对参与防疫人员的死亡人数进行过总结,当地中医9人中死4人,死亡率为44.4%;而西医及学生29人中仅死1人,死亡率为3.5%。在万国鼠疫大会出具的《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中,不乏有中医为鼠疫病患望闻问切后即与病人一起死去的记录,如果将这些难以确算的实例加以计算,东北中医的死亡率只会更为惊人。
民间中医的战况如此,那伍连德作为中国医生中的翘楚,他的成果是否能为中医的正名呢?答案是否定的——伍连德虽然是“中国医生”,但他却不是“中医”,而是一位彻彻底底的“西医”。
伍连德祖籍广东,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是个正宗的“华侨”。伍连德从小接受西式教育,1902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直到1907年才接受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邀聘,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而此时伍连德的汉语说得甚至不如英语流利。

伍连德
东北大鼠疫横行时,伍连德临危受命,以瘟疫调查员的身份前往东北,并最终因接受过极好的流行病学、细菌学医学训练,又兼通法、德等国语言,对于防疫和协调外国侨民事务素有经验而被推举为总医官,总管防疫事务——朝廷对于伍连德的邀聘与启用非但与中医无关,反而是看中了伍连德的西医背景。
当时西医尚不能治鼠疫,伍连德抗疫依然以防控为主,通过交通管制、隔离病患、焚烧尸体等方式阻断传染源。相关举措之下,疫情很快迎来“拐点”,伍连德宣统二年(1910年)12月至东北,次年3、4月疫情已基本停息。在总死亡人数约6万的情况下,防疫人员的安全也基本得到保障——当然,因不接受西医流行病学理论而拒绝佩戴口罩的中医除外。
作为一名中国医生,伍连德东北大鼠疫中居功厥伟,其医疗理念、水平为欧、美、日等众多医生所不及,但伍连德本人却是一位实实在在的西医。而至于他日后所著的《中国医史》,更多是在欧美医学界对中医历史了解不足的情况下,从医学史的角度,以海外读者为受众,用英文撰写的著作。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中国医史》在1965年还被定性为批判“封资修”和“崇洋媚外”的对象,此番境遇虽有其特殊历史背景,但足以看出《中国医史》与中医医书的不同了。
整个东北大鼠疫期间,中医中不乏取义成仁的英雄;但从防疫与治疫的实效来看,中医面对鼠疫这种飞沫传染的烈性传染病束手无策,所做的贡献实在聊胜于无。中医中自也有借机发国难财者,这一类卑劣者失于人品,其污点不应由中医这一学科或职业承担。不过,中医在“前线”与“后方”渐受质疑、日显颓势的事实,已经基本宣告了中医在中西医论战中话语权的丧失。
后来数十年间出现的中西医论战事实上正是这一次论战的自然延续。1913年与1925年的大学规程中,中医完全缺席;1929年,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余岩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直到1950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将“团结中西医”作为共和国卫生工作三大方针之一时,会上还出现了如下感叹:“中医只有治疗,是没有预防的。现代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的进展,仅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但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医的主要特点是几千年文字理论毫无进展。而中医的优点,只是经验秘方”“中医理论玄虚的地方多,实效虽多却少统计,但偶然的例子亦多,未必尽然。中医实效有,而经验未必可靠,科学二字误解亦多。”
而这三句话的发言者,分别为陆渊雷、高仲山和叶劲秋,均为知名中医。可见自西学东渐后,以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寸关尺为理论基础的中医,显然难以与以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临床诊断学为特征的西医相抗衡;当西医现代化愈加明朗、而中医却依然止步不前时,中医群体本身也出现了深刻的反思甚至是否定,“团结中西医”背后,未免也沾上了“西医东渐”的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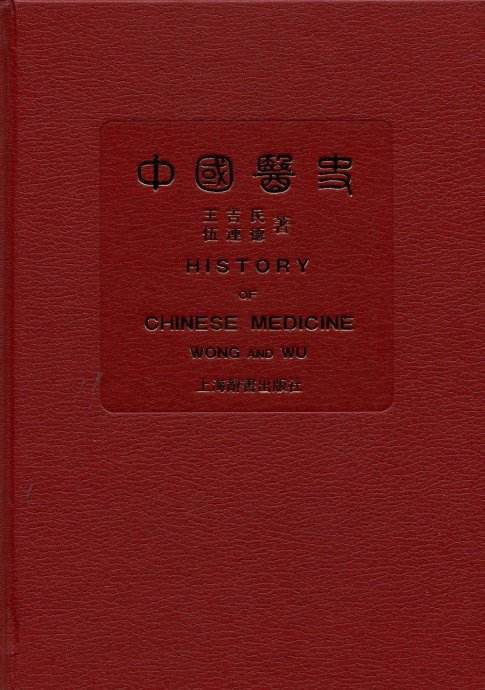
《中国医史》
未曾缺席的中医防疫
中医对西医的式微,应当放在中西文化碰撞的大背景下加以考量。传统中医正面“迎战”已经踏入现代化征程的西医自然毫无胜算,但这是传统医学面对现代医学之败局,而非中医面对西医之败局,更非传统中医面对传统西医之败局。
事实上,传统西医中的体液学说与传统中医的阴阳五行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传统中医依经络穴位施针灸,同一时代的传统西医则依月相星座为病人放血;甚至直到文艺复兴时期,霍恩海姆赖以挑战体液学说的精华理论也并没有本质性的改进。因此,中西医的划分意义并不大,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分野才是医学史上的真正进化,只是因为中医尚未现代化,而西医早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完成了对传统西医的自我更迭,中西医论战才会成为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论战的代名词。
从这一角度出发,便不能因为中医在东北大鼠疫中的失败而否定中医的意义。历史功绩一定要用历史本身去评判,同样是在1950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另一位中医袁平的发言便能代表很多中医所想:“中医数千年来作治疗工作,如果没有什么价值,根本早就不会存在了。中医在病理方面,诊断治疗方面,也都是累积的经验。”
那么,清末中医所谓的“中国防疫之法不如西人之严者”和陆渊雷所称的“中医只有治疗,是没有预防的”是否冤枉了中医?求实而论,传统中医在理论与实效两个层面,针对瘟疫究竟表现如何?要回答这一历史问题,就不能不将视线回归到历史本身——幸运的是,在瘟疫这个战场,中医从未缺席。
《说文解字》将“疫”解为“民皆疾也”,可见最迟在两汉,烈性传染的“瘟疫”便已从“疾病”中被区分出来。事实上历代中医对瘟疫的定义均有认知,《素问·刺法论》言“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症状相似”;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论瘟疫为“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直明清各医家更以“役”解“疫”,如明朝吴又可《温疫论》的“疫者,以其延门阖户,如摇役之疫,众人均等之谓也”、清朝莫枚士《研经言》的“疫者役也,传染之时,病状相若,如役使也”,均突出了疫“皆相染易”的特性。
瘟疫备受医家重视,源于其巨大的传播力与破坏力。唐朝孙思邈的《银海精微·天行赤眼》中言“一人害眼传于一家,不论大小皆传一遍,是谓天行赤眼”,这里的“天行”即为瘟疫别称,而“一人害眼传于一家”已然是最轻微的注解。宋朝庞安时《伤寒总病论》言“天行之病,大则流毒天下,次则一方,次则一乡,次则偏一家”,而这种“流毒天下”的瘟疫往往能使得社会“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直到清朝乾隆年间,师道南尚有一首《死鼠行》描绘当时横行的鼠疫,其中“鼠死不几日,人死如圻堵。昼死人,莫问数,日色惨淡愁云护。三人行未十步多,忽死两人横截路”人间惨剧,实令人不忍卒读。

孙思邈邮票(右上)
那这种动辄令人“千户灭门”的瘟疫又何以发生呢?各医家对此虽解释不同,但大体可以归纳为“气候不正”四字。《素问·刺法论》言“升降不前,气交有变,即成暴郁”也即气候反常是瘟疫发生的直接因素,《吕氏春秋》《周礼·天官》《公羊传》《淮南子》中的记载与此亦大同小异。《诸病源候论》对此解释更为详细:“时行病者,是春时应暖而反寒,夏时应热而反冷,秋时应凉而反热,冬时应寒而反温,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病无长少,率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瘟疫源于气候反常、寒暑错位,其致病因素便非“内伤”而是“外邪”,这些“外邪”除了传统的“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邪”外,还有如王叔和的“时行之气”、巢元方的“乖决之气”等“戾气”“温毒”。
病因既明,与之对防治方法自然也应运而生。《素问·刺法论》言:“黄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歧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这一段文字在中医理论系统中影响深远,中医防疫的两基本原则——“正气存内”与“避其毒气”,由此确定下来,千古不易。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正气存内”可视为提高抵抗力与免疫力,从而使“外邪”无法侵入;“避其毒气”则是远离病原体与传染源这些“外邪”。两者的重点均在“防”而非“治”,这倒也符合《素问》中“不治已病治未病”之论。《素问》中继而言道:“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己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这里所针对的虽然是所有病症,但足以看出中医确实有预防理念了。
“正气存内”之法,有修身养性、藏精固本、节制饮食、服食药饵等法,中医甚至发明了种痘术,这在现代医学发展史上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而“避其毒气”之法,则依靠注意卫生、消毒杀虫等法隔绝“外邪”。张仲景《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中梳理了三大“外邪”之源:“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而“内”与“外”的辩证,明朝吴又可于《温疫论》中有一段颇具辩证色彩的表述:“若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又不拘于此矣。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邪不胜正,未能顿发,或遇饥饱劳碌忧思、气怒,正气被伤,邪气始得张溢。”
在“不治已病治未病”理念面前,陆渊雷“只有治疗,没有预防”之论似乎对中医有所冤枉。不过,医书中的种种表述毕竟过于原则化,中医防疫的虚实毕竟还要从“正气存内”与“避其毒气”两个具体原则的实行情况来分析。

《黄帝内经》
中医防疫:“正气存内”篇
“正气”一词本出于《素问》,于是在此书中,也的确记载了一种最为古老的“意念防疫法”,其法云:“欲将入于疫室,先想青气自肝而出,左行于东,化作林木;次想白气自肺而出,右行于西,化作戈甲;次想赤气自心而出,南行于上,化作焰明;次想黑气自肾而出,北行于下,化作水;次想黄气自脾而出,存于中央,化作土。五气护身之毕,以想头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后可入于疫室。”
而另一种同样古老而且“福泽绵长”的方法则是取媚鬼神。虽然中医将瘟疫归结为“气候不正”,但在科技水平低下的时代,上至朝廷下至民众往往容易在恐慌中将瘟疫认定为鬼神作祟,《释名》中便将“疫”解释为“役也,言有鬼行役也”。既然瘟疫源于鬼神,那通过祭祀仪式取媚鬼神就成了自然选择。周朝流传下去的驱疫仪式“傩”几乎贯穿整个古代中国,甚至大力禁巫的两宋都不能“免俗”,每年腊八前一日都要举办壮观的“大傩仪”以求身体健康、无疫无灾。而在民间,除去小型驱疫仪式外,通过佛教的抄经诵咒和道教斋醮符咒固自身“正气”的活动就更不在话下。
通过构思“五气护身”来防疫显然是天方夜谭,不过医疗技术的发展亦有其从荒蛮走向文明的过程,《素问》成书甚早,至唐宋明清时期,纵然是最不识医者也不可能仅靠“想头上如北斗之煌煌”就敢出入疫室。而取媚鬼神之事则更接近于古人面对瘟疫的群体性应激反应,不宜将其归为中医之法。在祛魅的基础上,比较正统的“正气存内”法大体包括藏精固本、节制饮食、调摄情志、运动健身、服药种痘五种。
藏精固本,以节欲为主。《素问·上古天真论》言“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於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千金方》中亦有“态情纵欲,命同朝露”之论,可见中医自古认为纵情酒色会导致体制衰竭。元代朱震亨在此基础上更提出“阳有余阴不足论”,提倡“不见所欲,使心不乱”,因为“温柔之盛于体,声音之盛于耳,颜色之盛于目,馨香之盛于鼻,谁是铁汉,心不为之动也”。
节制饮食即讲“有节”,亦重“均衡”。《素问》反复强调脾胃的重要性,“五脏者皆享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本也”,若饥饱无常、暴饮暴食,则会损伤脾胃进而伤害“正气”。对于饮食有节,历代医家均有其论,如张仲景提倡“忌冷食、勿贪食”;孙思邈提倡“先饥而食,先渴而饮”,且最好保持“饱中饥、饥中饱”的半饥饿状态。
调摄情志,大意指保持精神安定。《灵枢·口问》言:“夫百病之始生者,皆生于风雨寒暑,阴阳喜怒,饮食居处,大惊卒恐。则血气分离,阴阳破败,经络厥绝,脉道不通,阴阳相逆,卫气稽留,经脉虚空,血气不次,及失其常。”明朝万全认为“心常清静则神安,神安则七神皆安,以此养生则寿,段世不殆”;清朝温病学家叶天士、熊立品则认为“颐养工夫,寒喧保摄,尤加意于药耳之先”,而若能以此达到正气充实”的程度,则病气、尸气无从侵入”,可见中医眼中调摄情志对于防疫的重要性。
运动健身亦是中医传统手段之一。马王堆出土的《导引图》中就绘有徒手运动和利用器械运动图样,华佗根据“流水不腐”的道理创造了“五禽戏”更是防疾体操的代表,在此之后,太极拳、八段锦、口津功、健身桩功,以及道家大小周天功、气功、导引按摩术等多种健身运动,也都为中医运动健身术的组成部分。

八段锦
不过,藏精固本、节制饮食、调摄情志、运动健身等依然流于理论,且难以确定其防治瘟疫过程中的因果关系。相比之下,面对瘟疫最有说服力的是服药种痘之法,因为服药种痘因果性最为明显,能够直接通过病患是否被治愈、易感人群是否达到预防效果来评价其疗效——服药种痘的效果,几乎可以视为中医防疫效果的最佳例证。
先说药。中医防疫治疫的药方,早期以张仲景《伤寒论》最为经典,其中计397法,130方。晋朝医家葛洪在《肘后方·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中亦有20多种防治疫病的方剂,大部分是预防药方。与此相应,历朝在“时疫大作”时,朝廷一直也将施医散药作为控制疫情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历朝五行志中关于疫情往往对医疗机构、发廪蠲租、收容埋骨等多加笔墨,而对疫情中出现的药剂一笔带过,或缺乏对药方的描述,或少通过药剂“活人”的记录。至于纪实故事如《太平广记》,关于民间药剂又多为“有疾得药者,无不愈”的模糊描述,甚至不乏“诵经四十九遍,李氏寻愈也”的“奇迹”。
平心论之,民间传说中的“医人无数”与史册中瘟疫期间“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之间,存在着极大冲突。在“死者十有五六”“户灭村绝”“流尸无算”之语史不绝书的背景下,“医人无数”的人数上限如何考量、既有此效为何不被推广,以及瘟疫频频为何不被控制就成为一桩桩难以解释的公案。
相对于药,中医中的种痘术值得大书特书。现代免疫学证明,传染病痊愈后,大多机体会对该病原体产生抗体,以后再遇到同类病原体即可受到保护不再感染,这便是疫苗的原理。不过,疫苗并非现代医学的产物,而源于中医古老的种痘术。
种痘术源于中医“以毒攻毒”“以类治之”的朴素理念。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指出“疗狂犬咬人方,仍杀所咬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这一情形与巴斯德研制狂犬病疫苗的过程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医治痘疹与天花等疾病时,中医发现这一类疾病“终身但作一度,后有其气不复传染焉”,于是产生了通过主动感染轻微病症并痊愈,进而获得免疫能力的尝试。最初的种痘术为旱苗法,即将患者的痘痴研粉吹入健康人鼻中使其感染的方法;此外又发展出了水痘法、痘浆法、痘衣法等方式。明清时期的种痘术尚不尽成熟,一旦失败便有如“一儿布痘,痴中生蛆,痴破蛆流满床”的惨剧发生,不过从时人的评价来看,种痘术的效果应当给予肯定。清朝张琰《种痘新书》中说:“经余种者不下八九千人,屈指纪之,所莫救者不过二三十耳。”康熙在《庭训格言》里写道:“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尝记初种时,老年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知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这两份记录,从医者与患者两个角度说明了种痘术的成功率与实效。
中医种痘术后辗转传入欧洲,为更先进的牛痘术打下基础,清朝后期邱熹又写成《引痘略》,将牛痘术引入中国。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天花被消灭,这背后便有中医种痘术的启蒙之功。

痘衣法
中医防疫:“避其毒气”篇
如果说“正气存内”诸术多可由医者与患者自力实现,那“避其毒气”之法有时则需借助公共力量的支持干预。《素问》虽言“不治已病治未病”,但医家所治自当包括“未病”与“已病”,针对瘟疫,自然也包括“未疫”时之法和“已疫”时之法。
“未疫”时的防疫主要在于卫生消毒,其方式不成体系,但可以用古书中散落的记载中管窥一二。如《礼记·内则》载“凡内外,鸡初鸣……洒扫室堂及庭”;清朝温病学家王士雄《随息居重订霍乱论》载“住房不论大小,必要开爽通气,扫除洁净”,均指明家居当保持卫生。《周礼》言“炮生为熟,令人无腹疾”;孔子要求“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则是指饮食要保持卫生。而至晚在北宋,勤于沐浴已成民俗,尤以江南为盛。当时王安石“衣逅不浣,面垢不洗”,吴冲卿还要相约“每一两月即相串洗沐定力院家”,即定时至公共浴室沐浴,这以是对个人卫生的重视了。除去家居、饮食、沐浴等私事,通过不少民俗也能看出古代民众的防疫意识。元旦时饮屠苏酒、放爆竹、投麻豆;端午时制香囊、插菖蒲、燃艾叶;重阳时钦菊花酒、佩茱英、食蓬饵,这些习俗自是前人从医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避疫方法,因广为流传而逐渐演变为民间习俗,在不经意中自然也会各依其原理、药性起到一定的防疫作用。
不过有些习俗非但无法防疫,反而有助于瘟疫传播,其中最典型者莫过于病患子女通过尝粪以尽孝道。《梁书·庾黔娄传》中有“时易(娄父)疾始二日,医云:‘欲知差剧,但尝粪甜苦。’易泄痢, 黔娄辄取尝之”的故事,这一事件被收入《孝行传》,可见尝粪之举备受时人称赞。直到清朝,依然有刘时华在其父病危时“以手承痰尝之”以确定病情有无好转可能的记载,在瘟疫面前,这些习俗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
相比于个人,历代朝廷在公共卫生方面也颇有关注。《周礼》中已设有专职卫生专员,如“庶氏掌除毒蛊……嘉草攻之”“ 薙氏掌杀草”“翦氏掌除蠹物……以莽草熏之”。《管子·禁藏》载“当春三月,荻室摸造,钻遂易火,抒井易水,所以去兹毒也”,也即安排专员除井中污泥以防疫去毒。秦国依“商君之法,弃灰于道者黥”,由此还引出了沈家本“此法太重,恐失其实”的疑问;至宋朝,公共卫生立法已经颇为细致,春初时官府会“街道巷陌,官府差顾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顾船只搬载乡落空闲处”,通过清整沟渠保障城市环境;而对于恶意破坏环境者,则以律法严加管理,如“辄将粪土瓦砾等抛入新开运河者”,将“杖八十科断”,其刑罚力度之大,几近于售卖过期成药与伪劣药物。

庾黔娄:尝粪忧心
“未疫”时有所防,“已疫”时自然亦有所隔。中医对疫时的卫生观论述不少,至少在清朝时已极为全面。如熊立品《治疫全书》提出的“四毋”原则:“瘟疫盛行,递相传染之际……毋近病人床榻,染其秽污;毋凭死者尸棺,触其恶;毋食病家时菜,毋拾死人衣物。” 刘奎在《松峰说疫》言及“识观入瘟疫之乡,是处动有青蝇”,由此提出“逐蝇避疫法”,均是切实之举。
“毋近病人床榻”“毋凭死者尸棺”等语,为的是远离传染源。而对于朝廷来说,就能够通过公共政策集中处置作为传染源的病患。《秦简·法律答问》中所记载的"疠者有罪,定杀”自然有违人道,而西汉元始二年(2年)大疫中,汉平帝便通过“空舍邸第,为置医药”的诏令隔离疫民。至晋朝时,出现了“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疾,百日不得入宫”的规定,虽然此举在当时被嘲为“不仁”,但的确是合乎医理的做法。南北朝时期,北魏和萧齐分别设立了收治病患、疫民的医疗机构;唐朝又设疠人坊以隔离传染病人,且“男女别坊,四时供承,务令周给”,医疗供养之制已颇为完善。
中国古代医疗机构及公益机构以两宋为盛,而至明清式微,而即便是清朝亦不乏隔离机构。清人入关前下逢天花流行,遂设立专门的“避痘处”,并屡次驱逐、隔离痘疹患者,如顺治二年(1645年),曾有令“凡城中之民出痘者,即行驱逐。城外四十里东西南北各定一村,使其居住”,这里“使其居住的村庄,大类于唐朝的疠人坊。
传染源除病患外尚有尸体,这一点历朝早有认识,并每每诏令各地掩埋尸体。有唐一朝,关于埋骨的诏书极多,仅《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四》中便收录了唐高祖《收瘗隋末丧乱骸骨诏》、唐玄宗《埋瘗暴露骸骨敕》、唐肃宗《收葬将士及慰问其家口敕》和唐代宗《收瘗京城骸骨诏》四种,其中《埋瘗暴露骸骨敕》有“如闻江左百姓之间,或家遭疾疫,因此致死,皆弃之中野,无复安葬……宜委郡县长官严加诫约……其先未葬者,即勒本家收葬”的命令。宋朝时朝廷每于灾害过后招募僧人掩埋尸体,以度牒为奖励,僧尼凡有牒者得免地税、徭役,相当于朝廷以税收承担埋尸之资。之后,宋朝更设立专门的漏泽园,也即官办公墓,用于安葬无力承担丧葬费用的死者。
漏泽园之名,取“泽及枯骨,不是有遗漏”之意。从含义上来看,宋人与前人的动机未必完全是为了预防疫病,但朝廷大规模埋尸多发生于疫后,此举为阻止瘟疫传播和新瘟疫的爆发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是不可质疑的。
以上种种“避其毒气”的方式与政策,虽然大多不出于医书所谋划而源于朝廷政令,但中医这一概念理当置于宏观历史的框架下考量,因为朝廷作出相应政令时,其思路一定源于当时的认知尤其是医学理论。否则,“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疾,百日不得入宫”的这种有违仁义的命令便不可能出现。

漏泽园墓志
东北大鼠疫的疑问
通过对“正气存内”与“避其毒气”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医传统中并不缺乏对瘟疫的认知与基本的卫生常识。中医早于欧洲发明种痘术,以至成为后世疫苗的滥觞;中医在望闻问切的同时也极为注意隔离传染源;甚至历朝历代还不乏有关于公共卫生和疫情处理的政策。也正因为此,清末大鼠疫中中医的表现才更令人困惑。
论及“正气存内”,几千年来积累的“可以立救人命“的无数辟瘟之方在鼠疫面前毫无效果;明清时中医已经发明了种痘术,然而东北大鼠疫蔓延至京师后,外务部尚需电咨驻奥公使“在维也纳购买避疫苗浆十万服,即日运华,并聘定西医,无论官民绅商有愿预用此苗以防身体者,可到民政部领取凭据,即当指示地方官前往受种。”而且还需要遍贴劝种避瘟浆告示,以化解民众的排他之心。
论及“避其毒气”,熊立品们力倡的“四毋”原则显非共识,面对疫情,拒绝佩戴口罩成为中医死亡的最重要原因,以至于伍连德感叹:“我国医学与防疫一道, 素欠讲究, 浸至蔓延, 死亡无算。而当时中国的医界, 凡遇病症, 多不知其病原, 如时症、疫症、传染病等症, 究以由何发生及应如何预防之法, 莫不愕然无以应。”
中医自己不欲隔离,清朝当局采用隔离、焚烧等方式防疫反而被民众指责。与天津中医界关系较好的《正宗爱国报》就指出:“若一遇瘟疫,即事张惶,非圈禁,即弃置,是已病者万无生理,未病者亦必遭劫。不但少数之患疫者无一生活,即多数之不患疫者,亦必随之同死,天下有此等防疫治疫之善法乎?”事实上如果不是伍连德当机立断,及时遮断的东北通向内地的交通,直隶、山东一带恐怕如东北一样会变成人间炼狱,而内地民众面对鼠疫尚且不及,又何来“闲情”抨击西医的隔离制度呢?
问题出来了:为什么种种理念与实践,在清末东北大鼠疫中或完全失效,或干脆不见其踪迹?将这一切归于知识断层显然不合史实。而且以中医发展的脉络来看,明清时期中医尤其是温病学派日趋成熟,不仅出现了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四大温病学家,更针对瘟疫病患的临床证侯发展出了“卫气营血”与“三焦传变”理论。证候,大体是指中医通过望闻问切所获知的疾病传变规律。叶天士将疫病传变过程区分为卫分证、气分证、营分证和血分证四过程,吴鞠通则划为上焦证、中焦证和下焦证三过程——这些理论的诞生时间与东北大鼠疫爆发时间相距不过百年上下,又皆有知识断层之理?
另一个猜测,是医书与史籍勾勒的中医史,其实是一种理想状态,将这些散落的理想状态拼缀出来的历史,一定不是真实历史。从《素问》到《治疫全书》,其中提到的理念、原则、方法,有多少被后世医家所吸纳、落实甚至在此基础上创新?如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初步形成的隔离理念,清末中医居然不以为然,书籍中的“理想状态”与时人态度中的“事实状态”之间的差距,或许正是中医文字与现实差距的源头。

叶天士
如果这一猜测成立,便衍生出了更深一步的问题:中医医书传承之久、资料之丰可谓举世罕见,那后世医家在如此丰富的经验之谈面前,为何又往往裹足不前,甚至不以为意呢?答案很可能是这样的:中医理论的确能自洽,但毕竟只是哲学层面上的自洽。无论是“气候不正”的解析,“不治已病治未病”理念,“正气存内”“避其毒气”原则,还是清朝才发展出的“卫气营血”与“三焦传变”理论,都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证伪。后世医者有实践中只能如“神农尝百草”般一一尝试,有用者留下,无用者删除,而在变量极多、规律不明的情况下,经验医学的累积之路自然具有极强偶然性。
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证明:任何一个形式系统,只要包括了简单的初等数论描述,而且是自洽的,它必定包含某些系统内所允许的方法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的命题——中医理论的困境,正在于此。
然而,中医理论虽然无法证明与证伪,但中医防疫的实效却可以通过史籍对于瘟疫结果的记载去逆推。从《史记》记载的秦王政四年(前243年)“天下疫”始至1949年,中国历大疫约500次,瘟疫死亡的人数并没有随着中医学发展而整体呈减少态势,直到西医引入、现代卫生体系的建立,中国防疫事业才有所改观。中医在中西医论战中每每陷入危局,其根源在内,而不在于外。
余岩在《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认为废止中医有四条理由,也绝非危言耸听:
“今旧医所用者,阴阳五行六气脏腑经脉,皆凭空结撰,全非合实,此宜废止,一也。
其临床独持桡动脉,妄分一部分之血管为寸、关、尺三部,以支配脏腑,穿凿附会,自欺欺人。其源出于纬侯之学,与天文分野,同属无稽,此宜废止,二也。
根本不明,诊断无法,举凡调查死因,堪定病类,预防疾疠,无一能胜其任,强种优生之道,更无闻焉。是其对民族民生之根本大计,完全不能为行政上之利用,此宜废止,三也。
人类文化之演进,以在绝地天通为最大关键,考之历史,彰彰可按。所谓绝地天通者,抗德而崇人事,黜虚玄而尚实际也。(北伐后)方破除迷信,废毁偶像,以谋民众思想之科学化,而旧医乃日持巫祝纬之延以惑民众;政府方以清洁消毒训导社会,使人知微虫细菌为疾病之源,而旧医乃日持其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等说以教病象,阻遏科学化,此宜废止,四也。”
而当时中医的自辨清白之论为:一是中医有治疗实效,二是废止中医等于禁绝国粹学术,三是废止中医将影响社会稳定。这三条理由,后二者殊为牵强,而“有治疗实效”五字在已经接受现代化洗礼的西医面前,也着实有些苍白无力了……

余岩
结语
不过再回头看袁平的那句话,似乎仍值一辨。“中医数千年来作治疗工作,如果没有什么价值,根本早就不会存在了”——这句话是有理的。作为经验科学,中医在科技水平不够发达的时代的确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中医在试错的过程中积累出的药方,的确有反复利用的价值,其相生相克的关系也为日后现代医学累积了大量素材。有了这些有实效的药方,就更能鼓励民众“信医不信巫”,从这一角度看最朴实的医学也比最“全能”的神鬼要优越。民国中医们声称的“中医有治疗实效”并非粉饰,因为这一功绩早已溶入了历史。
在特定的历史时代下,中医需要在看似无序的世界寻找甚至构建因果关系,给后世的医家与患者以逻辑思辨能力,哪怕这种逻辑出了错,也远比没有逻辑要强。而且一旦后世开始了现代化进程,中医数千年积淀的素材就能加以运用,青蒿素的发现正是这一现代化的成果。
中国凭借千年帝制延续了漫长的文明,这不代表帝制可以原封不动地延续于21世纪;中国人凭借朴素的传统中医度过了漫长的岁月,这自然也不代表中医不加现代化能满足21世纪人类的需要。现代化是中医唯一的出路,而那些无法证明与证伪的理论只会让中医愈加远离科学的圣坛。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