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文学访谈 | 杨知寒 × 梁海:写作就是跟自己较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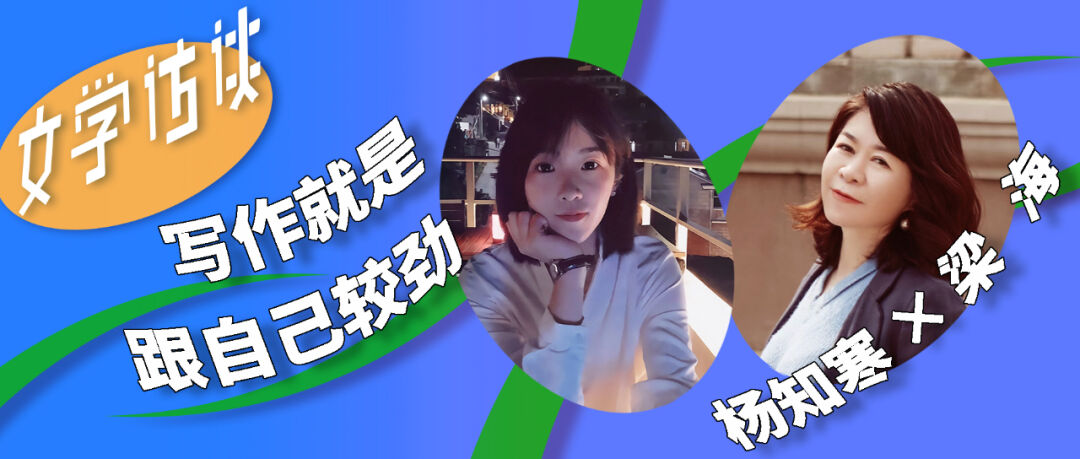
Photo by Dusan Kipic on Unsplash
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24年4月号
写作就是跟自己较劲
杨知寒 × 梁海
梁 海:知寒你好,前不久你的短篇小说集《一团坚冰》获得了第六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奖,首先向你表示祝贺。
杨知寒:谢谢梁老师。
梁 海:当时在颁奖典礼上,你声称没有想到能获奖,“可能还得回去想一会儿”。(笑)现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淀,能够谈谈你的“获奖感言”吗?
杨知寒:其实回去反而不想了,应该说怕想。觉得一切都很像梦,既然像梦,想也想不清楚,就放在那儿吧。每次登台说感言,会不知道说什么,好像只有谢谢是想表达的,但“谢谢”两字太简短,也包含太多,不可能真这样表达,于是想了个办法,任大脑放空,简单说点儿站在台上当下真诚的感受。那天也是这样,只不过那天我放空的时间,有点儿长。
梁 海:马伯庸在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给《一团坚冰》的授奖词是,“如刀旁落雪、寒后舔门,她以冷峻犀利的笔触将故乡冻结,然后退开一步,用舌头轻舐,温热的血肉粘于冰冷,一动则触目惊心,痛裂深切”。我认为,这一评价特别形象,又特别贴切,荒寒和残酷可以说是你作品的美学底色,透出一种与你的年龄极不相符的沧桑感。
杨知寒:这个形容简直听着都疼,像我多有勇气似的,应该不是。写的时候不会预期,会有怎样的效果,能让人看到这里很打动,还是很痛苦,没有准备。只是当我对一个人物和他的命运产生了信任,在这一段写作的过程里,我们灵魂伴随,能体验到他的感受。像一个人在风暴中心,其实会有点儿麻木,别人觉得很惊险很恐怖,而身处其中的人,是无暇感受的。他要做事,他要完成自己的目的,我在他的身上,陪他走在路上,我们一起走到小说的最后一个字。
梁 海:我最开始关注你的作品是从《上海文学》开始的。二○一八年《上海文学》“新人场特辑”刊发了你的短篇小说。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你的第一部纯文学作品。只是惊异于一位青年作家居然叙述如此老道,收放自如,又带着一股子凌厉和冷峻。之后,在各类文学刊物和各类文学排行榜上越来越多地看到你的名字,一篇篇作品看下来,对你了解更多。在我看来,《黄桃罐头》是你文学创作中具有非常意义的一部作品,其中讲述的家庭关系、亲情伦理一直绵延于你的创作中,你也曾说这部作品让你的文学道路有了新的方向走。能够具体谈谈这部作品吗?
杨知寒:《黄桃罐头》是一个家里亲人的故事,在小说里是故事,在生活里只是我对一个不太熟悉的长辈的零散的记忆。只有这篇小说,是我在一天内完成的,再实现不了这样的效率,觉得它很可能不是我的小说。它属于是给我的一把钥匙,在那天帮我同时打开了几道门。
梁 海:这个说法很形象。的确,很多优秀的作家都会因某种特殊的机缘获得一把打开文学之门的钥匙。我记得阿来说过,他在创作《尘埃落定》之前,已经三四年没有写小说了。在某个雪天的清晨,他听到窗外的画眉鸟叫声,于是有了想写点东西的冲动,他打开一台旧电脑,以当下情景为原型写下了《尘埃落定》的第一行文字。在《尘埃落定》之前,阿来也创作过很多文学作品,但是,在我看来,是《尘埃落定》让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学之路的钥匙。从这点来看,《黄桃罐头》也是打开你文学之路的钥匙。在此之前,你也写了不少网络文学作品。可以说,在进入纯文学写作之前,有着网络写作的前史,相继发表了《沈清寻》《寂寞年生人》等作品。那段时间正好经历了你大学刚毕业的一个阶段。那时你好像并没有着急找工作,而是专注于网络文学写作,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杨知寒:单纯是不想上班,清楚自己的性格,不擅长合作。所以如果有可能写作,就想继续下去。当时的写作非常青涩,也没出路,更实在的想法就是别在家里啃老。能写写一点儿,赚上收入,养活自己再说。
梁 海:你从网络文学转场到纯文学领域非常丝滑,似乎是一次无缝对接。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你的网络小说并没有大红大紫,但在纯文学领域却大放异彩。
杨知寒:这是个客气的说法了(笑)。不是没大红大紫,是根本没什么人看。可能我写得还不太像网络小说,严肃不够严肃,通俗不够通俗,有一阵也想,是不是浪费了一些时间?后来想法转变,两年的网络写作,不是浪费,或是准备的一种。两年的摸索,让我明白什么是自己想要的状态,不止写作,还有生活中想要的状态。合该如此,寂寞锻炼人的心性,更能体谅别人的感受和境遇了,这给我帮助很多。
梁 海:其实,近年来受到关注的青年作家,辗转横跨多个写作平台和媒介进入文坛视野的“出道”方式已成为常态。对此你是怎么看的?
杨知寒:有些阶段里有的路就是走不通的。不是路的问题,也和走的方式关系不大,而是阶段不对。我想,能及时意识到转化的需要,就是好事。
梁 海:你的小说取材不少以一九九○年代为背景,书写上一代人的故事,也就是黄平老师所说的“子一代”视角。实际上,一九九○年代已经成为近年来文学东北叙事的一道“流行风景线”。包括班宇、双雪涛在内的不少“八○后”作家,他们书写一个时代的落幕,不仅是东北作为“老大哥”的衰落,还有东北人的那种自我优越感、自豪感,以及相信奋斗和努力可以有更好的生活,明天是会越来越好的那种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精气神”的溃败。这些书写带有创伤记忆的性质。美国学者凯西·卡鲁斯提出创伤代际传递的观点,即创伤亲历者的延迟性记忆,会通过各种途径传递给他们的“子一代”,由“子一代”代为讲述。可以说,一九九○年代恰恰正是班宇、双雪涛等“八○后”作家青少年时代的创伤记忆。由此,我想到,你出生于一九九○年代的中期,你的青少年时代已经度过了那段历史阵痛期,那么,你是从什么角度考虑书写一九九○年代的东北呢?
杨知寒:我看到的属于一代人的骄傲的部分,已经稀少。和成长环境有关,看到的更多是属于个人的挫败、失意,故事一般会和具体人物的性格挂钩,较少写及一个庞大的环境或时代。我对他们更有印象的时候,该是千禧年后,我已经上学,父母都还年轻,将将三十岁。他们工作忙碌,陪伴我的时间很少,我常是默默观察,把不懂的事情埋在心里,记住了一个个时刻的“不懂”。成年后,它们被挖掘,与我的生活再作对照,有了新的理解。
梁 海:你讲得很好。的确,每一位作家的书写和记忆都与他(她)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息息相关。我最近正在参与张学昕老师主持的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有关于作家的写作发生。每一位作家,乃至每一篇作品都有着不尽相同的写作发生机制,你是否能就你的一两部作品谈谈你的写作发生?比如《一团坚冰》。
杨知寒:《一团坚冰》这篇小说和我其他小说的创作过程有些不同。吸引我去完成表达的不是具体的人物、具体的情节,而是一处场景的萦绕。我甚至没经历过那样的场景。它存在于我的脑海,即一片热闹的有点儿失序的午夜环境、网吧里的点点光亮、陌生人间冷淡的距离、压抑的情绪……种种元素糅合到一起,构成这篇小说青蓝的底色。我是从感觉里得来这样一篇小说的。记得当时和现在一样,也是元旦将至,我在暖屋子里感受着冬天,觉得自己走进了天域网络世界,就是小说里那个地下室。
梁 海:《一团坚冰》中的“李芜”给我印象很深,我注意到你的一些小说中都有一个叫做“李芜”的女性。
杨知寒:随便起的名字,听着顺耳,又给它编了不随便的来由。李是大众姓,芜是小众名,希望这些我喜欢的女孩儿都有普遍的由来,都有特别的个性。希望她们看着落落寡欢,似乎和哪儿都不兼容,但生命力强,扎哪儿都能生长。
梁 海:你的很多小说人物都有生活原型,我认为这些“原型”并不是为了还原生活原本的样子,这些“原型”隐射着你的主体意识。其实,任何一个作家的深层意识里都不同程度地潜藏着特定的“心理原型”,而生活中的人必然要经作家心理图式的同化后才能成为艺术形象。所以,我想问的是,你在小说的生活原型中寄予着怎样的“心理原型”?
杨知寒:也许如您所说,许多小说里都还有个人意识的痕迹,或深或浅,我想那大概是作者目光的投射,属于“我”的注视,人是能感觉到被注视的感觉的。这种心理原型我没法说清楚,可能说清楚了也大失趣味。小说应该保留一点玄虚感。
梁 海:我觉得你的小说取材很广,有《大寺中年无雪》《瑞贝卡》《故事大王》等青春题材、童年旧梦,有写马戏团的《虎坟》,有写批发市场的《百花杀》,有怀旧浪漫的《水漫蓝桥》,有游戏背景的《一团坚冰》,等等,这些故事有的取材于你身边发生的真实事件,有的是你比较陌生的题材。由此可以看出你未来创作的巨大潜质。面对这些你熟悉的,或不熟悉的题材,你是怎样处理真实与虚构、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关系?
杨知寒:即便是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身份,人与人之间的感受差异,不会太相左。我一直这样相信,所谓感同身受,如果真的抵达了身受,感同是能够得到的体验。每个人的素材获取总是有限,早晚要面对一些不太熟悉的领域,这种时候我没有太好的办法,除了模拟身受,用各种法子说服自己信,你是这个人,你在体验类似的旅程,你的感受如果可能成为真实,那么便或许可以得到一篇让人信任的小说。
梁 海:你的话让我想到了玛丽安·摩尔关于诗歌创作的诗句:“想象的花园里面有真实的蛤蟆。”小说家创作了想象的城市和想象的人物,他们有真实的问题,真实的困境。这种“真实”应该就是源自你说的“感同身受”,我想这也是很多青年人喜欢你作品的真正原因。就我的阅读体验,你小说中最打动人的地方是那种一言难尽的家庭关系,那种源于血缘之间的陌生隔膜、无法沟通,令人心悸,很多人物的悲剧源自于原生家庭。为什么会选择书写这类故事?
杨知寒: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习惯了扮演倾听者,我喜欢听各种各样的谈话,嘴上不参与,心理一直跟随着谈话的指引,被话题和情绪带动,像一名旅客。我的成长环境又是个语言密度比较高的地方,能让我观察到语言之外遗留下来的一些情感痕迹。家庭关系在这样的观察里充满疑团,后来你会明白,那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所有关系的疑团,不局限在家庭,而家庭是一个很好的培养皿。家庭关系又是我们落生为人要处理的第一重关系,对孩子而言,它意义重大,影响至深。
梁 海:你在一次专访中谈到镜子:“照镜子是我的一个方法。我书桌上立着一面镜子,写人物的时候我会观察我的表情,带入人物的语气、表情、心理。听起来有点玄乎,但对我很有用。从镜子里,我可以看得到那个人物的状态。不写作的时候,平时照照镜子,观察自己啥状态也挺好。”在你的作品中,镜子也是一个经常出现的意象。比如《连环收缴》中燕好通过后视镜看到自己因酒醉而浮肿的眼睛,看见妹妹燕凤朝向窗外的脸和上面零落的色斑。《瑞贝卡》中镜子意象更是频繁出现,还有《出徒》《一团坚冰》也都有镜子意象。这些人物通过镜子观察世界,也观察自己。镜中的世界既真实又虚幻,融合了诸多的想象。
杨知寒:是的,我平时也喜欢照镜子,对镜子做反应,作为解压的一种。喜欢看着这个最熟悉也最陌生的人,是怎么在生活里扮演自己的。
梁 海:我猜想,正是基于“照镜子”的写作方法,你小说中的人物塑造和小说结构有时呈现出一种镜像关系。最典型的是《瑞贝卡》,其中,瑞贝卡与李晓瑞、“我”与李晓瑞、“我”的母女关系与李晓瑞的母女关系,都呈现出镜像对照。不知道我的猜想对不对,你能具体谈一下吗?
杨知寒:您的感觉是对的,最后看起来也很像是一种设计,即两对母女关系的对照。在写的时候,没想到这些,似乎故事都已经安排好了,我拿到素材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两对母女,两个同龄女孩,两段破碎的人生经历。她们像是人和镜中人的身份,又更像是一部恐怖电影的桥段:你站在镜子前,向左挥手,镜子里的人,向右挥手。她们不是同步的,她们不是彼此的镜像,灵魂各异,说不好谁是谁的宿主。
梁 海:你的纯文学创作都是中短篇小说。从文体上看,中短篇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在纯文学领域是一种边缘化的文体,这一方面是因为短篇小说对一位作家的叙事技术,以及叙述中穿透生活、呈现人与世界的能力,都有更高的要求。这种文体对作家的审美表现力,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从文学生态来看,长篇小说能够给作家带来更多的利益和回报。所以,当下依然活跃在文坛的“五○后”“六○后”乃至“七○后”作家大多都将重心放在长篇小说上,倒是这几年表现突出的一些“八○后”“九○后”作家更多地关注短篇小说,比如你、班宇、双雪涛、王占黑、郑在欢等,你对这一文学现象怎么看?你为什么会偏爱中短篇小说?
杨知寒:在我的阅读过程里,也是这样,偏爱短篇,偏爱那种讲不完全的感觉。合上书,你知道故事已经结束了,但它和你的联结可能刚刚开始,它还会在你的生活里盘旋一段时间,即使你意识不到它的影响,它就横亘在那儿,很暧昧,很微妙。现在中短篇受到关注,可能和生活节奏有关,也可能是别的。我只能解答自己的心情。我偏爱有打击感的画面,比如玩射击游戏,迂回潜行,快速一枪,正中眉心。
梁 海:很多起步于短篇的作家,往往都会过渡到长篇。我知道你在网络文学平台曾发表过长篇小说,未来在纯文学领域是否也有创作长篇的打算呢?
杨知寒:写作就是自己跟自己较劲,会什么都想试试,尤其在一个乐园里待久了,会想进入下一个乐园,当然那里可能布满荆棘,到处陷阱,需要开垦,需要重新搭建。那里可能永远也成为不了乐园。不过总是想去看看。
梁 海:近年来我一直在做有关东北文学研究的课题,所以,也注意到很多媒体在报道你的文学创作时会将你称为“东北文艺复兴”的接力者,或将你纳入到“新东北作家群”的行列。对于这些“标签”,你是怎样看的?我知道,很多作家都不大愿意被某一标签所绑定。
杨知寒:其实更多是觉得有点儿茫然。不单写作者,生活里的人都会被贴上各种标签,我们现在似乎都接受了,也会拿标签去轻易辨识一个人,就跟初次见面时,问询对方的星座MBTI差不多。你知道那不能解释什么,无非是建立了解的一种方式。因为我是东北人,写了我了解的东北的一些事,因此被进行划分,就是这样吧。
梁 海:尽管你是从黑龙江走出的作家,但在具体创作上,我认为你和班宇、双雪涛等作家有着很大的不同。你的创作是“向内转”的,不是关注东北老工业基地外部的“锈色”对“子一代”的影响,而是由外部世界向创作对象的内心世界位移,关注创作对象的内心体验和感受,“转”向生命本真,“转”向心灵本位。
杨知寒:写作者都是具体而特别的人,所以关注点会不同吧。像前面说的,一些不是太触动我的东西,写得就少,一些触动我的,会反复写,想挖得更深。
梁 海:“新东北文学”已经成为当下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对于“新东北文学”我有一点担忧,在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作家的近期创作中,东北似乎正在被悄然“放逐”,班宇新出的短篇小说集《缓步》,东北的色彩就淡了很多。所以我也在想,你离开东北已经十年,一直住在杭州,尽管你的文学书写至今依然保留着“东北影像”,但这种“第三地写作”随着写作的积淀和时间的推移,加之南北文化的差异,会不会发生走向的位移?今后你的文学创作还会在东北这块土地上持续发力吗?
杨知寒:不知道自己未来会怎么写。能确认的是,我也仅能,或者说愿意写自己想写的故事。像之前写网络小说,因为当时就觉得写那个有感觉,别的没感觉,所以不写。在杭州生活已经十年,没发现自己在生活习惯上有太大的改变,可能因为我没真正进入过社会。我一直还保留着相对的、不受影响的状态。希望能一直保持。
梁 海:关于“新东北文学”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新东北文学”引发了“新南方写作”等地方性写作热潮,受到学界的深度关注,对地方性话语的建构和限度开展了广泛的讨论和思考。从作家的角度,你如何看待地方性写作的问题?
杨知寒:我觉得怎么都行。没什么是确定的,相对论现在应用太广阔了,同一件事正反怎么说,怎么都有道理。所以地方性写作也好,没有地方性的写作也好,都该被接受,标尺非要定一个的话,是写出好小说。
梁 海:在我看来,“新东北文学”引发的还不仅仅是地方性写作的问题,还有关于文学的“破圈”。班宇、双雪涛、郑执都有作品被影视改编,前不久,班宇担纲文学策划的《漫长的季节》更是被视为“现象级作品”。你怎么看待这些“破圈”现象?
杨知寒:一切还得由作品的质量决定,作品好了,一些事情是水到渠成的,作品不好,推波助澜也无意义。我们处在一个信息繁多到爆炸、处处爆炸的时代。网络极大淡弱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文学不可回避,它也将海纳百川,容纳更多,被更多去容纳。
梁 海:最后谈谈你的打算吧,对未来的文学之路有什么样的规划?
杨知寒:没什么打算,就一如往常,最好了(笑)。再次谢谢梁老师。
原标题:《文学访谈 | 杨知寒 × 梁海:写作就是跟自己较劲》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