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黄进兴︱沙漠的智者:田浩教授

田浩与我享有不折不扣的同门之谊。我们都曾是林毓生、余英时、史华慈教授的学生。
首先,林先生乃是田浩就读弗吉尼亚大学硕士班的指导教授,而我则是林先生1974年返台,客座台大时的忠实听众。由于当时法规并不容许,因此林先生所授的课,并不算学分;但丝毫挡不住那些来自各校求知心切的学子,课堂上总挤上百来人,连夜晚的研讨课也不下数十位,学员个个士气高昂。而这些听课者不乏日后研究思想史的种子。究其实,林先生和余先生乃是台、港两地思想史崛起的最重要的播种者。初起,经由林先生的授课,打开了该时颇为沉闷的人文气氛,颇有拨云雾、见青天的感觉。
林先生出身学术名门。他的博士学位乃得自芝加哥大学的“社会思想中心”(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该中心网罗全美首屈一指的学者,标榜跨领域攻坚的研究取向,号称难读,故别有特色。在课堂上,林先生不时地抛出他的业师、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大师——哈耶克,以及海德格尔的得意门生——政治哲学家阿伦特、化学家兼知识论的怪杰——迈克尔·波兰尼、社会学的大师——爱德华·希尔斯等人的大名,光彩夺目,让我们这些远在异乡不得亲炙的求知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无以复加。
除此之外,林先生并引进韦伯、库恩和伯林以及史华慈的论旨。课堂当下,众人朝夕讽读韦伯的《政治作为志业》(Politics as a Vocation,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eds. & tran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77-128)和《学术作为志业》(Science as a Vocation,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eds. & tran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129-156),以及伯林的《自由的两种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 Isaiah Berl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18-172)和《刺猬与狐狸》(The Hedgehog and the Fox, Isaiah Berlin, Russian Thinkers, ed. Henry Hardy and Aileen Kell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9, pp. 22-81)诸文,人人牙牙学语,乐不可支;遂在台湾大学掀起一股弦歌不辍的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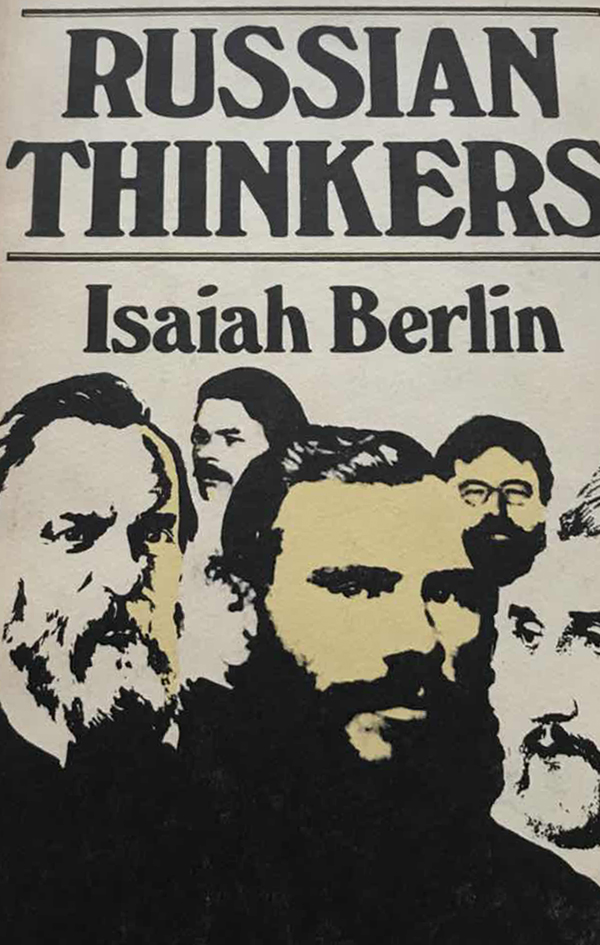
当时的人文学界:缘有林毓生阐发诸观念于前,复有余英时的史学实践共鸣于后,遂谱成动人心弦的学术二重奏,而获得极大的回响。尤其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2)里所涵摄的“范式”(paradigm)的核心概念(库恩以范式的转移解释了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影响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的人文及社会科学),经由余英时先生在《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具体的操演,“尊德性”和“道问学”遂成范式迻转极具启发性的示例,进而深深影响了日后近二十年人文研究的方向。
此外,伯林的“刺猬”(hedgehog)和“狐狸”(fox)的概念,原本意在分析大文豪托尔斯泰的思路,不意由余先生转手用来彰显清代中期两位标竿性的学者——戴震(1724-1777)与章学诚(1738-1801)——泾渭分明的学风。之后,学界群起仿效,中国思想史的领域顿成了野生动物园,一大群“刺猬”和“狐狸”跑来奔去,好不热闹(伯林撷取希腊诗人的断简残篇“狐狸知道许多事情,但刺猬只注意一件大事情”,倚之分类西方学者、作家和艺术家中存有迥然有异的两种风格;另见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台北:华世出版社,1977)。的确,七八十年代,大陆与台、港两地相形隔阂,但林、余两位先生确是其时中国思想史最关键的开拓者。受此影响,我便下定决心,负笈西方,追求真理。
1977年前去哈佛报到,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巧遇田浩,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他甫获得博士学位,正准备前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任教。须知当时在美国人文学界谋职甚为艰困,连几位日后成名的学者其时也多是流浪教师,而田浩一下子便找到任职的学校,算是幸运不过了。但是位于沙漠之际的该校,竟然留住田浩一辈子的教学生涯,则是他始料未及的。他终成了沙漠的智者。
田浩的博士论文原是处理南宋非主流的儒者——陈亮(1143-1194),他谓之“功利型的儒家”(Utilitarian Confucian)。但之后,他便把注意力移至朱熹(1130-1200)这位理学集大成者,甚至与其后裔结了不解之缘。有趣的是,在二十世纪陆王之学环伺之下,田浩的太老师——钱穆(1895-1990)先生,晚年以《朱子新学案》孤鸣独发,重振不绝之学,而其业师——余英时则以《朱熹的历史世界》名重于世。而田浩本人则继之以《朱熹的思维世界》风行两岸,一系三杰,洛闽之学,接踵而起,遂得重现光辉。
还记得九十年代田浩曾挑起了一个小小的论战[可参阅田浩和狄百瑞1992年至1994年所发表的论文和响应,收入《东西哲学》(Philosophy East and West)]。原来 “Neo-Confucianism”(新儒家)此一英文用词,困扰了不少专家学者。一般用它来指称“宋明理学”,偶尔也用来指涉民国的新儒家,恒相混用。惟田浩以研究异端陈亮起家,他所见的宋明儒学远较他人宽广、多元,因此他不满意当时北美研究理学的巨擘——狄百瑞,专挪“Neo-Confucianism”一辞来概括宋明儒学的全貌。是故,他起而纠举,发文声讨,却引起了你来我往的论战,可惜狄百瑞只回了一两合,便置之不顾。因此《旧约圣经》所描述的大卫与歌利亚的决战,在今日学术界并未得复制。而田浩只能以卵击石收场罢了。
对照北美汉学新潮的流风,田浩的治学不免显得质朴少华,难以兜售。其实,以他所积累的学术成果,照理谋得顶尖大学的教职,并不为过,但他却“回也,不改其乐”,依旧择善固执,只能如曾国藩“屡败屡战”,而为知者所叫屈。但他的问学稳健扎实,不贬道以求售,颇类东方人理想的治学风范。在冥冥之中,上帝似又为他在东亚开了一扇大门,在异乡受到甚大的赏识和掌声。如前所述,他为学厚重踏实,中文底子甚佳,极早便因发现陈亮的佚文,补充了《陈亮集》,而为中国宋史大家邓广铭(1907-1998)慧眼所识,并和其下一代邓小南教授学术上过从甚密,允为跨代情谊。又田浩的英文原著,均有中文繁体、简体译本(间有韩文译本),遂为东方学界所熟悉。盖其立论肯綮,不乏新意,复兼中、西学之长,故广受邀约,四处交流。田浩亦乐此不疲,有回听他说,在上海一区便有五间高校请他演讲,由此可印证他宣道的热诚。

又甫回国,我缘受同学吴东升之托,整理了他父亲——吴火狮(1919-1986)先生的口述传记(拙作《半世纪的奋斗》,台北:允晨文化事业公司,1988;日译本《台湾の狮子》,东京:讲谈社,1992),吴先生乃是该时台湾本土重要的企业家。后来田浩承担英译,并为英译本(Business as a Voc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撰写了长篇导言,不意却促使他踏进“儒家伦理”和“东亚经济”的议题,并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论文,取得了这个议题的发言权,或许可视作他研究历史上“功利型儒家”在当代关怀的赓续。究其实,田浩绝非食古不化的书生。近年他戮力疏通中、西文化里“正义”(justice)“人权”(human rights)诸观念,颇思有益于世道人心。
于私人情谊一方,1995年个人从美返台途中,受田浩之邀到沙漠之城——坦佩(Tempe)作客。田浩全程陪同我及家人前去参观废弃飞机的坟场、沙漠博物馆。最精彩便是他不辞辛劳,开了整天的车去大峡谷,大自然鬼斧神工,不得不赞叹造化之奇。沿途车中,聊了家常私事,他说父亲本为机械匠,老是担心他学人文会饿死,常不放心。言谈之间,父子彼此之间真情自然流露,让我心有戚戚焉,十分感动。原来东西方父子的情结,并无两样。他本身乃是虔诚的基督徒,加上儒学的濡化,待人谦和有礼,热心助人,故为友人所称道。此外,必须一提的,田浩作为师兄,对我们这些小学弟,在学术发展的过程中,从不吝予以鼓励与协助。这点我想不少同门应知所言不虚,就此不表了。
末了,田浩动辄以“乡下佬”“土包子”自我嘲解,岂不知他信道弥坚的学行正应验了《圣经》所预示的:“先知”注定在家乡受到误解和轻视,在异乡却得大发光彩。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