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读︱蔡伟杰:争议之外,“新清史”有何新进展
按:岁末年终之时,应澎湃编辑部之请,略谈一年来的读书与见闻。此处仅就笔者学力所及,不揣浅陋,与读者分享一些读书心得。敬祈方家指正。
首先,如果要总结2016年几个与笔者专业相关的关键议题,也许可以用“内亚”(Inner Asia)、“新清史”与“一带一路”三个词来概括。就笔者今年所参加的几个会议来看,六月于日本京都参加2016年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亚洲区年会(AAS-in-ASIA),讨论如何整合历史人类学(另称为华南学派)与新清史两种研究取向。八月赴张家口参加“张家口•冬奥会与一带一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转赴北京人大国学院参加第二届“清朝与内亚”工作坊。11月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一带一路:现代中国、内亚与东南亚的交织网络”工作坊。从这些会议主题与内容来看,前述的三个关键词在笔者今年的阅读与写作中反复出现。因此以下即针对这三个主题相关的书籍进行讨论。
在今年所寓目的新译西人边疆游记当中,《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的面世无疑是件让人兴奋的事情。作者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为德国著名的地质地理学家,也是最早提出“丝绸之路”(Seidenstraße)一词的学者。在这本书中记载了他于1868至1872年间在中国的七次考察,并且对各地的地质与物产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与描述,包括了华北的黄土以及山西的煤矿等等。不过严格来说,本书所提及的地区以中国内地为主,至于蒙古、中国新疆与西藏等内亚边疆的记载相对较少。再加上本书的出版所受的关注较多,故本文不拟多加着墨。

下面想谈谈另一本时代较晚但较被忽略的近期译作《黄色的神祇黄色的人民》(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作者李盖提(Ligeti Lajos,或依英美习惯作Louis Ligeti)为匈牙利的著名东方学家,尤其以蒙古学与突厥学见长。笔者的业师卡拉(György Kara)教授也是他的高足。本书是李盖提于1928至1930年间游历内蒙古与满洲等地的游记。他见到了当时在内蒙古的中外重要人物,例如瑞典人拉森(Frans August Larson)与喀喇沁亲王贡桑诺尔布。与通过田野调查与自学的美国蒙古学者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不同的是,李盖提在游历中国内蒙古以前,已在布达佩斯与巴黎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他喜欢吃北京烤鸭,对蒙古佛教甚为着迷,并且直陈当时内蒙古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商贸在中国与外蒙古切断联系后大为衰退。大量汉人移入内蒙古,蒙古人的生活凋敝等等。在政治上,他对国民党地方干部对他三番两次盘查表示不耐,更抨击国民政府与军阀治下的中国基层混乱与失序。他也常常比较蒙汉两个民族的差异,提到汉人在饮酒上的节制,对比蒙古人的嗜酒;汉人喋喋不休,蒙古人则沉默寡言等等。就译文本身而言,本书有时采用了非惯用译名,甚或出现一词二译的情形,例如将汗八里(Kan balik,或记为Cambaluc,即今日的北京,元代称为大都)分译为可汗巴里克与康巴鲁克(第33页)。另外有部分人名错译,例如第51页的帮助明朝铸造大炮的神父亚当·夏尔(Adam Schall)应为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第52页提到在喀喇沁王府负责教育的日人酉井(Torii)实为著名的鸟居龙藏(Torii Ryūzō),第63页述及忽必烈时期著名的穆斯林萨义德‧艾哲尔(Szajjid Edzsell)家族应作赛典赤等等。但瑕不掩瑜。没有译者刘思岳的辛劳付出,这部兼具学术与历史意义的游记恐怕不知要再等多久才能与中文读者见面。本书推荐给对20世纪上半叶的内亚边疆与一带一路有兴趣的读者。

自去年将美国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比喻为“新帝国主义史学”的批判文章出版以来,中国学界的相关批评与争议至今仍余波荡漾。少数学者呼吁对新清史可以批判性的接受,主要是蒙古史学者。例如张志强主编之《重新讲述蒙元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文集中的部分学者将蒙元史与美国新清史作比较,并且试图去回答何谓元代中国的性质问题。就笔者管见所及,虽有中国人大清史所讲师胡祥雨的《清代法律的常规化:族群与等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北京社科院满学所哈斯巴根的《清初满蒙关系演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与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马雅贞的《刻画战勋:清朝帝国武功的文化建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等书与新清史对话,但整体而言中文学界宣称采用新清史取向的研究仍旧不多。相较之下,直接或间接驳斥新清史相关的文章数量明显较多,其中从政治立场问题、非汉文档案的局限性、维护中国历史学界话语权与中国历史主体性,乃至质疑新清史学者的语言与研究水平等角度入手,不一而足。部分的论战文章已收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所编的《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北京:中华书局,2016)中。新清史在中国的影响与接受度可说是“雷声大,雨点小”。
中国学界的批评声浪也引起了国外学界的注意,并试图进行更广泛的了解。例如《当代中国思想》(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第47卷第1期(2016年)便以“近年新清史在中国的论争”为题出版专号,收录了李治亭、李爱勇、章健与杨念群等四位中国学者相关论文的英译,并由澳门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康言(Mario Cams)导读。此外,相关学者更前来中国交流演讲,或在网络或报刊杂志上撰文,试图说明“新清史”内部主张的差异,并澄清新清史实为学术理论,并无政治阴谋,与二战前日本学者主张的满蒙非中国论不同,且并未主张清朝非中国王朝等等。但截至目前为止,这类澄清似乎收效不大,类似的质疑仍旧存在。而且从网络上的讨论看来,对新清史的批评已成为宣泄民族主义情绪的出口,短期内没有消失的迹象。
任何学术思想的传播与接受或多或少都伴随着误解与争议。但新清史在中国的情况加上了政治与民族主义情绪,使得这类争议更加难以厘清。笔者无意纠结于这些争议上,建议有兴趣的读者直接阅读新清史学者的原作,而非仅止于阅读相关的引介或争论文章。今年柯娇燕(Pamela K. Crossley)的旧作《孤军:满人一家三代与清帝国的终结》(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就被引介出版,另外欧立德(Mark C. Elliott)的《满洲之道》(The Manchu Way)中译本也预计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而对新清史学者有所影响的日本东洋史家冈田英弘(OKADA Hidehiro),其文集《从蒙古到大清:游牧帝国的崛起与承续》(モンゴル帝国から大清帝国へ)的繁体中文版也于今年由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些都提供了中文读者更多认识新清史的管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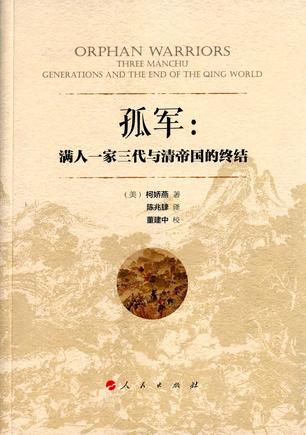
以下笔者想谈谈今年所见的新清史新进展,供读者参考。新进展之一主要是反映在清代新疆史领域上,其特色是从跨国族群网络与全球比较观点,运用多语种史料,重新评估新疆的历史发展。例如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历史系助理教授金光明(Kwangmin Kim)今年出版的新作《边地资本主义:突厥斯坦产品、清朝的白银与一个东方市场的诞生》(Borderland Capitalism: Turkestan Produce, Qing Silver and the Birth of an Eastern Market)(史丹佛:史丹佛大学出版社,2016)利用了满、汉、维与俄文材料,主张清朝统治新疆的成功在于联合当地的回部贵族伯克(beg)。美洲白银以清朝赏赐或薪俸的形式流入新疆,扶助回部贵族取得优势地位。而回部贵族则利用这些政治优势与白银资本,雇用当地人成为劳工,生产当地的特产(包括玉石、马匹、牲畜、棉花与谷物等)供应贸易市场以牟利,扮演类似西方资本家的角色,跟英属印度治下的当地贵族地主所起的作用类似。金光明引用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布劳岱尔(Fernand Braudel)对资本主义的广义诠释,称此为“边地资本主义”,也是全球资本主义许多不同形式中的一种,而这也是作为一种脱离以欧洲中心的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叙事。而且可以修正过去学界强调汉人移民与驻军等外来因素来解释清朝之所以能成功治理新疆的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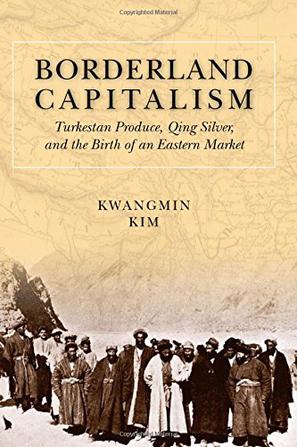
另外一部相关的新作则是澳洲悉尼大学现代中国史讲师大卫‧布罗菲(David Brophy)的《维吾尔民族:俄中边疆的改革与革命》(Uyghur Nation: Reform and Revolution on the Russia-China Frontier)(麻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16)。本书征引了满、汉、俄与察合台文档案,探讨新疆使用突厥语的穆斯林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上半叶如何在俄国、中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三方的影响下,形成了今日的维吾尔民族。十九世纪末以追求启蒙与现代化文明为号召的扎吉德主义(Jadidism)广泛流行于俄国突厥系穆斯林当中,并且透过这个跨国网络传入中国新疆与奥斯曼土耳其境内的突厥系穆斯林,以此作为共同抵抗欧洲帝国主义的连结纽带。这是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的展现。但是维吾尔民族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并不符合中俄两国的利益。因此一直要到1934年盛世才与苏联合作巩固在新疆的统治后,在苏联式的民族概念传入下,新疆的维吾尔人才得以被承认为一个民族。本书的特点在于通过对中、蒙、俄、土四方材料的广泛使用,把当时的跨国突厥系穆斯林社群网络,以及这个网络在形塑维吾尔民族过程中的作用加以说明,有助于学界从跨国的综合角度对这段历史有整体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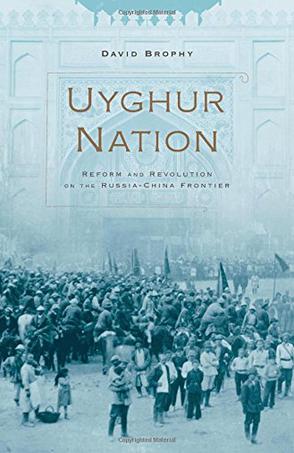
另一种新进展则是与环境史取向的结合。华盛顿和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贝杜维(David A. Bello)的新作《越过森林、草原与高山:清代中国边地的环境、认同与帝国》(Across Forest, Steppe, and Mountain: Environment, Identity, and Empire in Qing China’s Borderland)(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6)就反映了这种取向。本书利用满汉文材料,讨论满洲(森林)、内蒙古(草原)和云南(高山)三种生态环境与当地民族之交互作用,聚焦于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揭示清帝国如何形塑不同边地的族群认同。诸如满洲的代表动物为猎物;内蒙古的代表动物为牲畜;云南的代表动物主要是以蚊蚋传递的吸血寄生虫。而代表满洲认同的骑射透过打猎维持,清廷以八旗制度管理之;蒙古人在草原上透过牲畜维持生存,清廷以札萨克制治理之;云南土著则以瘴气疟疾守护自己的主动性,清廷以土司管理之。而汉人领域的代表则是农地与谷物种植,清廷以郡县制度治理之。本书的特点在于将清代族群认同的形塑与生态环境、生计方式与行政制度连结在一起,有助学界发展更具整合性的分析架构来讨论清帝国如何形塑其环境与族群认同,并且注意到汉人认同中农业开垦及其对环境的强大改变能力所起的作用,以及清帝国内部的不和与冲突很大一部份起因于汉民农业垦殖扩张到边地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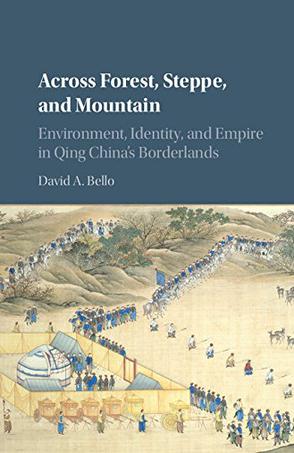
除了前述的作品以外,其实尚有一些佳作。但限于篇幅,不免有遗珠之憾。爰列数条,方便读者按图索骥:
1) 山东大学历史学教授陈尚胜的文集《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5)中关于明朝与清朝的封贡体系比较的文章中主张,清朝封贡体系的基本目的在于保障国家安全与边疆稳定,且这点也影响了清廷对某国是否应纳入封贡体系的选择。窃以为此分析值得注意,并可连结到马世嘉(Matthew W. Mosca)对于清朝与廓尔喀关系的分析,以及野田仁(NODA Jin)与小沼孝博(ONUMA Takahiro)对清朝与哈萨克与其他中亚诸国关系的讨论。
2) 中国社科院社会所助理研究员郑少雄的新作《汉藏之间的康定土司:清末民初末代明正土司人生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探讨了清代康定与明正土司作为汉藏之间的中介地域与模糊认同。然而土司社会的消失伴随着国族历史叙事的出现与汉藏边界明晰化,最终导致双方冲突的极端化。可以说本书提供了一种对当代汉藏关系的另类思考面向。
3) 德国海德堡大学博士候选人俞雨森的近作《波斯与中国——帖木儿及其后》(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从图兰朵公主传说、玉器、瓷器、鬼魅图像与观音等主题,讨论中国风如何流行于帖木儿帝国治下的波斯。书中文字搭配彩图,娓娓道来这段鲜为人知的多彩多姿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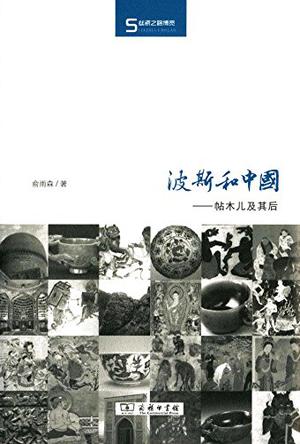
最后我想介绍的是印第安纳大学音乐人类学博士候选人魏小石的新书《民歌笔记:田野中的音乐档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本书收录了他在求学期间发表的民歌田野调查笔记与相关译文。作者长期关注突厥民歌,并且对于保护这些无形的文化遗产不遗余力。透过作者的参与观察,那些云南、新疆音乐人的形象与其歌谣中的故事跃然纸上。推荐给对民族音乐有兴趣的读者。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