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并不浪漫的民国师生恋:北大教授丢饭碗,知名出版人遭通缉
杨栋林、韩权华:北大教授恋上校花,被迫引咎辞职
对于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的韩权华而言,她似乎一直生活在聚光灯之下。出身天津八大家之首的“天成号韩家”,姐夫是清华校长梅贻琦,这一系列显赫的身份使得她甫一入校便受人瞩目。
不过,韩权华受到关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其出众的外貌。许君远在《读书与怀人》一书中回忆称:“乙部(文预)女同学较多,最漂亮的是韩权华,长身玉立,洒然出尘。” 被目为“校花”的韩权华,自然不乏追求者。来北大求学以来,韩收到“不认识人的来信不知凡几”。在众多来信追求者中,有一人身份颇为特殊,便是北大教授杨栋林。

杨栋林,字适夷,贵州毕节人,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从1923年年初开始,杨栋林便向韩权华释放爱意。或许是自矜身份,杨的爱情攻势较为含蓄,不过是写写明信片,抄录英文小诗寄给韩。1924年1月12日,杨栋林发表启事,为其兄代聘家庭教师。次日,杨特意私下将启事转寄韩权华,希望其能就聘,以此增进两人关系。
不料此事不胫而走,校内开始传出两人关系的谣言。有好事之徒还在厕所内张贴启事,大肆渲染。而北大学生裴文中则以“明华”为笔名,将二人之事添油加醋写成报告文学,以《厕所内的婚姻问题》为名投稿《东方时报》副刊。文章刊出后,在北大校内引起骚动,师生热议。
在风言风语尘嚣甚上之际,4月26日,杨栋林再度写信给韩权华。信中一方面转述坊间关于二人的诸种传言,另一方面则言辞暧昧,颇似亲近之人商讨如何处理。表面上看似在澄清谣言,实则试探韩的真实态度。正如《两性间一桩习见的事》一文在事后所分析:“原信全篇都引外界如何如何的话,作成功自己婚姻的圈套。”
不料韩权华却将此事写作文章,以《一封怪信》为名投至《晨报副刊》,并将杨栋林的长信全文转发。行文最后,韩权华不无愤慨地说:“不意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对本校女生——素不认识的女生竟至于如此。我以为此等事匪但与权华个人有关,实足为中国共同教育(co-education)之一大障碍。我北大女生,我北大全校皆足引为不幸。”
此文刊出后,舆论一阵哗然。被推至风口浪尖的杨栋林赶忙写文辩白,但也无济于事。北大学生发起“驱杨”运动,有人张贴皇榜,发檄文,指其为北大全校之不幸,全国女子之不幸,又有人称杨先生的信是教授式的强盗行为,是威吓欺骗渔猎女生的手段。整个北京社会的舆论,俱斥杨为十恶不赦的大罪人。就连远在上海的《妇女周报》记者奚明,都收到不相识的人从北京写来的信,请他们一致声讨。
与此同时,北大校长蔡元培也写信给杨,叫他自行辞职。而其余杨所授课的学校也纷纷要求他辞去教职。5月10日,杨栋林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通告,无奈辞职离去。而韩权华也受此事之累,转学女师大,后赴美留学,回国后嫁与卫立煌为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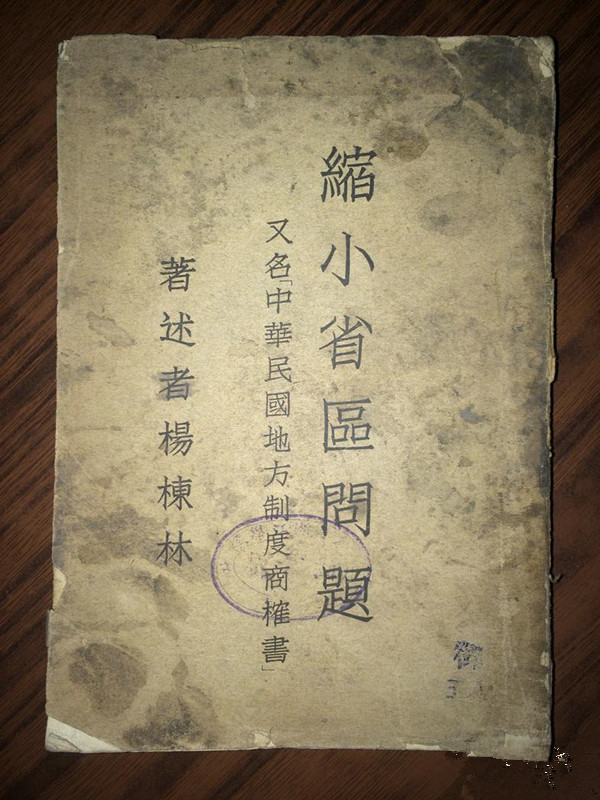
回望此桩风波,杨栋林尽管声名受累,但至少性命无虞。彼时却另有一人因师生关系暧昧受到通缉,险伤性命,累及好友受牢狱之苦。此人便是民国著名出版人舒新城。
舒新城、刘舫:一个被全城通缉、一个被勒令转学
1924-1925年间,舒新城任教于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期间,舒结识了高师的预科学生刘舫(又名刘济群)。舒新城爱好摄影,经常随身带有相机,刘舫对此颇为好奇。因摄影之由,他们开始了频繁的交往。舒刘二人的交往,慢慢由摄影转向学业。舒新城指视刘舫为私淑弟子,往来日多。
在成都高师里,刘舫因成绩优良,面容姣好,是校内颇有名气的“红人”,追求者甚众。而舒新城也因经常在校内外发表演讲,在当地风头颇劲。二人皆为校内焦点人物,其关系自然也被放到聚光灯下。舒新城事后回忆说,“在当时,我与刘君既为大家所重视,当然不免有人作为谈话资料。”关于二人的风言风语开始在师生间流传开来。
1925 年4 月24 日,高师校长傅子东找刘舫谈话,称有多位女学生反映她与教师舒新城恋爱,为学校安宁计,清除师生恋爱的恶劣影响,强令其转学。学校的做法令一部分有新思想的学生十分愤慨。4 月27 日晚,这些学生集中百余人要求校长收回成命。迫于压力,校长只得照办。
学校强令刘舫退学未果,转而把目标放在了舒新城身上。4 月28 日上午,学校以教职员全体名义召集学生开会,以“诱惑女生、师生恋爱”为罪名,缉拿舒新城。校长傅子东率领教职员学生代表至军署请兵,斋务长秦某则指挥一些教职员工、学生到舒平时往来的友人处及街上寻捕,明令捕得即行殴毙。
当日中午,舒新城正出校访友李劼人和陈岳安,得知学校要缉拿他,赶忙易装躲避。军警抓捕舒新城未果,只好将李劼人抓去关押做替,至5月8日才释放。
据舒新城《我和教育: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1893-1928》中记载,当时场面颇为紧张:“易装甫毕,即闻门外人声嘈杂,劼人乘酒兴出,与大闹,我乃由岳安乘间引至劼人舅氏后院短墙边,扶我逾墙跳至邻居,邻人初以为盗,大声呼喊,岳安告之,且同逾墙,始获无事。劼人之闹,则为故延时间,使我能安全逃出,经过半小时之争辩,劼人卒令督署宪兵及学生代表入室搜索,不得,乃将劼人捕去。”
为了抓住舒新城,军警一方面发布通缉令,在四川全省悬赏缉拿务获,另一方面将舒新城平日过往的一切地方与教堂洋行全部派人查访。而此时的舒新城,则在成都友人居所不断辗转藏匿,躲避追捕,并抓紧计划逃离成都。
经过一番周密策划,5月10日晚,舒新城改西装革履为长袍布鞋,戴墨镜,操蓝青官话,剪掉长发,剃成光头,留胡须,改姓名为余仁,扮成京华书局主任身份,11日凌晨趁守城军士睡眼朦胧之际,混出城外,经10天旅途,于5 月20 日到达重庆,逃离了是非之地。
有趣的是,这桩意欲拆散舒刘二人的“恋爱风波”,反而促成了二人的良缘。经此一劫,舒新城对刘舫的了解更进了一步,对其无视他人诬害并时时关心别人的表现甚为赞赏,认为其勇气“似乎不是一般青年尤其年未二十至女子所能有。平时我们的思想本多相通,此次结成生死之交,人格上之感应力更大,在当时我们固然说不上恋爱,但自此而后,彼此的潜意识中都有爱苗在滋长”。后来,随着两人通信的频繁,接触愈来愈深入,于1931年终成爱侣。

“《辞海》之父”舒新城
“师生如父子,万不可有结婚之事”
回看杨栋林、舒新城身陷师生恋爱风波的悲惨境遇,似乎与今人关于民国的浪漫想象不同,但却是彼时实相。
近代中国,男女之防破除,社交公开、自由恋爱之风渐起。随之而来的是在自由解放的大旗之下,师生恋爱之事时有发生。《中国摄影学会画报》曾有文称:“新华艺专师生爱,已成一习气。每一教员,大有非恋一女生不可。”此报道虽言一校,但其实很多学校都有同类事件发生,报章之上也多以艳史之名进行报道,已成坊间热议话题。
师生恋在彼时舆论之中,多以负面形象示人,时人也对其负面影响多有思考。《觉悟》曾载《男女同学前途上的大障碍》一文认为:“在男女同学的各专门以上学校里——无论私立或国立——常常发现的,并且为男女同学前途上障碍的,并不是同学和同学之间的事情,却是教员和学生之间的事情。这种事情的发生,已经不止一次,不止一校了。”此言一则表明师生恋爱并不乏见,另一方面则视师生恋爱反而妨害了男女同学、社交公开。本为社交公开产物的师生恋爱,反而成为其前行之障碍,颇为吊诡。
当时社会舆论对师生恋爱的容忍度不高,与传统中国的道德观念相关。传统中国社会,为人师表者有着严格的道德操守,师生关系与伦理关系相关联,男老师与女学生往往界限严明,不得越雷池半步。
正如彼时《妇女周报》上的《成都的恋爱狱》一文中所言:“师生如父子,是中国社会里不刊的定论”,师生之恋,干犯名分,社会舆论多有抨击。昔日罗素携学生勃拉克女士来华演讲,公然承认二人夫妻关系。这不合社会习惯的恋爱关系颇受国人非议。只不过是因其为外国人,“以中国的道德观念去批评他,总觉不甚吻合,所以攻击他的,也就不十分激烈。”
罗素是外国人,得以逃过一劫。但若当事人是中国人,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1923年,时任甘肃第三师范学校校长的高文蔚,因娶女学生为妻,遭到了当地士绅和教育界人士的激烈反对。地方守旧人士发起“维持纲常名教会”,对高文蔚群起而攻。结婚当日,群众散发传单,誓将高文蔚驱逐出境。还有人连打电报,请求政府惩办,而女学生更激烈,大有“灭此朝食”之概。高文蔚的老师、甘肃学界名流杨汉公也致函《时事新报》,激烈谴责高文蔚:“师徒之谊,在父子兄弟之间,为维持人道尊重师道计,万不可有结婚之事。”
高文蔚身处内地,传统束缚较多。但彼时北京之类大城市风气也难说开明。北京广安中学,就曾因所谓师生恋爱事件发生学潮,闹得满城风雨。对此,《每周评论》评论表示:“学生运动的对象,现在由文化及政治转到恋爱;这是现在中国腐化教育的一种严重病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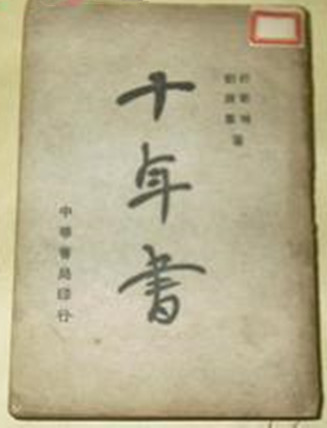
应否容忍师生恋,知识分子怎么看?
与彼时社会舆论对师生恋的苛责不同,知识分子的态度则相对宽松。尽管有所责难,但也多聚焦于别处,对师生关系着墨无多。如成仿吾、冯乃超批评鲁迅“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实为思想落伍者”之语,更多还是着眼于鲁迅有妻,将其比作娶妻纳妾的老旧做派。
以前述韩杨事件为例,知识分子多认为杨栋林求爱实属平常。《妇女周报》的记者奚明就称杨栋林对韩权华不过是正常的人的感情,其错不在恋爱,而在于其没有掌握好方法,没有走对步骤:“对于不认识的女子突然写一封信去和伊讲恋爱,(杨君的信是否向韩女士讲恋爱姑且不说)这种举动即使不能说是对于女子的重大侮辱,但至少不能不说是冒昧或失礼,因为他还没有到了可以写信和伊讲恋爱的步骤的缘故。”
周作人也认为杨栋林的过错只不过是“向不认识的女生通信而且发言稍有不检点之处”,并没有触犯什么法律道德的界限。相反,“倒杨”的北大学生们反倒成了周作人的矛头所指。在周看来,这些学生们发动社会运动来维护传统礼俗,实在可悲:“中国自五四以来,高唱群众运动社会制裁,到了今日变本加厉,大家忘记了自己的责任,都来干涉别人的事情,还自以为是头号的新文化,真是可怜悯者。”这一观点也得到孙伏园的认同,孙直接表示:“现在少年人维持礼教,我总觉得比老年人着实热心,着实负责任。”在呼吁自由恋爱多年后,青年仍旧未脱传统礼俗的窠臼,对于开启民智、倡导新知的知识分子而言,多少有些怒其不争的意思。
以今日后见之明观之,在现代化程度更高的欧西诸国,对于师生恋的容忍程度却要低上不少。以对待师生恋的态度来区别新旧,恐多有不妥。孙伏园也同样注意到,“少年人的礼教却从老年人间接得来,除了圣经贤传的糟粕都具备以外,还加了许多不知从哪儿来的新鲜条例。”学生的态度,尽管可能有传统礼俗的观念留存,但也有彼时社交公开下诸种流弊的反动之意。此中所涉颇广,非本文所能一一论及,便不再展开。
其实,近代以来师生恋的出现也有其历史合理性。在男女社交初开的近代中国,除了学校,两性并无太多交往场所。学校内,女学生的青春靓丽,男教师的沉稳博学,相互吸引,日久生情也属正常。哲生曾在《新女性》上撰文《两件师生恋的悲剧》,文中转述时人观点认为师生恋爱是“自然的相互吸引的现象”,因为“在男女同学或男女同教的潮流中,教授们不得能不暗中爱上了他的年轻漂亮的女学生,而女学生们发于英雄崇拜的心理,也不免倾心于教授们。”
但哲生此文也指出,“为师者如以深沉的世故,学问的权威,甚至以别种的计谋或诱惑而引人入阱,这简直是强暴欺凌弱者的行为,必得加以社会的制裁的。”确实,师生之间并非单纯独立个体,其中颇有权势关系纠葛,并不能单纯用自由恋爱来衡量。
但凡事皆有尺度,如若仅因师生之名,便彻底否决恋爱之可能,恐有矫枉过正。前述高文蔚事件中,张东荪曾回复汤权公一言,颇为持中:夫在学校内为师者不得与女性学生有恋爱,此固为天经地义。然出学校以外,若谓对于凡曾为其所教之女子皆不能结为婚姻,此真狗屁不通之论也。”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