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蒋介石日记公开十年:从学术界到娱乐圈,哪些人查阅日记
公开蒋介石日记:孰是孰非?
2005年1月10日,蒋介石的孙媳蒋方智怡正式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签署合约,将蒋介石日记手稿(以下简称“蒋日记”)暂存胡佛研究所,时间为50年。到今年为止,正好过去十年。
现存蒋日记实际起于1918年、止于1972年,长达54年,对蒋介石成为最高领导人前后的心路历程及诸多不为人知的政坛内幕均有记载,是了解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军事、财经、社会文化的珍贵史料。日记手稿原存放在台北蒋介石官邸,蒋去世后由蒋经国保管;1988年蒋经国去世前交付给幼子蒋孝勇,1996年蒋孝勇去世前嘱咐其夫人蒋方智怡女士做妥善管理。

2000年,台湾地区发生“政党轮替”,民进党上台后台湾政治氛围变化,出现了一系列“去蒋化”的动作。蒋方智怡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称“蒋公日记属于全体中国人民”,但需要找到一个既专业又有声望、公正客观的单位才能交出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两位学者马若孟、郭岱君前往接洽,最终说服蒋方智怡将日记存在胡佛,并从2006年3月开始逐步向读者开放了手稿复制件。
郭岱君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当时蒋家认为日记放在台湾不妥当,而胡佛档案馆对历史档案的保存、修复、保护和开放的设施都是世界一流的,所以选择了胡佛档案馆。”
然而由于蒋介石身份的特殊性,日记的公开受到万众瞩目,亦引发诸多争议:蒋日记是私有财产还是公共财产?是否应该存放在外国?其中有许多涉及个人隐私的部分,是否应该公开?
宋曹琍璇是宋子安(宋子文幼弟)的儿媳妇,也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她曾应宋子文家属之邀审读开放前的宋子文档案,后又受蒋家后人委托对蒋介石日记进行初读,看是否有内容不宜开放。她向澎湃新闻强调:“蒋日记是暂存(deposit)胡佛档案馆,蒋家随时可以取回,只需提前2个月告知胡佛。如果有一天台湾准备好了,它就可以回去。”谈到日记开放的决定,郭岱君表示,“日记是非常私人的东西,蒋家大可不必拿出来,他们没有这个义务。但最后胡佛从学术价值、还原历史的角度,说服蒋家开放日记给学者研究。”

日记开放过程的确颇为曲折。
蒋介石最后一任秘书秦孝仪的学生潘邦正曾和宋曹琍璇一起做初读日记的工作,用宋曹琍璇的话来说,“他是政治上敏感问题的顾问。”日记前十年,有部分内容坦率地记录了蒋介石早年生活的浮浪,秦孝仪等人认为这些内容不必公开,以免影响“蒋公”的形象。宋曹琍璇则力争“还原他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把“成长的十年日记”全部开放。郭岱君也表示:“我们当时跟蒋家说,相信不会有学者拿他早年时候的生活来批评他,因为他同时还是年轻的革命者。果然,日记开放了那么多年,没有任何学者,即使是最左派的、最反蒋的学者,也都没有拿他早年的生活来批评他。我想日记不但使我们对蒋本人有一个重新认识,对整个近代史也都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宋曹琍璇曾竭力游说蒋家。“一开始蒋方智怡说,每过一年,则开放一年的日记。日记有五十多年,我跟她说我活不了那么长。她没有完整看过日记,我跟她讲,以我看完的感受,我觉得蒋公日记越早开放越好,这对整个中华民族会有很大的建设性的影响。”
郭岱君特别推崇宋曹琍璇和宋仲虎夫妇的支持,“他们两位懂历史、尊重历史,因此,宋子文档案全部开放,一片纸都没有保留。 蒋日记也是一样,除了早年一些家里的隐私外,30年代以后的日记可以说是全部开放。”

目前对蒋日记影响最直接的纷争,应属蒋经国孙女蒋友梅与蒋方智怡的官司。蒋友梅认为,蒋方智怡无权擅自处理蒋介石日记,于2009年在台湾提出日记所有权诉讼,一时引来外界议论纷纷。尽管蒋友梅最终撤诉,蒋方智怡也提出和解协议,但所有权一事至今没有明确说法。原本已经排印就绪、准备公开出版发行的部分《蒋介石日记》也因此而耽搁。
2013年,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为避免牵涉蒋家所有权的争议,在美国加州法院递交诉状,由法院谕令蒋家家属自行解决他们对蒋介石日记的所有权争议,以便顺利把这份史料交给合法的继承人。
“家属在蒋日记所有权上有不同的意见,耽搁了出版时间。我们现在还在协商。目前大部分家属希望日记送到台湾的‘国史馆’保存。”宋曹琍璇告诉澎湃新闻,“出版是有希望的,但是要达到共识需要时间。尤其我们希望今年纪念抗战七十周年时能出版一部分关于抗战的内容,蒋介石毕竟是当时的统帅。”

“盛况空前”:从学术界到娱乐圈,哪些人查阅日记?
台湾学者吕芳上曾说:“能用这样一位政治领导人的私人日记作学术研究,恐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事。海峡两岸及海外,往赴阅读蒋日记之学者,遂络绎于途。蒋日记及蒋的生平研究,几乎成为近代中国史研究的新‘显学’。”
此前公开的民国要人档案、日记不少,蒋介石档案(国民党迁台后存桃园大溪,又称“大溪档案”)也已于1990年代在台湾“国史馆”开放,其中有他1923-1972年间执掌大陆及台湾军政期间的大宗文件。但这些档案引发的公众关注都未及蒋日记的公开。
据介绍,日记开放之初,一天有几十人前往查阅,对于这个位于地下一层的安静档案馆来说可谓“盛况空前”。“我们要开两个阅览室才可让学者都能坐下看日记,”宋曹琍璇告诉澎湃新闻。
“去得最早、最多的就是来自大陆的学者,”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说。他自2006年起每年前往胡佛查档,对“盛况”有切身感受。“从社科院到一般高校,从沿海到内地学校,乃至其他个人、机构,争先恐后。蒋日记仿佛是一个检验器,检验民国史研究机构对海外一手资料的重视程度。”
中国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员杨天石就是“最早”去的学者之一。他于2006、2007、2008、2010年四次前往胡佛,前后待了10个半月,来来往往的学者同人多到记不清。“2010年龙应台也去了,她要写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历史,来看档案。朋友来打招呼,说如果她有需要,希望我毫无保留地帮助她,我当然答应。”杨天石说他们后来也没有真的讨论写作的内容,不过还是常和台湾的学界朋友聊天。
浙江大学教授陈红民于2008年、2010年两次赴美查阅日记,他记得同在那里查档的还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金以林、黄道炫,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段瑞聪,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授鹿锡俊,中国社科院近史所杨天石,南京大学教授李玉,台湾学者吕芳上、林桶法、陈立文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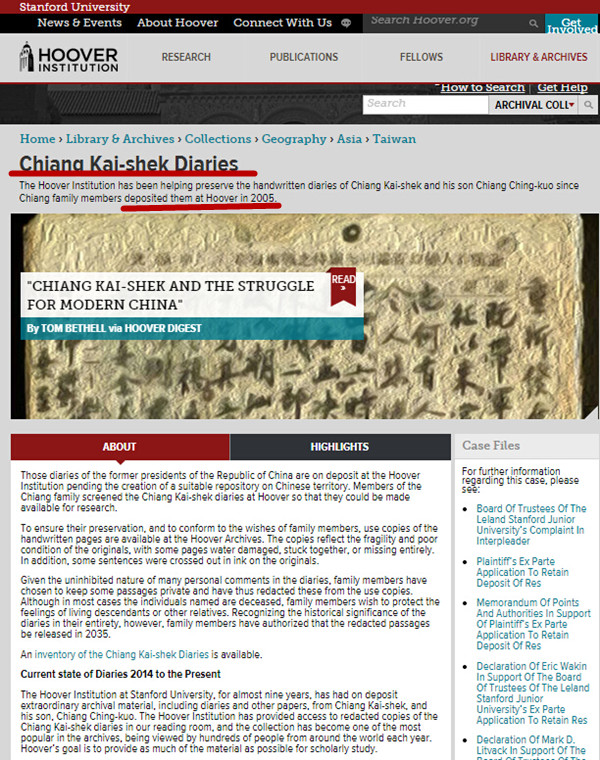
胡佛档案馆里的蒋介石日记手稿不允许复印,只能用馆方提供的纸、笔手抄。在最原始的方式面前,不论这些学者如何心急如焚、迫不及待,也只能耐住性子一页页抄录。据说斯坦福大学曾出现一种兼职工作,就叫“抄写蒋介石日记”。然而雇佣抄写毕竟是少数,多数人、多数时候还是只能靠自己。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于2007-2009年间先后派出10余名研究人员赴美,抄录1918-1952年的蒋日记,后又派专人驻美一年,将录入打印的文稿与原稿核对。据副所长金以林介绍,这一项目得到社科院的外事经费资助,目前这份日记抄件供研究使用。
陈红民就带了一个帮手——太太。陈太太并非文史工作者,起初以为到美国可以四处旅游,没想到跟着陈红民的“深度游”太“深度”,每天都在档案馆地下一层。抄到后来,即便是有些极难辨认的蒋介石字迹,陈太太也能够认出。“鹿锡俊教授的太太帮忙抄了一年的日记,一开始是鹿教授告诉她该抄什么、不用抄什么,到后来她能反过来给鹿教授提建议,这里为什么不抄?”陈红民笑言,“鹿太太也成了半个专家。”

但感兴趣的远不止学者。根据胡佛档案馆的规定,只需出示有效证件,任何人都可以查阅日记。“斯坦福的学生、附近硅谷的上班族、在美国帮子女带孩子的老人,来学习访问的政府干部、甚至一般游客,都有来看蒋日记的。有些纯粹是出于好奇,也有些是业余历史爱好者,甚至有人因此转而走上研究的道路。”陈红民告诉记者。
西南大学的研究生周昌文告诉澎湃新闻,2014年夏天他在胡佛查阅蒋介石日记,“因来看蒋日记的人很多,胡佛直接把供查阅的复制件放在阅览室,而不是地下档案库。”他曾见到一对40岁与70岁的台湾父子来抄日记,碰到有趣的内容便停下讨论;还曾见到著名音乐制作人高晓松来查日记。“7月份看到高晓松来了好几次。”周昌文说。

吴景平认为,蒋日记的开放,“整体来说是件好事”,“只有经济发达、社会进步、自信心强了,我们才不再忌讳去看蒋日记。如果是二十年前,很难想象能为此申请因公出国,而现在的学术环境、条件都有很大变化。”
当学者们谈论蒋日记时,他们在谈论什么?
蒋日记内容丰富,远道而来的学者往往时间有限,自然也各有各的“重点关注对象”。
杨天石表示:“我只有一个问题:蒋介石日记原稿和毛思诚的摘抄本有无重大差别?”他此前利用毛思诚编选的《蒋介石日记类钞》发表过相关研究,这份资料系毛思诚于1930年代根据蒋介石提供的部分日记编选而成。“我关心的是,摘抄本有没有隐瞒、歪曲日记的内容,我写过的那本书(《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的观点是否站得住脚。看过以后我觉得,摘抄本是恰当、准确的,没有问题。最重要的中山舰事件的记载也没有问题。”
陈红民致力于胡汉民研究多年,他也是带着问题去的。立法院长胡汉民1931年因与蒋介石在约法问题上产生分歧,被蒋软禁,转眼成阶下之囚。陈红民想知道,蒋介石如何决定要扣下胡汉民?他如何看待西南地方的实力派?
吴景平则介绍了日记中关于国民党对日政策的线索。“从妥协退让,到抗日成为既定政策,脉络清晰;‘九一八’、淞沪抗战、塘沽停战、华北事变等中日关系演变中的重大事件,日记中都有不少笔墨。我们还能知道有哪些高层人士参与、态度如何。”

胡佛档案馆楼上有一自助咖啡厅,供学者交流、小憩,来胡佛查档的学者常聚在这里讨论心得。郭岱君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每天下午五点档案馆闭馆之后,我们就常常在咖啡厅聊天,天黑了还不想走。每个人的关注点不一样,有人看西安事变,有人看1949年建国,大家会交换心得,所有人都非常兴奋,每天要聊好几个小时,欲罢不能。”
宋曹琍璇记得当年学者们最关心的话题:“起初是中山舰事件,接着是西安事变。蒋介石看到张学良的时候说,要军法审判,他说张学良当时‘昂昂然而去’,蒋日记就写到这里。所以大家都在猜,张学良‘昂昂然而去’之后,蒋是什么样的态度?还有台湾学者来问我‘二二八’事件有没有写上去。”
陈红民也记忆犹新。“一开始大家聊的是,老蒋骂了谁?可蒋介石在日记里骂的人实在太多,后来讨论的主题就成了:老蒋没骂过谁?李石曾、张静江这种元老他也骂过,宋美龄他都骂,有人幸免吗?还真有。”陈红民说:“据我看到的日记内容,蒋经国、吴稚晖他没有骂过。蒋介石对蒋经国的确非常偏爱;而吴稚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无政府主义者,无欲无求,忠心辅佐蒋介石。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去世了,要他接任,他都不肯。蒋介石常在日记里夸他,说稚老有远见啊。”
宋曹琍璇还谈起一桩趣事:“当时有很多学者,各人观点不同,纷纷发表言论,有位学者每次讲话都不过瘾,就决定请大家吃饭。请了3桌,30多人,可整个晚餐时间他本人一口饭也没吃,滔滔不绝地讲了2个多小时。等我们都吃完了,他说,谢谢大家聆听,他好满意。——所以你就知道当时大家的情绪有多激动,看了日记都有很多话要说。”
故事的主角是华人学者阮大仁,对于他的健谈,杨天石和陈红民也有很深的印象。杨天石回忆,和阮大仁认识就在胡佛的咖啡厅,五六个人聊天,主角就是阮大仁,依稀记得是在谈蒋介石的婚外情。“阮大仁非常好客,常招待学者们。他精通数学和电脑,当过新闻记者,他父亲是原台湾《中央日报》社社长阮毅成。阮大仁知道很多掌故,记忆力超群,能一口气讲两个小时。我有一次去他家,聊了一下午,晚上又聊了两小时,我要告辞了,他还要继续留我聊。” 杨天石后来给阮著《蒋中正日记揭秘》写序言,还把聊天欲罢不能的事写了进去。
陈红民对阮大仁的评价也是“巨能说”。他曾邀请阮到浙大就蒋介石日记进行演讲,活动结束后请客做东,但阮先生在饭桌上仍是热情演讲,却不吃饭,东道主虽无奈但也只得奉陪。
“阮大仁并非学历史出身,因蒋日记开放而钻研民国史,对照其父阮毅成的日记做了颇为精彩的研究,现在成专家了。”陈红民说,“蒋日记的影响已经溢出学术圈,除了来看日记的一般公众,阮先生的经历也是很好的注脚。”
此前浙江大学出版社曾计划出版《走近蒋介石》,邀请看过蒋介石日记手稿的学者写下在胡佛的心得。这本小书由宋曹琍璇、郭岱君牵头约稿,前后筹备了两年,其中有不少有趣、有意义的小故事。只是两年过去,这本书仍在出版流程中,尚未面市。
“后日记时代”的蒋介石形象:孰真孰假?
如何看待蒋日记的真实性?日记中的蒋介石和真实的蒋介石一样吗?这些问题在大陆曾引发争论,一次次把蒋日记和相关研究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宋曹琍璇始终认为,“蒋公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他晚年要求儿子(蒋经国)看他日记,作为借镜,作为他以后可能执政的参考。如果写的是假的,有什么参考的价值呢?”
在吴景平看来,蒋日记中对于内政外交重大问题的考虑,颇多不能为他人和外界所知的内容。“如他在1929年4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要在5年之内,‘当以(日本)江户川为陪都也’;如皖南事变爆发前关于对中共部队如何‘照预定计划逐渐压迫使之就范’和事变发生后‘应积极肃清’的谋划;又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记中大量宣泄对英美的不满,对罗斯福、史迪威等高层人物有极端厌恶甚至贬低之辞。诸如此类的内容,在写的时候不可能是有意识地随时准备公开的。”
陈红民则表示,蒋日记跨越五十余年,随着年龄、身份、地位的变化,写日记的心境亦有变化,要仔细讨论起来很复杂。“但是,记下来的事情没有假的,只是解释的动机可能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进行。这也是人之常情。”陈红民曾着重搜集1949年以后的资料著《蒋介石的后半生》一书,他表示蒋在台湾期间的日记反而更加坦率:“办孙立人、吴国桢的案子,他每天都记载动态,利弊权衡全都写了进去。甚至1972年他和宋美龄如何闹矛盾、分居,日记里都写了,还有骂宋美龄的内容。”

金以林亦赞同“写的都是真的”,但“真的未必都写”。“蒋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以后的日记就是写给别人看的。比如他在1931年时就印了一部分日记,罗家伦看过。《事略稿本》中也有大量日记摘抄,那是明确要留给后人看的。皖南事变他不可能不知道,但日记中甚为含糊。包括第三次反共高潮闪击延安,胡宗南日记里提到了,蒋日记却只字不提,布置、安排、想法,完全不流露。”金以林说。
谈起“该记而不记的内容”,杨天石举了“四•一二政变”的例子。“在上海宝山路射杀工人的是桂系当时领导下的军队,蒋介石自己则于4月9日动身前往南京。他离开前应该和李宗仁等有所交代,但是,这些蒋的日记并无记载,事实上是避开了。”此外,他表示蒋介石日记中也有说假话的情况。“所以,研究近代史,不看蒋介石日记不行,但是全信蒋介石日记,也会上当。”

论及蒋日记的价值,杨天石说:“一是透露了他的内心世界,这是一般档案中不可能有的。比如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致力于建立与美国的友好关系,但是他个人对美国人的憎恶,只能日记中看到。二是揭示了不少政坛秘闻。高层政治中的暗箱操作,日记里有,档案里看不到。但要做研究也不能只看日记,要和其他档案资料结合,相辅相成。”
金以林则表示,“蒋日记的新闻价值大于史料价值,对学术研究的推动不如对学术普及的推动。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它没有提供颠覆性的观点和新发现,但丰富了我们对历史细节的认识、了解。”
对“后日记时代”的蒋介石研究的评价的确并非一片赞美之声。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奎松曾在《蒋介石相关主题的研究回顾与展望》(“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2010年4月)一文中指出,尽管有大批学者前往查档,但近两三年大陆发表的有分量、有新意的蒋介石问题研究论文的数量却明显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究其原因,在于“以往的蒋介石研究者过多地侧重于政治史的研究,较少关注蒋的思想、情感、性格、宗教信仰、家庭关系、人际关系以及蒋的心理活动等较私人的情况。……而手稿最大的特色是大量增加了涉及蒋个人生活、情感和内心活动方面的内容……因此,过去单纯从事政治史或军事史研究的学者,要想马上将这些样新的内容与他们过去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 获得新的发现,就比较困难。”杨奎松指出,日记开放之初能够迅速诞生一批优秀的解读文章,主要是因为杨天石、金冲及等前辈学者此前的研究已有深厚积累,而不少新加入的学者前期的研究准备不足。
但可以确信的是,蒋日记的开放刺激了更多国家、地区学者对中国历史的关注。“美国前外交官陶涵依据日记写成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一书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而日本、台湾地区都有蒋日记读书会,这都是学术的交流。”吴景平告诉澎湃新闻:“从整个学界来说,日记的影响已不局限于文本本身。一方面,它刺激学术界关注更多散落海外的史学资源,另一方面,人才培养更是题中之义。日记开了一扇门,越来越多青年学者、学生有机会赴海外查档,得以开阔视野。”

蒋日记开放已近十年,这些年来对蒋介石及其日记的研究着实不少。那么我们距离一个真实的蒋介石还有多远?陈红民认为,在台湾,蒋介石正从神坛上走下;在大陆,则正从“污名化”的过去中走出,越来越接近客观的“人”——这反而使海峡两岸的蒋介石形象有了交集。金以林则这样评价蒋介石:“他不像我们以前说得那么坏,也不像‘蒋粉’说得那么好。他是一个人,做出过贡献,也带来过灾难。”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