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 +14
专访|白天他做着八卦周刊,晚上他唱着荒凉民谣

专访蒋明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晚上,他是民谣歌手,8月30日将带着空山乐队在上海MAO Livehouse带来“诗与歌的旅行”巡演,是为此次夏季巡演的尾声。白天,他是南都娱乐周刊的副总编和资深乐评人,因是“局内人”,所以在露出音乐面相的时候反而更通透亦更坚持内心的古典世界。于是他的音乐与众不同,有种书生意气特有的固执和干净。
2011年,蒋明的第一张专辑《再见北方》出版。混杂童谣和俄罗斯民歌记忆的旋律是七零、八零年代人的集体回忆。这张蒋明写于十几年前的歌曲集合,虽难免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但童声“青青山外山,绵绵云上云” (《游子谣》)的清脆破题,“我只能爱你一世不能一时”(《某年某日的情歌》)的情感沉淀,以及《桂花巷》和《时光小唱》里时光和归人的故事,已经足够建立一个完整的音乐世界。
2013年,他的第二张专辑《罔极寺》,是一张更为成熟的作品。人到中年,怀念爱情,看见死亡,末了请小河、刘东明、钟立风等朋友们合唱的一曲《啊朋友 再见》,推翻了这一代人曾被要求坚信的东西,“相信它的人就像相信一个漫长玩笑,不信它的人已没了灵魂”。蒋明和他的朋友们没有给出答案,大概怀疑就是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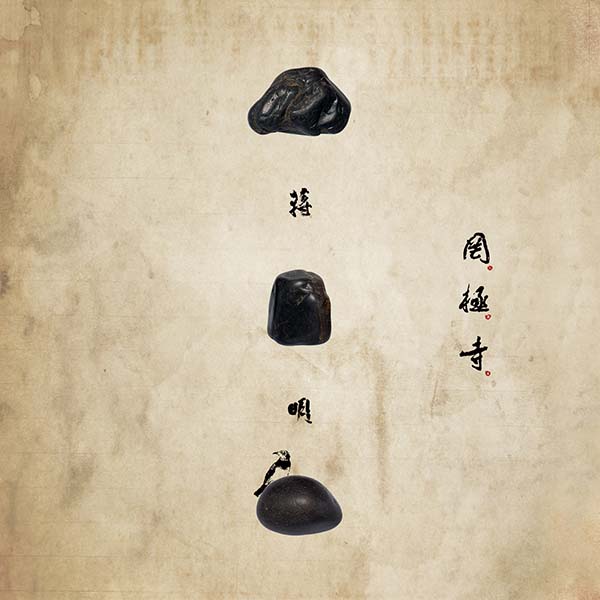
蒋明的第二张专辑《罔极寺》
【对话】
“《再见北方》是少年前传,《罔极寺》是转折口的回望”
澎湃新闻:白天做编辑,晚上做自己的事,会觉得时间不够用吗?
蒋明:没有,我觉得蛮够用的,因为我不习惯把工作上的事留到下班的时候做,一般都可以很快处理完。只要你自己会去做合理的、科学化的分配,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澎湃新闻:你觉得在娱乐周刊的工作对于你本身喜欢的文字和音乐,是会有伤害还是互相补益呢?
蒋明: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娱乐八卦是肤浅的、表面化、速食的东西,跟我现在做的民谣音乐,这种能沉淀下来的东西是相反的。但是我有时候觉得,这两者其实都是社会中存在的一种现象,八卦反映的也是社会一个层面,一种现实的状态。这种状态很多时候反而能给我启发,让我把很多这个行业里发生的事情,所思所想,转移到音乐的描述上。
澎湃新闻:现在还会经常写乐评吗?
蒋明:我做音乐之后就很少写,基本上是封笔了。
澎湃新闻:《再见北方》会有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比如《我们》里的手风琴元素带来俄罗斯民谣的味道,到了《罔极寺》的《啊朋友再见》也是这样的感觉。你自己在音乐上的喜好是不是一直很固定?
蒋明:其实是非常繁杂的,包括古典,爵士,还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国外的原生态音乐,流行音乐的各个层面。
我对民谣的特别喜好可能是来自于我们那个年代特定的记忆,以及一路走来接触到的很多其他的民谣歌手对我的影响。
在做《我们》的时候,这首3/4拍歌曲中的俄罗斯风格,并没有特别定下来。只是我作为词曲作者,以及我的制作人,都觉得这首歌就应该顺理成章地这么编,这么唱。如果你听惯了一种音乐,它在你心里会扎下根来。
《啊朋友再见》我从小听着长大,到现在也觉得它还有现实的意义。那个年代的很多伟大的、光荣的、可以上升到理想高度的事情,到了现在的社会就变成非常古怪滑稽的东西。
澎湃新闻:《罔极寺》的音乐都是这几年写的吧。在这个年纪想到贾宏声,或者《赶路》里顾城的诗,是不是会思考死亡?
蒋明: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已经处于中年状态了,难免会看到一些身边的朋友,或者长辈,陆陆续续地离开这个世界,而且和我同年代的一些小说家,诗人,都会在讨论这样的题材,这些让我去思考。
我在《赶路》和《苏州河》里都提到了关于死亡和告别的想象,引入了我自己对(这些事物)理论性的定位。《赶路》里说“人时已尽,人世很长,我在中间应当休息”,这就是我对于生命、死亡的一种理解。我们只是在这个世界上稍做休息的一个生命,每个人对于整个宇宙都像非常微小的蜉蝣。可能你对自身的死亡会看得很大,但是对于整个人类,或者上升到哲学角度的思考来说,死亡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
我在《罔极寺》里面就是想表现这种心态,希望听到的人不要因为挫折、死亡等等,表现出颓废的状态,这都是人生的无常,尤其是死亡,这是与生俱来的。在我的第三张里面,我还希望能更加深入、详细地阐述这方面的领悟。
澎湃新闻:已经在准备第三张专辑了吗?
蒋明:第三张专辑里的歌曲已经全部写完了,但是还不太知道该怎么说第三张,因为是更深层次的对生命的感悟,还需要用自身的时间去消化。
澎湃新闻:从《再见北方》到《罔极寺》,两张专辑的气质挺不一样的。第一张明确,第二张更多意向也更碎。做专辑之前你会有一个整体的概念吗?还是像写日记一样一首一首写下来,然后集成一张?
蒋明:第一张专辑集合的是我十几年前的作品,制作人在挑这张作品的时候,有两个概念,其一是向“民歌三十年”致敬,其二是做一张最简单、纯粹的专辑。
关于第二张,我并不觉得它的意象更碎,因为它是我这两三年对生命的总结。对我来说,《罔极寺》是表达内心展望,突破年龄界限的歌曲。
澎湃新闻:可以用一句或两句话来概括这两张专辑吗?
蒋明:从创作角度来讲,《再见北方》是一个前传,是少年欲闯荡江湖,懵懂无知的状态;《罔极寺》是经过了漫长的旅途之后,在人生的转折口上回望,停下来歇息的状态。
澎湃新闻:从听音乐评别人的音乐到把自己的音乐送进录音棚变成专辑,中间的过程会觉得困难吗?
蒋明:第一张挺困难的,因为还处于摸索状态。我和制作人想要达成的民谣表达方式,可能已经很多年没有人体现过了。到《罔极寺》就顺了很多。
我想可能制作每一张新专辑的困难主要并不是来自技术,而在于沟通方面。要让制作、编曲、乐队的演出跟你达成一致,这不太容易。
“看淡相逢,你最终能保全的只有你自己”
澎湃新闻:你音乐里的古典世界是个人内心世界的一个面相,还是想要坚守的全部?
蒋明:基本上是一个面相吧。我觉得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很多很多的坚守和坚持都只是人生中的一部分,但不可能脱离开现实来说。除了内心世界的安顿之外,还应该有一个现实的世界需要你去协调。
澎湃新闻:你的音乐基调挺荒凉的,是回忆本身的感觉是这样,还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蒋明:我的深层次意识里应该是个悲观的人,所以我的音乐里面透露出很多苍凉的东西。
每个人的回忆本身并不是荒凉而是温暖的,只不过这种温暖嫁接在时间里,就会产生悲伤的基调。所以写这方面的歌,悲伤的情绪会蔓延出来。但是这两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会更多地尝试表达更开阔的意境吧。
澎湃新闻:听一张专辑,很容易最后在脑子里就留下一句句子。你对自己的两张专辑会不会也有印象最深刻的“题眼”?
蒋明:《啊朋友再见》里面这句“如果我在生活中牺牲,你一定要把我埋葬”是回响比较多的,还有《遮浪镇纪事》里面的副歌部分。
如果是让我印象深刻,又能作为“题眼”的,我想应该是让我至今仍然在消化的一些哲理性的句子。如果一句歌词让一个人印象很深,那应该是跟他的生活有某种连带关系,因此产生了共鸣。
澎湃新闻:你唱了很多关于爱情的歌,想听听你对爱情的理解。
蒋明:我觉得爱情是非常古怪的,它就跟病一样。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认为爱情有“伟大”的色彩,表现出欲生欲死的姿态,甚至是更疯狂的一种态度。我觉得,爱应该是相对冷静的,是抛去欲念的。
可能会有某个人体现出来的某个瞬间,让我觉得她特别可爱。但是在爱情上,我不可能再去一见钟情,或者很疯狂。相濡以沫的,淡淡的,有距离的,甚至不去干扰对方生活的,我觉得才算是爱吧。爱情的形式有很多种。有时候可能只是一种挂记。我反而觉得天天腻在一起是最表象,最让人不放心的一种。
澎湃新闻:能结合你的某一首歌来谈吗?
蒋明:比如说《沉香亭》这首歌,写的是我认为很伟大的爱情故事(关于唐明皇和杨贵妃)。但是这个“伟大”,不在于歌中的人当初是如何在一起,而是生活在这个故事里的人,终于能在历史、命运、无数的道理当中,明白爱情真的就像一个传说。
你最终能保全的只能是你自己。就像里面最后一句唱的,“沉香亭北倚栏杆,这一场相逢要看得淡,不然年年牡丹我年年想,我种丝瓜它不长长。”
澎湃新闻:从《告别北方》到《罔极寺》,是一次从离乡到回乡的旅途吗?如果不用工作也有足够的收入生活养家,你愿意回西安还是继续留在广州?
蒋明:从歌曲的角度来说,可以大致地理解为是一次回归。把我在做的第三张专辑加进来,就可以把它们统称为“故乡的三部曲”,因为它们都是在描述我对少年时北方,以及旅途中各种故事的感悟。
我觉得“回”是一种必然。人生到了一定阶段,他必然抛弃青春时期很多疯狂的想法,回归平淡。
我觉得我要“回”的“故乡”不一定是实体。我不一定回西安,可能会去到杭州,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地方。这是一种精神方面的归宿,可能跟某一个地标没有太大关系。
澎湃新闻:你在之前的采访里说过大意是有了一定年纪写歌才会比较好。现在依然是这么认为吗?
蒋明:对,这是毫无疑问的,除非你是天才,不然必须要经过人世间的锻炼,和各种经验的栽培,否则你写出来的歌是空洞无趣的。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急急忙忙写歌,现在看着都觉得惨不忍睹,觉得怎么这么空呢?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才会对社会,对人情世故,对内心有个清晰的了解,这个时候你才能去创作,这时候你才能去告诉别人真正的道理,不然可能会误导别人。
澎湃新闻:现在觉得自己到了成熟、适宜的年纪了吗?
蒋明:我觉得我还在摸索。现在可能会有一些事情可以告诉大家了,但是成不成熟,也许还是比较两说的境地吧。
澎湃新闻:你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阅读品味是怎样的?
蒋明:我看书跟听音乐一样特别杂,各种中文小说,诗集,关于禅学的、道学的、儒家的,还读一些轻松的小说,比如《鬼吹灯》这样的,还有一些猎奇类的。这几年,我更倾向于看一些理论方面的书。这几天正在看的是林谷芳的作品。
我不读的有两类书。
一类是网络小说,像现在年轻人喜欢的穿越小说。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的小说,要给你提供想象的空间,提供养分,这是最起码的标准。
还有一类是翻译小说,因为我对文字的美感特别敏感。就我之前曾尝试阅读的翻译作品来说,我觉得很多东西被翻译过来之后,总觉得磕磕巴巴的,隔着一层。
蒋明音乐作品试听链接:www.xiami.com/album/1185049819

- :说得好
- 2014-08-26 ∙ 未知2回复举报
- :懂毛
- 2014-08-30 ∙ 未知1回复举报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